大家好,這裡書本滑欄目,本期繼續和大家探索晚期希臘的學說。此前的第4期(【哲學篇·第四期】皮浪:你說的都對,但我就是不一定相信)、13期(No.13 崇高的理想,理性平等的起源——斯多亞學派的倫理學)和14期(No.14 号稱遵守自然律的斯多亞學派,真有那麼“自然”嗎?)分别為大家介紹了晚期希臘的皮浪主義和斯多亞學派,本期,則向大家分享以“快樂”、“享樂”著稱的伊壁鸠魯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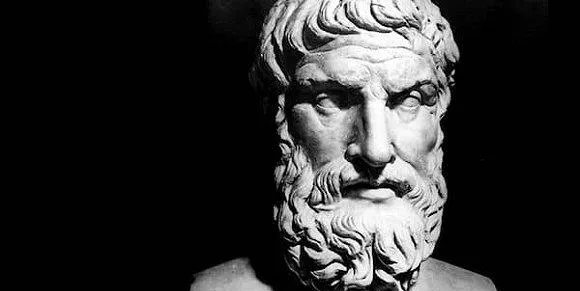
伊壁鸠魯
如往期所言,動蕩的社會環境使哲學家們不得不思考如何才能幸福生活等倫理問題,故而,伊壁鸠魯學派和斯多亞學派都需要指出,在他們看來的幸福是什麼,包含了世界如何運轉,什麼是幸福,如何認識到這個幸福,如何才能達到幸福?這種種的問題,就使得伊壁鸠魯學派和斯多亞學派的學說都同樣涵蓋了本體論/形而上學、邏輯學/認識論和倫理學等這幾個領域,以此來分别回答上述問題。
形而上學上,斯多亞學派繼承了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與logos學說;而伊壁鸠魯則繼承了德谟克裡特的原子論,認為世界由原子構成,原子本身有重量,自身即在做無規律的下落運動,不同原子的之間産生碰撞進而才産生如此千變萬化的世界。在認識論/邏輯學中,斯多亞學派推崇邏輯推論,傳承了亞裡士多德辯證法的傳統;伊壁鸠魯學派則進一步将德谟克裡特的學說發揚光大,“大逆不道”的推崇感覺主義,認為知識的來源即是感覺,感官知覺正是正确認識的基礎,我們看到的、聞到的、嘗到的、感受到的都是真的,帶來柏拉圖所說的“意見”的謬誤,隻是因為判斷出錯了,而非感覺出錯,這一點與近代哲學中的經驗主義十分相似。
既然有此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的基礎,也就決定了伊壁鸠魯學派與斯多亞學派的倫理學截然不同。在形而上學的推導下,世界本身即是無序的原子所構成,那麼“命運”和命定論的說法在伊壁鸠魯這裡自然就站不住腳。每個人的人生就是自己的人生,随機、偶然地出生,又随機、偶然地死亡,并不像斯多亞學派所說的“人生如舞台”,那麼,每個人便有自主決定生命、改變生活軌迹的權利。與此同時,在認識論的角度上,伊壁鸠魯學派推崇以感覺為認識基礎,那麼對于個人的生活來說,對生活的好與壞,自然也就是感覺上的好與壞,感情同時也顯明了人具有趨樂避苦的自然傾向。是以,伊壁鸠魯指出,倫理學中的善,即是快樂;惡,則是痛苦。
正因為将快樂視作善,伊壁鸠魯的倫理學又被稱作快樂主義。從亞裡士多德至晚期希臘這段時間,倫理學的目的都是為了追求幸福。伊壁鸠魯認為,為了能幸福地生活,必須學習倫理學,正如不能治療身體疾病的醫藥是無用的技藝,不能解除靈魂痛苦的哲學是無用的空話。是以,在伊壁鸠魯這裡,快樂便是幸福的代言詞。追尋快樂的哲學,即是能解除靈魂痛苦的哲學。
不過,雖然是快樂主義,但不像我們字面意義上所認為的偏向于享樂的快樂。伊壁鸠魯認為,人的本性傾向于追尋快樂,且每一種快樂都有其自身的吸引力所在,然而卻不是每一種快樂都值得選擇,同樣的,也并不是所有痛苦都需要避免。比方說,有的快樂之後可能帶來的是快樂的喪失,甚至是帶來痛苦,而有的痛苦之後可能會帶來長期的快樂,在這種情況下,前者的快樂并不值得追求,後者的痛苦理應承受。除了後果的不同以外,快樂也有強度的差別,精神的快樂高于肉體的快樂,倘若沒有精神的快樂,肉體的快樂不可能。伊壁鸠魯以兩種方式區分出不同的快樂,以此來說明哪些快樂更加進階,哪些快樂更加值得選擇。
一種分類法是按需求與自然的關系劃分,最低級的自然的和必需的快樂,比如食欲;又有自然卻非必需的,如性欲;還有非自然且非必需的,如虛榮心、榮譽、權力欲等等。另一種則是區分為強烈但不能持久的動态快樂和平靜而長久的靜态快樂,前者主要是欲望的要求和滿足,如娛樂、玩耍;後者則為痛苦的消除,如不饑餓、不口渴,無憂無慮的狀态。有此區分之後,延續着希臘思辨的傳統,“靜态”往往是高于“動态”,因為“靜”的東西往往都是持久而平和的,動态的東西稍縱即逝,比如自然的卻非必需的性欲的滿足,在短暫的快樂之後,迎來的卻是空虛,如同上文所說的,有些快樂之後伴随着的是痛苦。而且,滿足一個欲望之後,往往帶來的又是新的對另一個欲望的期待,在對動态快樂的追求中,所得到的快樂總是在增加或減弱,無法享受快樂會帶來心靈不安的痛苦,過度享受快樂也同樣會帶來痛苦。伊壁鸠魯指出,“當我靠面包和水而過活的時候,我的全身就洋溢着快樂;而且我輕視奢侈的快樂,不是因為它們本身的緣故,而是因為有種種的不便會随之而來。”
也就是說,伊壁鸠魯所推崇的靜态快樂,需要的是持久平和,這一點也是符合古希臘哲學中精神價值大于肉欲價值的傳統。從肉體上,需要身體健康,自然和必需的快樂需要滿足,但不必過度追求這類口舌之欲的享受,通俗點講,就是吃少了餓,吃多了撐,剛剛好就夠。精神上,則需要審慎的生活,保持甯靜的态度對待一切,不過分追求自然的卻非必需的以及既不自然也不必需的快樂。
當然,這也并不是說伊壁鸠魯主義猶如禁欲主義一般要求人降低快樂的闊值,僅僅去滿足簡單的快樂就夠了。雖然在理論等級上,靜态快樂高于動态快樂,但也并不代表動态快樂不重要。相反,他認為動态快樂的刺激豐富了對不同快樂的體驗,結合到他的感覺主義認識論中,這種種動态快樂的體驗形成個人的回憶和認知,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來擺脫痛苦。從他的角度而言,隻要這類動态快樂不會妨礙身體健康和心靈的平靜,那麼就可以放心追求。他認為,正因為大家不知道哪些快樂值得追求,哪些快樂需要适度,是以才需要以審慎的态度對待生活,謹慎地對待每一個誘惑。他也像亞裡士多德一樣,認為“德性”是重要的,一個有德性的人,便是一個能在追求快樂時審慎權衡的人。故而,需要學習哲學以此去了解事物、了解自然、了解适合人的快樂。
伊壁鸠魯主義的倫理學細說下來,并沒有如斯多亞學派般的世界大同情懷。作為同時期的兩門學說,如果說斯多亞學派放諸四海皆準,适合應用于社會、政治上的實踐;那麼伊壁鸠魯主義則旨在亂世之中安身立命,切切實實地過好自己的幸福生活,于個人自我修養的角度上看,伊壁鸠魯的快樂主義也無可指責。
可惜的是,一切實踐學說隻要傳承下去便無可避免的功利化或庸俗化,如胸懷天下平等的斯多亞學派久而久之則成為羅馬帝國的官方統治學說,如同儒家思想從一開始的以仁夫妻變為以仁治人;而伊壁鸠魯的快樂主義在日後又逐漸淪為纨绔子弟享樂避世的開脫,又多麼像魏晉之際,竹林七賢中嵇康、阮籍之“越名教而任自然”和“放浪形骸,得意忘象”的情操,不與昏暗時世同流合污的魏晉風骨,在後世傳承之中,卻被後人曲解為單純地放蕩。中國哲學中的儒家與斯多亞,玄學與伊壁鸠魯主義,在倫理學層面上可謂相當相像。
晚期希臘的四大哲學流派已經向大家介紹了其中之三,下期預告,開創三位一體的新柏拉圖主義。這裡是書本滑欄目,喜歡的朋友點個關注點個贊,我們下期再見!
參考書目:
趙敦華,《西方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版
梯利,賈辰陽 解本遠譯,《西方哲學史》,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版
羅素,何兆武 李約瑟譯,《西方哲學史·上》,商務印書館,2015版
馮達文 郭齊勇, 《新編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20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