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子脫離直線而偏斜
伊壁鸠魯認為原子在虛空中有三種運動。一種運動是直線式的下落;另一種運動起因于原子偏離直線;第三種運動是由于許多原子的互相排斥而引起的。承認第一種和第三種運動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魯共同的;可是,原子脫離直線而偏斜卻把伊壁鸠魯同德谟克利特差別開來了。
對于這種偏斜運動,很多人都加以嘲笑。西塞羅一接觸到這個論題,尤其有說不完的意見。例如,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伊壁鸠魯斷言,原子由于自己的重量而作直線式的下落;照他的意見,這是物體的自然運動。後來,他又忽然想到,如果一切原子都從上往下墜落,那麼一個原子就始終不會和另一個原子相碰。于是他就求助于謊言。他說,原子有一點點偏斜,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據說由此就産生了原子之間的複合、結合和凝聚,結果就形成了世界、世界的一切部分和世界所包含的一切東西。且不說這一切都是幼稚的虛構,伊壁鸠魯甚至沒有達到他所要達到的目的。”在西塞羅《論神之本性》一書的第1卷中,我們看到他的另一種說法:“由于伊壁鸠魯懂得,如果原子由于它們本身的重量而下落,那麼我們對什麼都無能為力,因為原子的運動是被規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他臆造出了一個逃避必然性的辦法,這種辦法是德谟克利特所沒有想到的。伊壁鸠魯說,雖然原子由于它們的重量和重力從上往下墜落,但還是有一點點偏斜。作出這種論斷比不能為自己所主張的東西進行辯護還不光彩。”
皮埃爾·培爾也同樣地判斷說:
“在他〈即伊壁鸠魯〉之前,人們隻承認原子有由重力和排斥所引起的運動。伊壁鸠魯設想,原子甚至在虛空中便稍微有點偏離直線,他說,是以便有了自由……必須附帶指出,這并不是使他臆造出這個偏斜運動的唯一動機;偏斜運動還被他用來解釋原子的碰撞,因為他當然看到,如果假定一切原子都以同一速度從上而下作直線運動,那就永遠無法解釋原子碰撞的可能性,這樣一來,世界就不可能産生,是以,原子必然偏離直線。”
這些論斷究竟确實到什麼程度,我暫且放下不提。但是,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現代的一位伊壁鸠魯批評者紹巴赫卻錯誤地了解了西塞羅,因為他說:
“一切原子由于重力,即根據實體的原因,平行地往下落,但是由于互相排斥而獲得了另一種運動,按西塞羅的說法(《論神之本性》第1卷第25頁),這就是由偶然原因,而且是向來就起作用的偶然原因産生的一種傾斜的運動。”
第一,在前面引證的那一段話裡,西塞羅并未把排斥看作是傾斜方向的根據,相反,卻認為傾斜方向是排斥的根據。第二,他并沒有說到偶然原因,相反,他指責伊壁鸠魯沒有提到任何原因;可見,同時把排斥和偶然原因都看作是傾斜方向的根據,這本身就是自相沖突的。是以,他說的至多隻是排斥的偶然原因,而不是傾斜方向的偶然原因。
此外,在西塞羅和培爾的論斷中,有一個極其顯著的特點必須立即指出。這就是,他們給伊壁鸠魯加上一些彼此互相排斥的動機:似乎伊壁鸠魯承認原子的偏斜,有時是為了說明排斥,有時是為了說明自由。但是,如果原子沒有偏斜就不會互相碰撞,那麼用偏斜來論證自由就是多餘的,因為正如我們在盧克萊修那裡所看到的那樣,隻有在原子的互相碰撞是決定論的和強制的時候,才開始有自由這個對立面。如果原子沒有偏斜就互相碰撞,那麼用偏斜來論證排斥就是多餘的。我認為這種沖突之是以産生,是由于像西塞羅和培爾那樣,把原子偏離直線的原因了解得太表面化和太無内在聯系了。一般說來,在所有古代人中,盧克萊修是唯一了解了伊壁鸠魯的實體學的人,在他那裡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較為深刻的闡述。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偏斜本身。
正如點線上中被揚棄一樣,每一個下落的物體也在它所劃出的直線中被揚棄。這與它所特有的質完全沒有關系。一個蘋果落下時所劃出的垂直線和一塊鐵落下時所劃出的一樣。是以,每一個物體,就它處在下落運動中來看,不外是一個運動着的點,并且是一個沒有獨立性的點,一個在某種定在中——即在它自己所劃出的直線中——喪失了個别性的點。是以,亞裡士多德對畢達哥拉斯派正确地指出:“你們說,線的運動構成面,點的運動構成線,那麼單子的運動也會構成線了。”是以,從這種看法出發得出的結論是,無論就單子或原子來說,因為它們處在不斷的運動中,是以,它們兩者都不存在,而是消失在直線中;因為隻要我們把原子僅僅看成是沿直線下落的東西,那麼原子的堅實性就還根本沒有出現。首先,如果把虛空想象為空間的虛空,那麼,原子就是抽象空間的直接否定,因而也就是一個空間的點。那個與空間的外在性相對立、維持自己于自身之中的堅實性即強度,隻有通過這樣一種原則才能達到,這種原則是否定空間的整個範圍的,而這種原則在現實自然界中就是時間。此外,如果連這一點也不贊同的話,那麼,既然原子的運動構成一條直線,原子就純粹是由空間來規定的了,它就會被賦予一個相對的定在,而它的存在就是純粹物質性的存在。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一個環節便是純粹的形式,即對一切相對性的否定,對與另一定在的任何關系的否定。同時我們曾指出,伊壁鸠魯把兩個環節客觀化了,它們雖然是互相沖突的,但是兩者都包含在原子概念中。
在這種情況下,伊壁鸠魯如何能實作原子的純粹形式規定,即如何能實作把每一個被另一個定在所規定的定在都加以否定的純粹個别性概念呢?
由于伊壁鸠魯是在直接存在的範圍内進行活動,是以一切規定都是直接的。是以,對立的規定就被當作直接現實性而互相對立起來。
但是,同原子相對立的相對的存在,即原子應該給予否定的定在,就是直線。這一運動的直接否定是另一種運動,是以,即使從空間的角度來看,也是脫離直線的偏斜。
原子是純粹獨立的物體,或者不如說是被設想為像天體那樣的有絕對獨立性的物體。是以,它們也像天體一樣,不是按直線而是按斜線運動。下落運動是非獨立性的運動。
是以,伊壁鸠魯以原子的直線運動表述了原子的物質性,又以脫離直線的偏斜實作了原子的形式規定,而這些對立的規定又被看成是直接對立的運動。
是以,盧克萊修正确地斷言,偏斜打破了“命運的束縛”,并且正如他立即把這個思想運用于意識那樣,關于原子也可以這樣說,偏斜正是它胸中能進行鬥争和對抗的某種東西。
但是,西塞羅指責伊壁鸠魯說:“他甚至沒有達到他編造這一理論所要達到的目的;因為如果一切原子都作偏斜運動,那麼原子就永遠不會結合;或者一些原子作偏斜運動,而另一些原子則作直線運動。這就等于我們必須事先給原子指出一定的位置,即哪些原子作直線運動,哪些原子作偏斜運動。”
這種指責是有道理的,因為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兩個環節被看成是直接不同的運動,因而也就必須屬于不同的個體,——這是不合邏輯的說法,但它也合乎邏輯,因為原子的範圍是直接性。
伊壁鸠魯很清楚地感覺到這裡面所包含的沖突。是以,他竭力把偏斜盡可能地說成是非感性的。偏斜是“既不在确定的地點,也不在确定的時間”發生的,它發生在小得不能再小的空間裡。
其次,西塞羅,據普盧塔克說,還有幾個古代人,責難伊壁鸠魯,說按照他的學說,發生原子的偏斜是沒有原因的;西塞羅并且說,對于一個實體學家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不光彩的事情了。但是,首先,西塞羅所要求的實體的原因會把原子的偏斜拖回到決定論的範圍裡去,而偏斜正是應該超出這種決定論的。其次,在原子中未出現偏斜的規定之前,原子根本還沒有完成。追問這種規定的原因,也就是追問使原子成為本原的原因,——這一問題,對于那認為原子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而它本身沒有原因的人來說,顯然是毫無意義的。
最後,如果說培爾依據奧古斯丁的權威(不過這個權威同亞裡士多德和其他古代人相比,是無足輕重的,據奧古斯丁說,德谟克利特曾賦予原子以一個精神的原則)責備伊壁鸠魯,說他想出了一個偏斜來代替這個精神的原則,那麼可以反駁他說:原子的靈魂隻是一句空話,而偏斜卻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即抽象個别性的概念。
我們在考察原子脫離直線而偏斜的結論之前,還必須着重指出一個極其重要、至今完全被忽視的環節。
這就是,原子脫離直線而偏斜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現在伊壁鸠魯實體學中的規定。相反,偏斜所表現的規律貫穿于整個伊壁鸠魯哲學,是以,不言而喻,這一規律出現時的規定性,取決于它被應用的範圍。
抽象的個别性隻有從那個與它相對立的定在中抽象出來,才能實作它的概念——它的形式規定、純粹的自為存在、不依賴于直接定在的獨立性、一切相對性的揚棄。須知為了真正克服這種定在,抽象的個别性就應該把它觀念化,而這隻有普遍性才有可能做到。
是以,正像原子由于脫離直線,偏離直線,進而從自己的相對存在中,即從直線中解放出來那樣,整個伊壁鸠魯哲學在抽象的個别性概念,即獨立性和對同他物的一切關系的否定,應該在它的存在中予以表述的地方,到處都脫離了限制性的定在。
是以,行為的目的就是脫離、離開痛苦和困惑,即獲得心靈的甯靜。是以,善就是逃避惡,而快樂就是脫離痛苦。最後,在抽象的個别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獨立性,以其總體性表現出來的地方,那裡被擺脫了的定在,就合乎邏輯地是全部的定在,是以衆神也避開世界,對世界漠不關心,并且居住在世界之外。
人們曾經嘲笑伊壁鸠魯的這些神,說它們和人相似,居住在現實世界的空隙中,它們沒有軀體,但有近似軀體的東西,沒有血,但有近似血的東西;它們處于幸福的甯靜之中,不聽任何祈求,不關心我們,不關心世界,人們崇敬它們是由于它們的美麗,它們的威嚴和完美的本性,并非為了謀取利益。
不過,這些神并不是伊壁鸠魯的虛構。它們曾經存在過。這是希臘藝術塑造的衆神。西塞羅,作為一個羅馬人,有理由嘲笑它們,但是,當普盧塔克說:這種關于神的學說能消除恐懼和迷信,但是并不給人以愉快和神的恩惠,而是使我們和神處于這樣一種關系中,就像我們和希爾卡尼亞海的魚所處的關系一樣,從這種魚那裡我們既不期望受到損害,也不期望得到好處,——當他說這番話時,作為一個希臘人,他已完全忘記了希臘人的觀點。理論上的甯靜正是希臘衆神性格上的主要因素。亞裡士多德也說:“最好的東西不需要行動,因為它本身就是目的。”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從原子的偏斜中直接産生出來的結論。這種結論表明,原子否定一切這樣的運動和關系,在這些運動和關系中原子作為一個特殊的定在為另一定在所規定。這個意思可以這樣來表達:原子脫離并且遠離了與它相對立的定在。但是,這種偏斜中所包含的東西——即原子對同他物的一切關系的否定——必須予以實作,必須以肯定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一點隻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即與原子發生關系的定在不是什麼别的東西,而是它本身,因而也同樣是一個原子,并且由于原子本身是直接地被規定的,是以就是衆多的原子。于是,衆多原子的排斥,就是盧克萊修稱之為偏斜的那個“原子規律”的必然實作。但是,由于這裡每一個規定都被設定為特殊的定在,是以,除了前面兩種運動以外,又增加了作為第三種運動的排斥。盧克萊修說得對,如果原子不是經常發生偏斜,就不會有原子的沖擊,原子的碰撞,因而世界永遠也不會創造出來。因為原子本身就是它們的唯一客體,它們隻能自己和自己發生關系;或者如果從空間的角度來表述,它們隻能自己和自己相撞,因為當它們和他物發生關系時,它們在這種關系中的每一個相對存在都被否定了;而這種相對的存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就是它們的原始運動,即沿直線下落的運動。是以,它們隻是由于偏離直線才相撞。這與單純的物質分裂毫不相幹。
而事實上,直接存在的個别性,隻有當它同他物發生關系,而這個他物就是它本身時,才按照它的概念得到實作,即使這個他物是以直接存在的形式同它相對立的。是以一個人,隻有當他與之發生關系的他物不是一個不同于他的存在,相反,這個他物本身即使還不是精神,也是一個個别的人時,這個人才不再是自然的産物。但是,要使作為人的人成為他自己的唯一現實的客體,他就必須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對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純粹自然的力量。排斥是自我意識的最初形式;是以,它是同那種把自己看作是直接存在的東西、抽象個别的東西的自我意識相适應的。
是以,在排斥中,原子概念實作了,按這個概念來看,原子是抽象的形式,但是其對立面同樣也實作了,按其對立面來看,原子就是抽象的物質;因為那原子與之發生關系的東西雖然是原子,但是一些别的原子。但是,如果我同我自己發生關系,就像同直接的他物發生關系一樣,那麼我的這種關系就是物質的關系。這是可能設想的最極端的外在性。是以,在原予的排斥中,表現在直線下落中的原子的物質性和表現在偏斜中的原子的形式規定,都綜合地結合起來了。
同伊壁鸠魯相反,德谟克利特把那對于伊壁鸠魯來說是原子概念的實作的東西,變成一種強制的運動,一種盲目必然性的行為。在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他把由原子的互相排斥和碰撞所産生的旋渦看作是必然性的實體。可見,他在排斥中隻注意到物質方面,即分裂、變化,而沒有注意到觀念方面,按觀念方面來說,在排斥中一切同他物的關系都被否定了,而運動被設定為自我規定。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得很清楚:他通過虛空的空間完全感性地把同一個物體想象成分裂為許多物體的東西,就像金子被碎成許多小塊一樣。這樣一來,他幾乎沒有把一了解為原子概念。
亞裡士多德正确地反駁他說:“是以,應該對斷言原初物體永遠在虛空中和無限中運動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說,這是哪一種運動,什麼樣的運動适合這些物體的本性。因為如果每一個元素都是被另一個元素強行推動的,那麼,每一個元素除了強制的運動之外必然還有一種自然的運動;而這種最初的運動應該不是強制的運動,而是自然的運動。否則就會發生無止境的遞進。”
是以,伊壁鸠魯的原子偏斜說就改變了原子王國的整個内部結構,因為通過偏斜,形式規定顯現出來了,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沖突也實作了。是以,伊壁鸠魯最先了解了排斥的本質,雖然是在感性形式中,而德谟克利特則隻認識到它的物質存在。
是以,我們還發現伊壁鸠魯應用了排斥的一些更具體的形式。在政治領域裡,那就是契約,在社會領域裡,那就是友誼,友誼被稱贊為最崇高的東西。
第二章 原子的質
說原子具有特性,那是同原子概念相沖突的;因為正如伊壁鸠魯所說,任何特性都是變化的,而原子卻是不變的。盡管如此,認為原子具有特性,仍然是必然的結論。因為被感性空間分離開來的互相排斥的衆多原子彼此之間,它們與自己的純本質必定是直接不同的,就是說,它們必定具有質。
是以,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完全不考慮施奈德和紐倫貝格爾的說法:“伊壁鸠魯不認為原子具有質,第歐根尼·拉爾修書中給希羅多德的信第44節和第54節是以後加進去的。”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怎樣才能駁倒盧克萊修、普盧塔克以及所有談到伊壁鸠魯的著作家的證據呢?而且,第歐根尼·拉爾修提到原子的質的地方,并不隻是兩節,而是有十節之多,即第42、43、44、54、55、56、57、58、59和61節。這些批評家所提出的理由,說“他們不知道如何把原子的質和它的概念結合起來”,是很膚淺的。斯賓諾莎說,無知不是論據[注:參看斯賓諾莎《倫理學》第1部分第36命題附錄。]。如果每個人都把古代人著作中他所不了解的地方删去,我們很快就會得到一張白闆!
由于有了質,原子就獲得同它的概念相沖突的存在,就被設定為外化了的、與它自己的本質不同的定在。這個沖突正是伊壁鸠魯的主要興趣所在。是以,在他設定原子有某種特性并由此得出原子的物質本性的結論時,他同時也設定了一些對立的規定,這些規定又在這種特性本身的範圍内把它否定了,并且反過來又肯定了原子概念。是以,他把所有特性都規定成互相沖突的。相反,德谟克利特無論在哪裡都沒有從原子本身來考察特性,也沒有把包含在這些特性中的概念和存在之間的沖突客觀化。實際上,德谟克利特的整個興趣在于,從質同應該由質構成的具體本性的關系來說明質。在他看來,質僅僅是用來說明表現出來的多樣性的假設。是以,原子概念同質沒有絲毫關系。
為了證明我們的論斷,首先必須弄明白在這裡顯得互相沖突的材料來源。
《論哲學家的見解》一書中說:“伊壁鸠魯斷言,原子具有三種特性:體積、形狀、重力。德谟克利特隻承認有兩種:體積和形狀;伊壁鸠魯加上了第三種,即重力。”在歐塞比烏斯的《福音之準備》裡,這段話逐字逐句重複了一遍。
這一段話為西姆普利齊烏斯和斐洛波努斯的證據所證明,據他們說,德谟克利特隻認為原子有體積和形狀的差别。亞裡士多德的看法正相反,在他的《論産生和消滅》一書第1卷裡,他認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具有不同的重量。在另一個地方(《天論》第1卷裡),亞裡士多德又使德谟克利特是否認為原子具有重力這一問題成為懸案,因為他說:“如果一切物體都有重力,那麼就沒有一個物體會是絕對輕的;但是,如果一切物體都是輕的,那麼就沒有一個物體會是重的。”李特爾在他的《古代哲學史》裡,以亞裡士多德的權威為依據,否定了普盧塔克、歐塞比烏斯、斯托貝的論述;他對西姆普利齊烏斯和斐洛波努斯的證據未予考慮。
我們來看一看,這幾個地方是不是真有那麼嚴重的沖突。在上面的引文裡,亞裡士多德并沒有專門談到原子的質。相反,在《形而上學》第7卷裡說道:“德谟克利特認為原子有三種差别。因為作為基礎的物體按質料來說是同樣的東西,但是物體或者因外形不同而有形狀的差别,或者因轉向不同而有位置的差别,或者因互相接觸不同而有次序的差别。”從這一段話裡,至少可以立刻得出一個結論。[注:接着馬克思删掉了下面這句話:“德谟克利特沒有提出原子的質同它的概念之間的沖突。”]重力沒有作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的一個特性被提到。那分裂了的、彼此在虛空中分散開的物質微粒必定具有特殊的形式,而這些特殊的形式是根據對空間的考察完全外在地得到的。這一結論從亞裡士多德的下面一段話中看得更明白:“留基伯和他的同僚德谟克利特說,充實和虛空都是元素……這二者作為物質,就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據。有些人認為,有一個唯一的基本實體,其他事物是從這種實體的變化中産生的,同時還把稀薄和稠密看作是一切質的原則,同這些人一樣,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也同樣教導說,原子的差别是其他事物的原因,因為作為基礎的存在隻是由于外形、互相接觸和轉向不同而有所差别…… 例如,A在形狀上與N有差别,AN在次序上與NA有差别,Z在位置上與N有差别。”
從這段話可以清楚地看出,德谟克利特隻是從現象世界的差别的形成這個角度,而不是從原子本身來考察原子的特性的。此外還可以看出,德谟克利特并沒有把重力作為原子的一種本質特性提出來。在他看來,重力是不言而喻的東西,因為一切物體都是有重量的。同樣,在他看來,甚至體積也不是基本的質。它是原子在具有外形時即已具備了的一個偶然的規定。隻有外形的差别使德谟克利特感興趣,因為除了外形的差别以外,形狀、位置、次序之中再也不包含任何東西了。由于體積、形狀、重力在伊壁鸠魯那裡是被結合在一起的,是以它們是原子本身所具有的差别;而形狀、位置、次序是原子對于某種他物所具有的差别。這樣一來,我們在德谟克利特那裡隻看見一些用來解釋現象世界的純粹假設的規定,而伊壁鸠魯則向我們說明了從原則本身得出來的結論。是以,我們要逐個地分别考察他對原子特性的規定。
第一,原子有體積。另一方面,體積也被否定了。也就是說,原子并不具有随便任何體積,而是認為原子之間隻有一些體積上的變化。應該說隻否定原子的大,而承認原子的小,但并不是最小限度,因為最小限度是一個純粹的空間規定,而是表現沖突的無限小。是以,羅西尼在他為伊壁鸠魯《殘篇》所作的注釋裡把一段話譯錯了,完全忽視了另外的一面,他說:
“但是,伊壁鸠魯認定那些小得難以置信的原子是如此細微,根據拉爾修第10卷第44節提供的證據,伊壁鸠魯說過,原子沒有體積。”
我現在不願意去考慮歐塞比烏斯的說法,照他說,伊壁鸠魯最先認為原子是無限小的,而德谟克利特卻承認有最大的原子,——按斯托貝的說法,甚至像世界那麼大。
一方面,這種說法同亞裡士多德的證據相沖突,另一方面,歐塞比烏斯,或者不如說他所引證的亞曆山大裡亞的主教迪奧尼修斯,是自相沖突的;因為在同一本書裡宣稱,德谟克利特承認不可分割的、用理性可以直覺的物體是自然界的本原。有一點是清楚的:德谟克利特并沒有意識到這種沖突,它沒有引起他的注意,而這個沖突卻是伊壁鸠魯的主要興趣所在。
伊壁鸠魯的原子的第二種特性是形狀。不過,這一規定也同原子概念相沖突,并且必須設定它的對立面。抽象的個别性就是抽象的自身等同,因而是沒有形狀的。是以,原子形狀的差别固然是無法确定的,但是它們也不是絕對無限的。相反,使原子互相差別開來的形狀的數量是确定的和有限的。由此自然而然就會得出結論說,不同的形狀沒有原子那麼多,然而,德谟克利特卻認為形狀有無限多。如果每個原子都有一個特殊的形狀,那麼,就必定會有無限大的原子,因為原子會有無限的差别,不同于其他一切原子的差别,像萊布尼茨的單子一樣。是以,萊布尼茨關于天地間沒有兩個相同的東西的說法,就被颠倒過來了;天地間有無限多個具有同一形狀的原子,這樣一來,形狀的規定顯然又被否定了,因為一個形狀如果不再與他物相差別,就不是形狀了。[注:接着馬克思删掉了下面這段話:“是以,伊壁鸠魯在這裡也把沖突客觀化,而德谟克利特隻堅持物質的方面,再也不讓人在其他規定中看到從原則得出的結論。”]
最後,極其重要的是,伊壁鸠魯提出重力作為第三種質,因為在重心裡物質具有構成原子主要規定之一的觀念上的個别性。是以,原子一旦被轉移到表象的領域内,它們必定具有重力。
但是,重力也直接同原子概念相沖突,因為重力是作為處于物質自身之外的觀念上的點的物質個别性。然而,原子本身就是這種個别性,它像重心一樣,被想象為個别的存在。是以在伊壁鸠魯看來,重力隻是作為不同的重量而存在,而原子本身是實體性的重心,就像天體那樣。如果把這一點應用到具體東西上面,那自然而然就會得出老布魯克爾認為是非常驚人的、盧克萊修要我們相信的結論:地球沒有一切事物所趨向的中心,也不存在住在相對的兩個半球上的對蹠者。其次,既然隻有和他物有差別的、因而外化了的并且具有特性的原子才有重力,那麼不言而喻,如果不把原子設想為互相不同的衆多原子,而隻就其對虛空的關系來設想原子,重量的規定就消失了,是以,不管原子在品質和形狀上如何不同,它們都以同樣的速度在虛空的空間中運動。是以,伊壁鸠魯也隻在排斥和因排斥而産生的組合方面應用重力,這就使得他有理由斷言,隻是原子的聚集,而不是原子本身才有重力。
伽桑狄就稱贊伊壁鸠魯,說他僅僅由于受理性的引導,就預見到了經驗,按照經驗,一切物體盡管重量和品質大不相同,當它們從上往下墜落的時候,速度卻是一樣的。
是以,對原子的特性的考察得出的結果同對偏斜的考察得出的結果是一樣的,即伊壁鸠魯把原子概念中本質和存在的沖突客觀化了,因而提供了原子論科學,而在德谟克利特那裡,原則本身卻沒有得到實作,隻是堅持了物質的方面,并提出了一些經驗所需要的假設。
第三章 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
紹巴赫在上面已提到過的他關于伊壁鸠魯的天文學概念的論文中說:
“伊壁鸠魯和亞裡士多德一起把本原(不可分的本原,第歐根尼·拉爾修,第10卷第41節)和元素(不可分的元素,第歐根尼·拉爾修,第10卷第86節)加以差別,前者是通過理智可以認識的原子,它們不占有任何空間。它們被稱為原子,并非因為它們是最小的物體,而是因為它們在空間裡不能被分割,按照這種看法應該認為,伊壁鸠魯沒有賦予原子以任何與空間有關的特性。但是,他在給希羅多德的信中(第歐根尼·拉爾修,第10卷第44、54節),不僅賦予原子以重力,而且還賦予它以體積和形狀…… 是以,我把這些原子算作第二類,它們是從前一種原子中産生的,但又被看作物體的基本粒子。”
讓我們更仔細地研究一下紹巴赫從第歐根尼·拉爾修的書[第10卷第86節]中引證的一段話。這段話說:“例如,認為宇宙是物體和不可觸摸的本質,或者認為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觀點。”這裡伊壁鸠魯是在教導皮托克勒斯,他寫信給他說,天象學說不同于其他一切實體學說,例如,認為一切都是物體和虛空,認為存在着不可分的基質的學說。很顯然,這裡沒有任何理由認為所談到的是第二類的原子。[注:接着馬克思删掉了下面這句話:“如果從‘這一切都沒有本原,因為原子就是原因’(這句話,人們得出結論說,伊壁鸠魯認為有第三類原子——‘作為原因的原子’,那麼,這種結論既可以說是正确的,也可以說是錯誤的。”]也許“宇宙是物體和不可觸摸的本質”和“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這兩個說法的不同,造成了“物體”和“不可分的元素”之間的差别,在這種情況下,“物體”也許就意味着與“不可分的元素”相對立的第一種原子。但這是完全不可設想的。“物體”是指與虛空相對立的有形體的東西,是以虛空又叫作“無形體的東西”。是以,在“物體”這一概念裡既包括原子又包括複合的物體。例如,在給希羅多德的信中說道:“宇宙是物體……如果沒有我們稱之為虛空、空間和不可觸摸的本質的東西的話……在物體中,有一些是複合體,另外一些則是構成這些複合體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是不可分的和不可改變的……是以,本原必然是不可分的有形體的實體。”可見,在上述這段話中,伊壁鸠魯談的首先是與虛空不同的一般有形體的東西,其次是特殊有形體的東西,即原子。[注:接着馬克思删掉了下面這句話:“在這裡不可分的元素除了作為不可分的物體之外别無任何意義,最後一段引文中在談到這些不可分的物體時說,它們就是本原。”]
紹巴赫引證亞裡士多德的話也不能證明任何東西。斯多亞派所特别強調的“本原”和“元素”之間的差别,誠然在亞裡士多德那裡也可以找到,但是,亞裡士多德也承認兩種說法是等同的。他甚至明确地說,“元素”主要是指原子。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也同樣稱充實和虛空為“元素”。
在盧克萊修那裡,在第歐根尼·拉爾修書中所載伊壁鸠魯的書信裡,在普盧塔克的《科洛特》裡,在塞克斯都·恩披裡柯那裡,都認為原子本身具有特性,因而這些特性也就被規定為自己揚棄自己。
但是,如果說隻有靠理性才能感覺的物體具有空間的質,可以被當作二律背反的話,那麼說空間的質本身隻有靠理智才能被感覺,就将是一個更大得多的二律背反。
最後,紹巴赫引用斯托貝的下面一段話來進一步論證他的見解:“伊壁鸠魯說,……原初的東西(即物體)是簡單的;而由它們所組成的複合體全都具有重力。”對斯托貝的這段話,其實還可以加上另外幾段話,其中“不可分的元素”是作為一種特殊的原子而被提到:(普盧塔克)《論哲學家的見解》第1卷第246和249頁和斯托貝《自然的牧歌》第1卷第5頁。此外,在這幾段話裡根本沒有肯定地說,原始的原子沒有體積、形狀和重力。相反,隻是提到重力是差別“不可分的本原”與“不可分的元素”的标志。但是,我們在前一章已經說過,重力隻是在原子的排斥和由排斥而産生的聚集方面才得到應用。
臆想出“不可分的元素”也并沒有得到什麼結果。要從“不可分的本原”過渡到“不可分的元素”,就同想直接賦予它們以特性一樣,是困難的。但是,我并不絕對否認這種差別。我隻是否認存在着兩種不同的、固定不變的原子罷了。确切地說,它們是同一種原子的不同規定。
在說明這個差别以前,我還要提醒大家注意伊壁鸠魯的一種手法,即他喜歡把一個概念的不同的規定看作不同的獨立的存在。正如原子是他的原則一樣,他的認識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論的。在他那裡,發展的每一環節立即就悄悄地轉變成固定的、仿佛被虛空的空間從與整體的聯系中分離開來的現實。每個規定都采取了孤立的個别性的形式。
這種手法從下面一個例子來看就清楚了。
無限,或者像西塞羅譯作的infinitio,有時被伊壁鸠魯用來當作一種特殊的自然。而正是在“元素”被規定為固定的、作為基礎的實體的地方,我們也發現,“無限”也變成一種獨立存在的東西了。
但是,無限,按照伊壁鸠魯自己的規定,既不是一種特殊的實體,也不是存在于原子和虛空之外的某種東西,相反,無限是虛空的偶然的規定。是以,我們發現“無限”有三種意義。
首先,在伊壁鸠魯看來,“無限”表示原子和虛空共同具有的一種質。在這個意義上它表示宇宙的無限性,宇宙之是以無限,是由于原子無限多,由于虛空無限大。
其次,無限性是指原子的衆多,是以,與虛空相對立的不是一個原子,而是無限多的原子。
最後,如果我們可以從德谟克利特的學說來推斷伊壁鸠魯的話,則“無限”又恰恰意味着它的對立面,即與在自身中被規定的和為它自己所限定的原子相對立的無邊無際的虛空。
在所有這些意義——而它們是原子論中唯一的甚至是唯一可能有的意義——中,無限隻不過是原子和虛空的一個規定。然而它卻被獨立化為一個特殊的存在,甚至被作為特殊的自然而與那些原則并列,它表現着那些原則的規定性。[注:接着馬克思删掉了一句話:“這個例子是有說服力的。”—]
是以,也許是伊壁鸠魯自己把原子變成“元素”這樣一個規定确定為一種獨立的、原始的原子,但是,根據曆史上較可靠的材料來推斷,情況并不是這樣;或者也許,在我們看來更有可能的是,伊壁鸠魯的學生梅特羅多羅斯最先把不同的規定變成了不同的存在,無論在上述哪一種情況下,我們都必須把個别環節的獨立化歸因于原子論意識的主觀方法。由于人們賦予不同的規定以不同存在的形式,因而人們沒有了解它們的差别。
在德谟克利特看來,原子僅僅具有一種“元素”,一種物質基質的意義。把作為“本原”即原則的原子同作為“元素”即基礎的原子差別開來,這是伊壁鸠魯的貢獻。這種差別的重要性在下面就可以看清楚。
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與本質、物質與形式之間的沖突,表現在單個的原子本身内,因為單個的原子具有了質。由于有了質,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離,但同時又在它自己的結構中獲得完成。于是,從具有質的原子的排斥及其與排斥相聯系的聚集中,就産生出現象世界。
在這種從本質世界到現象世界的過渡裡,原子概念中的沖突顯然達到自己的最尖銳的實作。因為原子按照它的概念是自然界的絕對的、本質的形式。這個絕對的形式現在降低為現象世界的絕對的物質、無定形的基質了。
原子誠然是自然界的實體,一切都由這種實體産生,一切也分解為這種實體,但是,現象世界的經常不斷的毀滅并不會有任何結果。新的現象又在形成,但是作為一種固定的東西的原子本身卻始終是基礎。是以,如果按照原子的純粹概念來設想原子,它的存在就是虛空的空間,被毀滅了的自然;一旦原子轉入了現實界,它就下降為物質的基礎,這個物質基礎,作為充滿多種多樣關系的世界的承擔者,永遠隻是以對世界毫不相幹的和外在的形式存在。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因為原子既被假定為抽象個别的和完成的東西,就不能表現為那種多樣性所具有的起觀念化作用和統攝作用的力量。
抽象的個别性是脫離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發亮。定在是使得它失掉自己的性質而成為物質的東西的一個元素。是以,原子不會在現象領域顯現出來,或者在進入現象領域時會下降為物質的基礎。原子作為原子隻存在于虛空之中。是以,自然界的死亡就成為自然界的不死的實體,盧克萊修也就有理由高呼:
“會死的生命被不死的死亡奪去了。”[注:盧克萊修《物性論》第3卷第869行。]
伊壁鸠魯和德谟克利特在哲學上的差別在于,伊壁鸠魯在沖突極端尖銳的情況下把握沖突并使之對象化,因而把成為現象基礎的、作為“元素”的原子同存在于虛空中的作為“本原”的原子差別開來;而德谟克利特則僅僅将其中的一個環節對象化。也正是這個差别,在本質世界中,在原子和虛空的領域中使伊壁鸠魯和德谟克利特分手了。但是,因為隻有具有質的原子才是完成的原子,因為現象世界隻能從完成的并且同自己的概念相背離的原子中産生,是以,伊壁鸠魯對這一點作了如下的表述:隻有那具有質的原子才成為“元素”,或者說,隻有“不可分的元素”才具有質。
第四章 時間
既然在原子裡,物質作為純粹的與自身的關系沒有任何變易性和相對性,那麼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結論,時間必須從原子概念中,從本質世界中排除掉。因為隻有從物質中抽掉時間這個因素,物質才是永恒的和獨立的。在這一點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魯也是一緻的。但是在規定脫離了原子世界的時間的方式方法上,在把時間歸入什麼地方的問題上,他們又不同了。
在德谟克利特看來,時間對于體系沒有任何意義,沒有任何必要性。他解釋時間,是為了取消時間。他把時間規定為永恒的東西,是為了像亞裡士多德和西姆普利齊烏斯所說的,把産生和消滅,即時間性的東西,從原子中排除掉。據他說,時間本身就是一個證據,證明并非一切事物都必定有起源,有開始這一環節的。
必須承認,這裡面有一個較為深刻的思想。那具有想象力的、不能了解實體的獨立性的理智,提出了實體在時間中生成的問題。不過,它沒有看到,當它把實體當成時間性的東西時,它同時也就把時間變成實體性的東西了,進而也就取消了時間概念,因為成為絕對時間的時間就不再是時間性的東西了。
但是另一方面,這種解決辦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從本質世界中排除掉的時間,被移置到進行哲學思考的主體的自我意識中,而與世界本身毫不相幹了。
伊壁鸠魯卻不是這樣。在他看來,從本質世界中排除掉的時間,就成為現象的絕對形式。也就是說,時間被規定為偶性的偶性。偶性是一般實體的變化。偶性的偶性是作為自身反映的變化,是作為變換的變換。現象世界的這種純粹形式就是時間。
組合僅僅是具體自然界的被動形式,時間則是它的主動形式。如果我按照組合的定在來考察組合,那麼原子就存在于這種組合的背後,存在于虛空中、想象中,而如果我按照原子概念來考察原子,那麼這種組合或者完全不存在,或者僅僅存在于主觀表象之中;因為它是這樣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獨立的、自我封閉的、彼此似乎毫不相幹的原子之間也同樣不發生任何關系。相反,時間,即有限事物的變換,當它被設定為變換時,同樣是現實的形式,這種現實的形式把現象同本質分離開來,把現象設定為現象,并且使現象作為現象傳回到本質中。組合表示的隻是原子的物質性以及由原子産生的自然界的物質性。相反,時間在現象世界中的地位,正如原子概念在本質世界中的地位一樣,也就是說,時間是把一切确定的定在加以抽象、消滅并使之傳回到自為存在之中。
從這些考察中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伊壁鸠魯把物質和形式之間的沖突看成是現象自然界的性質,于是這個自然界就成了本質自然界即原子的映象。其是以如此,是由于把時間與空間、現象的主動形式與現象的被動形式對立起來了;第二,隻有在伊壁鸠魯那裡,現象才被了解為現象,即被了解為本質的異化,這種異化本身是在它的現實性中作為這種異化表現出來的。相反,在把組合看成是現象自然界的唯一形式的德谟克利特那裡,現象并沒有自在地表明它是現象,是一種與本質有差別的東西。是以,如果按照現象的存在來考察現象,那麼本質和現象就完全混淆起來了;如果按照現象的概念來考察現象,則本質和現象就完全分開了,因而現象便降低為主觀的假象。組合對于現象的本質基礎采取漠不關心的和物質的态度。相反,時間卻是永恒地吞噬着現象、并給它打上依賴性和非本質性烙印的本質之火;最後,因為在伊壁鸠魯看來,時間是作為變換的變換,是現象的自身反映,是以,現象自然界就可以正當地被當作客觀的,感性知覺就可以正當地被當作具體自然的實在标準,雖然原子這個自然的基礎隻有靠理性才能觀察到。
正因為時間是感性知覺的抽象形式,是以按照伊壁鸠魯的意識的原子論方式,就産生了把時間規定為自然中的一個特殊存在着的自然的必然性。感性世界的變易性作為變易性,感性世界的變換作為變換,這種形成時間概念的現象的自身反映,都在被意識到的感性裡有其單獨的存在。是以,人的感性就是形體化的時間,就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着的自身反映。
這可以從伊壁鸠魯對時間概念的規定裡直接得出來,也可以十分确定地用個别例證予以證明。在伊壁鸠魯給希羅多德的信裡,時間是這樣被規定的:當被感官所感覺的物體的偶性被設想為偶性時,就産生了時間。是以,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覺在這裡就是時間的源泉和時間本身。是以,既不能用類比的方法規定時間,也不能用别的事物來表述時間,而是應該把握住直接的明顯性本身;因為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覺就是時間本身,是以不可能超出時間的界限。
另一方面,在盧克萊修、塞克斯都·恩披裡柯和斯托貝那裡,偶性的偶性,自身反映的變化被規定為時間。是以,偶性在感性知覺中的反映以及偶性的自身反映被設定為同一個東西。
由于時間和感性之間的這種聯系,在德谟克利特那裡也可以找到的影象,也就獲得更加合乎邏輯的地位。
影象是自然物體的形式,這些形式好像一層外殼,從自然物體上脫落下來,并把自然物體移到現象中來。事物的這些形式不斷地從它們中流出,侵入感官,進而使客體得以顯現出來。是以,是自然在聽的過程中聽到它自己,在嗅的過程中嗅到它自己,在看的過程中看見它自己。是以,人的感性是一個媒介,通過這個媒介,猶如通過一個焦點,自然的種種過程得到反映,燃燒起來形成現象之光。
在德谟克利特那裡,這是首尾不一貫的地方,因為現象隻是主觀的東西,而在伊壁鸠魯那裡卻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因為在伊壁鸠魯那裡感性是現象世界的自身反映,是它的形體化的時間。
最後,感性和時間的聯系表現在:事物的時間性和事物對感官的顯現,被設定為事物本身的同一個東西。因為正是由于物體顯現在感官面前,它們便消失了。由于影象不斷從物體中分離出來并流入感官,由于影象在自身之外,而不是在自身之内有自己的感性作為另一種自然,是以,它們不能從這種分裂狀态中回複過來,是以它們便解體并消失了。
是以,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個别的自我意識的自然形式一樣,感性的自然也隻是對象化了的、經驗的、個别的自我意識,而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識。是以,感官是具體自然中的唯一标準,正如抽象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準一樣。
第五章 天象
德谟克利特的天文學見解,從他那個時代來看,可能是有洞察力的,不過這些見解并不具有哲學的意義。它們既沒有超出經驗反思的範圍,也沒有同原子學說發生較為确定的内在聯系。
相反,伊壁鸠魯關于天體和與天體相聯系的過程的理論,或者說關于天象的理論(他用天象這一名稱來總括天體和與天體相聯系的過程),不僅與德谟克利特的意見相對立,而且與希臘哲學的意見相對立。對于天體的崇敬,是所有希臘哲學家遵從的一種崇拜。天體系統是現實理性的最初的、樸素的和為自然所規定的存在。希臘人的自我意識在精神領域内也占有同樣的地位。它是精神的太陽系。是以,希臘哲學家在天體中崇拜的是他們自己的精神。
阿那克薩哥拉是第一個從實體學上解釋天空的人,這樣,他就在和蘇格拉底不同的意義上使天接近了地。就是這個阿那克薩哥拉,當有人問他為何而生時,他回答說:“為了觀察太陽、月亮和天空。”而色諾芬尼則望着天空說:一就是神。畢達哥拉斯派、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對天體所抱的宗教态度更是人所共知的。
确實,伊壁鸠魯反對整個希臘民族的觀點。
亞裡士多德說,有時看起來是概念證實作象,而現象又證明概念。譬如,人人都有一個關于神的觀念并把最高的處所劃給神性的東西;無論異邦人還是希臘人,總之,凡是相信神的存在的人,莫不如此,他們顯然把不死的東西和不死的東西聯系起來了;因為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是以,如果有神性的東西存在——就像它确實存在那樣,那麼我們關于天體的實體的論斷也是正确的。但就人的信念而言,這種論斷也是同感性知覺相符合的。因為在整個過去的時代中,根據人們輾轉流傳的回憶來看,無論整個天體或天體的任何部分看來都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就連名稱,看來也是古代人流傳下來直至今天的,因為他們所指的東西,同我們所說的東西是一回事。因為同樣的看法傳到我們現在,不是一次,也不是兩次,而是無數次。正因為原初的物體是某種有别于土和火、空氣和水的東西,他們就把最高的地方稱為“以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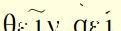
[注:永恒地流。]一詞而來),并且給了它一個别名叫作“永恒的時間”。但是,古代人把天和最高的地方劃給神,因為唯有天是不死的。而現在的學說也證明,天是不可毀滅的、沒有起始的、不遭受生滅世界的一切災禍的。這樣一來,我們的概念就同時符合關于神的預言。至于說天隻有一個,這是顯然的。認為天體即是衆神,而神性的東西包圍着整個自然界的看法,是從祖先和古代人那裡流傳下來并以神話的形式在後人中間儲存下來的。其餘的東西則是為了引起群衆的信仰,當作有利于法律和生活的東西而被披上神話的外衣添加進去的。因為群衆把衆神說成近似于人,近似于一些别的生物,進而虛構出許多與此有關和類似的東西。如果有人抛開其餘的東西,隻堅持原初的東西,即認為原初的實體是衆神這一信仰,那麼他必定會認為這是神的啟示,并且認為,正如曾經發生過的那樣,在各種各樣的藝術和哲學被創造出來,随後又消失了以後,上述這些意見卻像古董一樣,流傳到現在。
與此相反,伊壁鸠魯說:
除了這一切之外,還應當考慮到,人的心靈的最大迷亂起源于人們把天體看作是有福祉的和不可毀滅的,他們具有同這些天體相對立的願望和行為,而且他們還由于神話而産生懷疑。至于說到天象,應當認為,運動、位置、虧蝕、升起、降落以及諸如此類現象的發生,不是因為有一個享有一切福祉和不可毀滅的存在物在支配它們、安排它們——或已經安排好它們。因為行動與福祉不相一緻,行動的發生大半與軟弱、恐懼和需要有關。同樣也不應當認為,有一些享有福祉的類似火的物體,能夠任意地作出這些運動。如果人們不同意這種看法,那麼這種沖突本身就會引起心靈的最大迷亂。
是以,如果說亞裡士多德責備古代人,說他們認為天還需要阿特拉斯做它的支柱,這個阿特拉斯
“站在遙遠的西方,
用雙肩支撐着天和地的柱石”
(埃斯庫羅斯《被鎖鍊鎖住的普羅米修斯》第348行及以下各行),
那麼與此相反,伊壁鸠魯則責備那些認為人需要天的人;并且他認為支撐着天的那個阿特拉斯本身就是人的愚昧和迷信造成的。愚昧和迷信也就是狄坦神族。
伊壁鸠魯給皮托克勒斯的整封信,除了最後一節外,講的都是天體理論。最後一節包含着一些倫理方面的格言。把一些道德準則附在關于天象的學說後面是适當的。這一學說對伊壁鸠魯說來是有關良心的事。是以,我們的考察将主要依據給皮托克勒斯的這封信。我們将摘錄他給希羅多德的信作為補充,伊壁鸠魯本人在給皮托克勒斯的信中也援引了這封信。
第一,不要認為,對天象的認識,無論就整體而言或就個别部分而言,除了和研究其餘的自然科學一樣能夠獲得心靈的甯靜和堅定的信心之外,還能達到别的目的。我們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和空洞的假設,而是我們能夠過沒有迷亂的生活。正如自然哲學的任務一般是研究最主要的事物的原因一樣,認識天象時的幸福感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關于星辰的升起和降落、星辰的位置和虧蝕的理論本身,并不包含有關幸福的特殊根據。不過,恐懼卻支配着那些看見這些現象但不認識它們的性質及其主要原因的人。直到今天,關于天象的理論據說對其他科學所擁有的優越地位才被否定了,這一理論才被置于和其他科學同等的地位。
但是,關于天象的理論不僅同倫理學的方法,而且同其餘的實體學問題的方法也有着特殊的差別,例如存在着不可分的元素等等,這裡隻有一個唯一的解釋與現象相符合。而天象卻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它們的産生不能歸結于一個簡單的原因,它們有一個以上的、同現象相符合的本質範疇。因為對自然哲學的研究不應依據空洞的公理和規律。人們常常反複說,對天象的解釋不應是簡單的、絕對的,而應是多種多樣的。這适用于日月的升起和降落,月亮的盈虧,月中人的映象,晝夜長短的變化,以及其他天象。
這一切到底應如何解釋呢?
任何解釋都可以接受。隻是神話必須加以排除。但是,隻有當人們通過追尋現象,從現象出發進而推斷出不可見的東西時,神話才會被排除。必須緊緊抓住現象,抓住感性知覺。是以,必須應用類比。這樣就可以對天象以及其他經常發生并使其他人特别感到震驚的事物的根據作出說明,進而消除恐懼,使自己從恐懼中解放出來。
這大量的解釋、衆多的可能性不僅要使意識平靜下來,消除引起恐懼的原因,而且同時還要否定天體本身中的統一性,即與自身同一的和絕對的規律。各個天體可以時而這樣時而那樣地運作。這種沒有規律的可能性就是它們的現實性的特性。在天體中一切都不是固定的、不變的。解釋的多樣性同時就會取消客體的統一性。
是以,亞裡士多德同其他希臘哲學家是一緻的,他也認為天體是永恒的和不朽的,因為它們是永遠按照同一方式運作的;亞裡士多德甚至認為,它們具有特殊的、更高的、不受重力限制的元素,而伊壁鸠魯與他直接對立,斷言情況正好相反。他認為,關于天象的理論與其他一切實體學說的特殊差別在于:在天象中一切都是以多種多樣的和沒有秩序的方式發生的;在天象中一切都必須用多種多樣的、數量不确定的許多理由來解釋。伊壁鸠魯憤怒地、措辭激烈地駁斥對立的意見說,那些堅持一種解釋方式而排斥其他一切解釋方式的人,那些在天象中隻承認統一的、因而是永恒的和神性的東西的人,正在陷入虛妄的解說和占星術士的毫無創見的戲法之中;他們越出了自然科學的界限而投身于神話的懷抱;他們企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為毫無意義的東西而枉費精力,他們甚至不知道,心靈的甯靜本身在哪裡會遭到危險。他們的空談應該受到蔑視。必須屏棄這樣一種成見:認為隻要對那些對象的研究的目的僅僅在于使我們得到心靈的甯靜和幸福,這種研究似乎就是不夠徹底、不夠精細的。相反,絕對的準則是:一切擾亂心靈的甯靜、引起危險的東西,不可能屬于不可毀滅的和永恒的自然。意識必須明白,這是一條絕對的規律。
于是,伊壁鸠魯得出結論說:因為天體的永恒性會擾亂自我意識的心靈的甯靜,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結論就是,它們并不是永恒的。
伊壁鸠魯的這種獨特的見解究竟應該如何去了解呢?
所有論述伊壁鸠魯哲學的作者,都把這一學說說成是同其他一切實體學,同原子學說不相容的。反對斯多亞派、反對迷信、反對占星術的鬥争就被當成了充分的根據。
我們也曾看到,伊壁鸠魯本人也把在關于天象的理論中運用的方法同其他實體學的方法差別開來。但是,他的原則的哪一條規定中存在着這種差別的必然性呢?他怎麼會産生這種想法呢?
要知道,他不僅同占星術進行鬥争,而且也同天文學本身,同天體系統中的永恒規律和理性進行鬥争。最後,伊壁鸠魯同斯多亞派的對立并不能說明什麼問題。當天體被說成是原子的偶然複合,天體中發生的過程被說成是這些原子的偶然運動時,斯多亞派的迷信和他們的整個觀點就已經被駁倒了。天體的永恒本性是以就被否定了——德谟克利特隻限于從上述前提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而且連天體的定在本身也因而取消了。是以,原子論者就不需要新的方法了。
這還不是全部困難所在。這裡産生了一個更加難于了解的二律背反。
原子是具有獨立性、個别性形式的物質,好像是想象中的重力。但是,重力的最高現實性就是天體。在天體中一切構成原子發展的二律背反——形式和物質之間、概念和存在之間的二律背反都解決了;在天體中一切必要的規定都實作了。天體是永恒的和不變的;它們的重心是在它們自身之内,而不在它們自身之外;它們的唯一行動就是運動,被虛空的空間分隔開的各個天體偏離直線,形成一個排斥和吸引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它們同樣保持着自己的獨立性,并且最後從它們自身中産生出時間,作為它們顯現的形式。是以,天體就是成為現實的原子。在天體裡,物質把個别性納入它自身之中。是以,在這裡伊壁鸠魯必定會看見他的原則的最高存在,看見他的體系的最高峰和終結點。他聲稱,他假定有原子存在,是為了給自然奠定不朽的基礎。他聲稱,對他來說重要的是物質的實體性的個别性。但是,隻要他發現天體是他的自然的實在性(因為他除了機械的自然外不承認任何别的自然),即獨立的、不可毀滅的物質,而天體的永恒性和不變性又是為群衆的信仰、哲學的判斷、感官的見證所證明了的,那麼,他的唯一的意圖,就是要使天體降到地上的非永恒性中來,他就要激烈地反對那些崇拜自身中包含着個别性因素的獨立的自然的人。這就是他最大的沖突。
是以,伊壁鸠魯感覺到,他以前的範疇在這裡崩潰了,他的理論的方法[注:馬克思作了修改,原來是:“他的方法的理論”。]正在變成另一種方法。而他感覺到這一點并有意識地說出這一點,這正是他的體系所達到的最深刻的認識,最透徹的結論。
我們已經看到了,整個伊壁鸠魯的自然哲學是如何貫穿着本質和存在、形式和物質的沖突。但是,在天體中這個沖突消除了,這些互相争鬥的環節和解了。在天體系統裡,物質把形式納入自身之中,把個别性包括在自身之内,因而獲得它的獨立性。但是,在達到這一點後,它也就不再是對抽象自我意識的肯定。在原子世界裡,就像在現象世界裡一樣,形式同物質進行鬥争;一個規定取消另一個規定,正是在這種沖突中,抽象的、個别的自我意識感覺到它的本性對象化了。那在物質的形态下同抽象的物質作鬥争的抽象形式,就是自我意識本身。但是現在,物質已經同形式和解并成為獨立的東西,個别的自我意識便從它的蛹化中脫身而出,宣稱它自己是真實的原則,并敵視那已經獨立的自然。
另一方面,這一點可以這樣來表達:由于物質把個别性、形式納入它自身之中,像在天體中的情況那樣,物質就不再是抽象的個别性了。它成為具體的個别性、普遍性了。是以,在天象中朝着抽象的、個别的自我意識閃閃發光的,就是它的具有了物質形式的否定,就是變成了存在和自然的普遍的東西。是以,自我意識把天象看作它的死敵。于是,自我意識就像伊壁鸠魯所做的那樣,将人們的一切恐懼和迷亂都歸咎于天象。因為恐懼,抽象的個别的東西的消亡,正是普遍的東西。是以,在這裡伊壁鸠魯的真實原則,抽象的、個别的自我意識,已經不再隐蔽了。它從它的隐蔽處走出來,擺脫了物質的外殼,力求通過按照抽象的可能性所作的解釋,來消滅那已經獨立的自然的現實性,——所謂抽象的可能性是說,可能的東西也可能以别的方式出現;也可能出現可能的東西的對立面。是以,他反對那些簡單地,即用一種特定的方式來解釋天體的人;因為一是必然的和在自身内獨立的東西。
是以,隻要作為原子和現象的自然表示的是個别的自我意識和它的沖突,自我意識的主觀性就隻能以物質自身的形式出現;相反,當主觀性成為獨立的東西時,自我意識就在自身中反映自身,以它特有的形态作為獨立的形式同物質相對立。
從一開始就可以說,在伊壁鸠魯的原則将得到實作的地方,這個原則對他說來就不再具有現實性了。因為如果個别的自我意識事實上從屬于自然界的規定性,或者自然界事實上從屬于自我意識的規定性,那麼個别的自我意識的規定性,即它的存在,便會停止,因為隻有普遍的東西在它與自身自由地差別開來時,才能同時實作它的肯定。
是以,在關于天象的理論中表現了伊壁鸠魯自然哲學的靈魂。凡是消滅個别的自我意識的心靈的甯靜的東西,都不是永恒的。天體擾亂自我意識的心靈的甯靜,擾亂它與自身的同一,因為天體是存在着的普遍性,因為在天體中自然已經獨立了。
是以,伊壁鸠魯哲學的原則不是阿爾謝斯特拉圖斯的美食學,像克裡西普斯所認為的那樣,而是自我意識的絕對性和自由,盡管這個自我意識隻是在個别性的形式上來了解的。
如果抽象的、個别的自我意識被設定為絕對的原則,那麼,由于在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占統治地位的不是個别性,一切真正的和現實的科學當然就被取消了。可是,一切對于人的意識來說是超驗的東西,因而屬于想象的理智的東西,也就全都破滅了。相反,如果把那隻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現其自身的自我意識提升為絕對的原則,那麼這就會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義大開友善之門。關于這種情況的曆史證明,可以在斯多亞派哲學中找到。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識本身具有一種在事物自身中肯定自己的欲望,而這種自我意識要在事物中得到肯定,就隻有同時否定事物。
是以,伊壁鸠魯是最偉大的希臘啟蒙思想家,他是無愧于盧克萊修的稱頌的:
人們眼看塵世的生靈含垢忍辱,
在宗教的重壓下備受煎熬,
而宗教卻在天際昂然露出頭來,
兇相畢露地威逼着人類,
這時,有一個希臘人敢于率先擡起凡人的目光
面對強暴,奮力抗争,
無論是神的傳說,還是天上的閃電和滾滾雷鳴,
什麼都不能使他畏懼……
……
如今仿佛得到報應,宗教已被徹底戰勝,跪倒在我們腳下,
而我們,我們則被勝利高舉入雲。
我們在概論部分[注:指本文第一部分。]的結尾所提出來的關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鸠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别,在自然界的所有領域都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證明。是以,在伊壁鸠魯那裡,包含種種沖突的原子論作為自我意識的自然科學業已實作和完成,有了最後的結論,而這種具有抽象的個别性形式的自我意識對其自身來說是絕對的原則,是原子論的取消和普遍的東西的有意識的對立物。相反,對德谟克利特來說,原子隻是一般的、經驗的自然研究的普遍的客觀的表現。是以,對他說來,原子仍然是純粹的和抽象的範疇,是一種假設,這種假設是經驗的結果,而不是經驗的推動原則;是以,這種假設也仍然沒有得到實作,正如現實的自然研究并沒有進一步受到它的規定那樣。
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