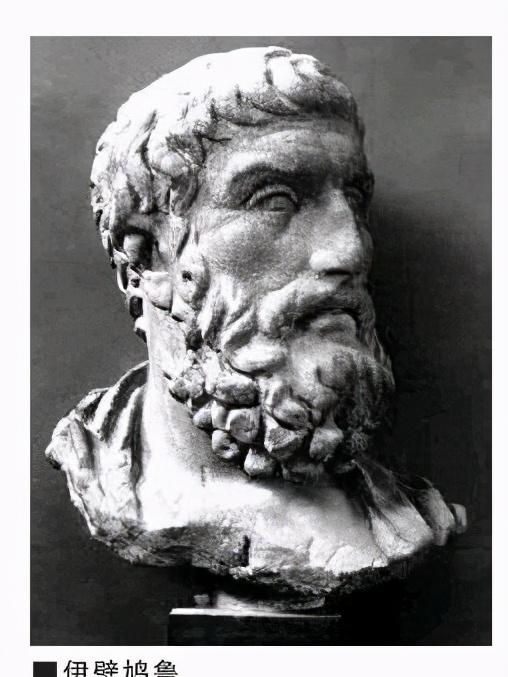
伊比鸠魯說:“所有的快樂從本性上講都是人的内在的好,但是并不是都值得選擇,就像所有的痛苦都是壞的,但并不都是應當規避的。主要是要互相比較和權衡,看它們是否帶來便利,由此決定它們的取舍。有的時候我們把好當作壞,有的時候又把壞當成好。“(伊壁鸠魯、盧克萊修:自然與快樂——伊壁鸠魯的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p.32-3;以下隻注頁碼)
伊壁鸠魯這裡說的,是通過理性的選擇,來決定最能實作幸福生活終極目的的做法。
既然并非所有的快樂都值得選擇,而快樂就是欲望的滿足,那麼在伊壁鸠魯看來,哪些欲望是應該滿足的呢?他說:“在所有的欲望中,有的是自然的和必要的;有的是自然的但不是必要的;有的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要的,而是由于虛幻的意見産生的。”按照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解釋,第一種情況,欲望的滿足是為了去除痛苦,例如渴的時候想要喝水;第二種情況,欲望的滿足不是為了去除痛苦,隻不過是種類變化的快樂,例如,同樣是“喝”,卻變化為奢侈的宴飲;第三種情況,例如想要滿足“戴上王冠,被樹立雕像”的欲望。(p.41)
有論者說:伊壁鸠魯“認為欲望有三種:自然而必要的,例如食欲;自然而不必要的,例如性欲;不自然又不必要的,例如獲得公權力的野心。”(徐國棟:伊壁鸠魯學派的快樂主義、邊沁功利主義與英國法人性假設的形成,河南财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持類似觀點的論者還有不少。
這種分類是不符合伊壁鸠魯本意的。就食欲即吃喝而言,“渴了喝水”是食欲,“奢侈的宴飲”也是食欲,伊壁鸠魯認為前者是自然而必要的,後者是自然而不必要的。
就性欲而言,不能籠統地說伊壁鸠魯認為它是自然而不必要的。伊壁鸠魯确實說過,“性愛對人并沒有好處;如果不受其傷害的話,那已經是謝天謝地了。”(p.52)該論者就是據此認定伊壁鸠魯把性欲看成是自然而不必要的。
伊壁鸠魯還有一段類似的話,不過更為詳細一些,我們來看一看:“伊壁鸠魯對一個年輕人說:我從你的信中得知你的天性使你過分地沉溺于性愛。這麼說吧,隻要你不違反法律或社會習俗或幹擾鄰居或搞垮身體或花光錢财,你可以跟着天性走,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幾乎不可能不受到這當中起碼一種問題的困擾。性愛從來也沒有對誰有過什麼好處過;如果它不傷害一個人的話,已經是僥幸了!”(p.48)
最後說的一句話跟上面所引的類似,而這句話有一個前提,就是它前面的一些話,它是從那裡得出的。這個前提就是,伊壁鸠魯是在談論一個具有“過分沉溺性愛”天性的年輕人;即使這樣,他還是建議對方跟着天性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說,伊壁鸠魯的态度是,性愛不僅是自然的,在不過分的情況也是必要的;如果過分了,就可能傷害到自己。這跟食欲的滿足是一樣的:吃吃喝喝在不過分的情況下不僅自然而且必要;如果過分了,講究到奢侈浪費的地步,就可能造成損壞腸胃、耗費錢财等傷害自己的後果,那就是雖然自然卻沒有必要了。
是以他說:“沒有任何快樂本身是壞的,但是某些享樂的事會帶來比快樂大許多倍的煩惱。”(p.39)
伊壁鸠魯認為,自然而必要的欲望之滿足,以“身體的由于匮乏而産生的痛苦全都被消除”為限度,此後“身體的快樂就再也不會增長了,隻能在種類上變換花樣。”(p.40)而這一點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是以,他認為奢侈的财富對于人們是毫無意義的,“就像水對于已經倒滿水的杯子毫無意義一樣。”(p.54)
有論者說:“伊壁鸠魯學派認為,能快樂還是盡量追求快樂,因為人生畢竟隻有一次,何況追求快樂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事情。”(丁智瓊:“快樂即幸福”和“有德即幸福”——伊壁鸠魯學派與斯多亞學派幸福觀之比較,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年第3期)
從我們前面對伊壁鸠魯思想的分析看,這樣來概括他關于快樂的學說是不準确的。伊壁鸠魯認為一個人應該追求的終極目的是身體無痛苦和靈魂無煩惱,對快樂的追求應該服從這個目的,并不是無論什麼快樂都值得追求的。
(作者黃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