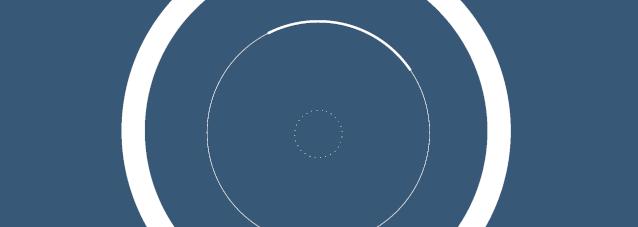
怡晴 | 文 石燦 | 編輯
2022年末,一檔《我們民謠2022》的綜藝節目,讓懷舊黨在朋友圈瘋狂刷屏。
張玮玮的《米店》,萬曉利的《陀螺》,鐘立風的《在路旁》……曾經的民謠經典,再次出現在螢幕前,讓大家回到了曾經白衣飄飄的年代,以及破舊的酒吧中,一起重拾态度,感懷青春。
音綜是圈層音樂最好的破圈管道,節目的播出,讓“民謠”再次進入大衆的視野。
而“到底什麼是民謠”的話題,也從節目一開始讨論到節目結束之後。在社交網絡上,一千個網友,對民謠就有一千種解釋,有人覺得民謠是一種純粹,有人覺得音樂之間沒有民謠與搖滾之分……
民謠确實沒有嚴格的定義,也以至于發生過一些有趣的混淆。十三月文化創始人盧中強和刺猬公社開玩笑,參加民謠節目的音樂人馬條,曾經還拿過華語傳媒的最佳搖滾獎項。
馬條,圖源新浪微網誌@愛奇藝我們民謠2022
《我們民謠2022》收官那晚,民謠樂評人郭小寒在酒吧中和大家一起觀看了這檔節目。她在現場說,或許我們不必去糾結民謠是什麼,民謠是否不火的問題,它一直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中,從未離開。
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在2023年的2月,和十三月文化創始人盧中強、樂評人郭小寒、音樂人陳鴻宇一起聊了聊民謠的定義,前世今生,以及生命力。
對于民謠圈的從業者來說,民謠一直都在細水長流;而對于大衆來說,了解民謠,才能更好地走近民謠,感受它的獨特魅力。
《我們民謠2022》的出現隻是一個契機,中國民謠發展三十年,肆意生長,又産生斷代。在圈層音樂成為爆款的當下,中國民謠比以往更需要被了解。
了解民謠
“民謠”是一種很難定義的音樂品類,即便一直沉浸在這個圈子中的盧中強,面對這個問題也隻能有些困惑地回答:“到今天為止,我也不知道該如何給‘民謠’下定義。”
90年代,正是校園民謠興盛的時代,那個時候有葉蓓《白衣飄飄的年代》,水木年華的《一生有你》,樸樹的《那些花兒》《NEW BOY》,以及老狼的《同桌的你》《戀戀風塵》等。
在流行音樂席卷大陸的時代,民謠也借勢而起,風光無限,成為很多中年人的青春過往。
盧中強在校園民謠正當繁榮的時期,創作了一首叫做《七月》的歌曲,這首歌曲的伴奏是一把吉他完成的,一首民謠範兒的音樂就這樣做了出來。後來,這首歌曲被劃分為校園民謠的代表性歌曲之一。
在大衆的印象中,民謠似乎就是音樂人在簡單的琴弦上撥出的懷舊青春。
盧中強,圖源受訪者
1999年,憑借着音樂才華,盧中強入職華納,參與老狼、葉蓓等人的專輯制作,然而他理想中的“民謠之路”才剛剛開啟。
從90年代進入到2000年代,港台音樂盛行,周傑倫、孫燕姿、SHE成為大街小巷的一種流行。彼時的華納總裁許曉峰想做一張獨特的專輯,他給盧中強提要求,“我想聽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許曉峰想要的是沒有聽過的非流行旋律、港台沒有,内地獨有的音樂。盧中強找了很長時間,都覺得不符合标準,後來有人告訴他,在北京晚報的中縫中可以看到一些地下的獨立演出廣告,那裡或許有他想要的音樂新物種。
事實确實如此,在往後的一段時間裡,盧中強在一些演出場合聽到了周雲蓬、萬曉利、小河、木推瓜、山人樂隊等完全不在主流流行音樂審美體系的、充滿了驚喜和強烈辨識度的音樂人。
周雲蓬,圖源新浪微網誌@愛奇藝我們民謠2022
可惜的是,因為種種原因這張合輯最終沒有完成制作,而盧中強也在那個時候下定決心,将來要簽這樣的音樂人,制作這樣的音樂。
比起民謠音樂人,盧中強更願意稱這些人為獨立音樂人。
“他們的音樂作品當中所彰顯出來的人文精神、收藏價值和現實批判深深的吸引了我,在音樂的編曲、演唱方式、和歌詞寫作方式上都有完全屬于他們自己的一套特有的辨識體系,其中有一些音樂人他們音樂當中的民族根源性,尤其吸引我。”
盧中強簽約的第一個音樂人是蘇陽,他是用布魯斯的形式唱西北的花兒;馬條的音樂創作當中,有強烈的西北少數民族的音樂屬性;此外,他還簽過山人樂隊,他們會用樂隊化的音樂去玩雲貴民歌。
而這批音樂人的出現,也讓民謠變得更為廣闊,跨出了校園,到地域中,傳達更多的思緒。
與大多數風格化成形的音樂品類不同,民謠似乎一直在變。
2010年之後,網際網路興起,豆瓣小組、QQ音樂、酷狗音樂、蝦米音樂、網易雲的發展,都為民謠的火助推了一把,普通人制作出簡單的音樂demo就可以上傳,被看到的機會變得更多。
于是趙雷的《成都》,馬頔的《南山南》,陳粒的《奇妙能力歌》,陳鴻宇的《理想三旬》都成為10年代後的經典曲目。
“那個時候可能有一個大風潮,就是很多獨立音樂人身上會有一種漂泊的氣質,比如拿着一把木吉他,然後朝着自己的方向去編曲。”
音樂人陳鴻宇回憶,民謠音樂人在沒有獲得一定知名度之前,制作初期條件往往有限。但自己邊彈邊唱的形式,反而表達出了最自然本質的東西,天然具備民謠的氣質。
陳鴻宇,圖源新浪微網誌@衆樂紀陳鴻宇
對于陳鴻宇而言,民謠除了容易傳唱外,自己認知裡的民謠更是與“個人情結”息息相關的,是具有根源性的。
陳鴻宇來自内蒙古額爾古納市,比起民謠,他從小受到本地民歌的影響更多。
長大之後,陳鴻宇背着吉他,走出了家鄉,來到更廣闊的世界,他的兒時、家鄉、曾經的玩伴、離家時父母的叮囑,都安置到了記憶的儲存櫃中,陪伴着他步履不停。
他把自己當做博物館,然後在這個博物館中不斷地去挖掘自己,進而完成對音樂的思考。
《理想三旬》隻是這個博物館中的一角,《額爾古納》《人在旅途》《一如少年模樣》也都是他從自己内心中尋找到的音樂。
樂評人郭小寒在大學畢業後,從事音樂記者的職業。他采過老狼、葉蓓、鐘立風,和民謠音樂人們打成一片。或許是因為寫作采訪太多而無法超越,她被大家稱作“民謠酵母”。後來,孰能生巧,她從記者的行業進入到民謠的産業當中,做音樂人的經紀人,為他們的演出做策劃等。
随着時代與人的變化,她将民謠分為三個階段,一類是以老狼、小柯等為代表的90年代校園民謠,“他們是學院派和唱片的工業精英”;一類是以野孩子、小河、萬曉利等為代表的城市新民謠,“他們是清苦的都市異鄉客”;一類是以陳鴻宇、程璧、好妹妹等為代表的網際網路新民謠,“他們是自由生長的新文化IP”。
從業二十多年的郭小寒覺得民謠不需要定義,它就是一個抽象而獨特的音樂品類,“它的叙事性比較強,跟日常生活聯系更近。民謠是娓娓道來,是自我意識的覺醒,是内心的情感的一種表達,是聽衆在音樂中看到的自己。”
比起技巧、風格、表達形式,民謠更是一種内生的力量,它被音樂人寫在歌詞中,賦予内心深處的靈魂。民謠可以是是青春,是懷舊,是民族,是遊走在城市上空的漂泊,也是一個群體的擰巴。
比起形式,它更走心,這或許是民謠容易擊中觀衆,卻也難以被了解的原因。
民謠在路上
民謠有過主流意義上的繁榮。
在郭小寒的記憶中,民謠曾一度火到“流行音樂”的程度。在90年代,老狼的一張唱片可以賣到上千萬張,甚至還帶着《同桌的你》登上了春晚的大舞台。
當時的民謠已經火成了一種“主流”,“那個時候雖然大家也叫它為民謠,但不會像現在刻意強調它的不同,它就是流行音樂的一部分,民謠也好,搖滾也好,流行也好,都有很火的人。”
當時的民謠,随着音樂行業的盛行而水漲船高。郭小寒回憶,當時大地唱片公司,在做産品的時候,會在電視台将賣點鋪滿,獨立唱片行業在這一方面的運作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2004年,郭小寒從蘭州畢業來到北京。魔岩三傑的搖滾時代已經過去,隻剩下相對簡約、低成本的音樂在小酒吧中日複一日地演出。
那時的郭小寒在主流媒體中寫東西,盧中強開始為蘇陽、萬曉利等獨立音樂人尋找更大的空間。當記者遇到制作人,兩個人便開啟了那個時代的宣傳合作,郭小寒開始了要在演出結束後,和音樂人聊天的工作。
“民謠人都是比較樸素的,采訪就像跟普通人、或者跟同僚聊天一樣。”
和大火的歌手不同,民謠人的采訪沒有安保和助理跟着,他們在演出結束後,和記者一起坐在飯桌上,就像朋友一樣,一直聊到半夜。
聊的内容未必是音樂相關,有的時候是詩歌,有的時候是電影,“把采訪變成了一種溝通方式,當時老盧(盧中強)給大家營造了像朋友一般互相了解的氛圍,還是很珍貴的。”
聊得來就當朋友,聊不來就話不投機半句多,然後各自回家。這些雞毛蒜皮的生活隻是創作者的冰山一角,他們會帶着冷靜客觀的心态去觀察生活,再将這些痛苦與美好化作酒後的靈感。
這批音樂人的創作是以一直都保持着獨特的審美,但現實發展的問題也不得不被重視。
2006年,盧中強創立了十三月文化,簽約了蘇陽、萬曉利、馬條、鐘立風等音樂人的藝人經紀。
那個時候這批音樂人的商業演出機會很少,十三月給出的專輯預付和工資是他們的重要的收入來源。盧中強也非常積極地讓這些非主流的音樂人有更多曝光的機會,如為山人樂隊争取到一次上《快樂大學營》的機會,還曾經在北京地鐵1号線投放了萬曉利的硬廣。
圖源:新浪微網誌@愛奇藝我們民謠2022
2009年,盧中強帶着馬條的新專輯找到了某著名排行榜,希望做一些推廣。那時候的音樂排行榜打榜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盧中強希望這個主流排行榜能夠好好宣傳一下馬條的新專輯,但遭到了拒絕,他一怒之下做了一部叫做《那一夜我們搞音樂》的話劇,為一大批才華橫溢、在主流很少有露出機會的音樂人發聲。
這部劇的男一号是《子曰》的主唱秋野,與此同時,萬曉利、蘇陽、馬條、張楚、謝天笑也都有參演。當時這部劇在解放軍歌劇院連演一周,獲得了場場爆滿的效果。
也在那一年的冬天,在北京的百子灣,距聖誕節還有一個月的時間,盧中強和榕樹下總經理張恩超、總編輯王小山喝了一頓大酒達成了一個合作:讓獨立音樂人組團進劇場、進音樂廳、甚至進體育館,做密集的巡演,給這些獨立音樂人以更大的舞台。
榕樹下作為冠名方拿出了60萬,盧中強湊了40萬,湊成了一個基本盤。
最後飯店要關門,基本盤的策劃也有了名稱,是盧中強随口起的,叫“民謠在路上”。那天他記憶深刻,三個人喝完酒,從飯店出來的時候,片片雪花正從空中飄落。
2010-2014年期間,大批音樂人開啟了“民謠在路上”的全國巡演,他們從北京、青島、西安、武漢,一路唱到了廣州,讓此時相對小衆的民謠,被更多人認識。
“其實我挺感謝王小山的,當時微網誌流行,他又是微網誌大V,對我們的活動起到了一個很好的宣傳作用。”
第一場演出就爆了。多年沒唱歌的沈慶再次登台,演唱的《青春》引來很多人的圍觀。也有特别無奈的時候,有一次在武漢的live house演出,周雲蓬、馬條、萬曉利、山人樂隊等人都在,結果幾個人的演出一共賣了47張票。
但無論如何,“民謠在路上”的計劃一直持續至今,演遍了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劇場、音樂廳,演出場次超過500場。
“當你演得夠多時,就有了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也正是有了盧中強這批從業者、音樂人近10年來對民謠的助推,使得民謠做好了網際網路時期爆發的準備。
民謠在壯大
《我們民謠2022》播出後,除了對民謠定義的讨論,這檔回報并沒有預期中熱烈的節目,又引發了觀衆的另一重疑惑:“民謠是否不火了?”
畢竟,校園民謠、都市異鄉客、再到新文化IP,每個時期都有現象級的音樂出現,而在節目中,口口相傳的依然是曾經的經典音樂。即便新生代音樂人蔣先貴受到了很多關注,卻也是這個領域為數不多嶄露頭角的新人。
陳鴻宇認為民謠沒有是否“不火了”的說法,而是存在着一個時空上的斷代。2016年後,陳鴻宇就很少聽說圈内有耳熟能詳的歌手了,從時間的縱軸上看,民謠确實存在着一段爆款的空白。
一方面,是因為2015年之後,音樂市場發生了收聽方式、版權邏輯、音樂人自身發展模式的變化,無論是聽衆的心态,還是音樂人的心态,都有所轉變。
另一方面,綜藝市場的崛起,讓民謠翻唱變得更為火爆,盡管在無形中催化了市場的發展,讓民謠走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但卻并未形成一種正面的鼓勵——翻唱帶來的隻是歌火,以及形态上的火,“很多民謠風格類的音樂都出現了,卻鮮少有好的原創音樂出現。”
而嘻哈、搖滾等音綜的走紅,也搶先赢得了一部分熱度。飛速發展的音樂市場,并不會留在原地等待民謠這一個品類。
事實上,民謠一直有着自己的節奏和步伐。
郭小寒在生活中也曾被問到民謠是否不火的問題,在她看來這是一個僞命題:“任何一種流行文化,從萌芽發展到繁榮,都要經過自身的生長,在這個過程中,創作者始終都保持着自身的水準。對于他們來說,既不會因為民謠火就流俗,也不會因為不火,而不做這個東西。”
大衆眼中的爆火、出圈少不了資本的助推,唱片行業的發展,讓一些獨立音樂人能夠被大衆認知,過上更好的生活,“相比之下,大家在平凡生活中沒有放棄創作這一點,實際上更為難得。”
對于郭小寒來說,民謠的生命力要比想象中更強大。這也是為什麼二十年前,周雲蓬的音樂能夠受到歡迎,二十年後,依然可以在一檔綜藝中奪得冠軍。
更準确地來說,民謠不是不火,而是在穩定發展中始終壯大的狀态,它就像一首不老的歌,用内生的力量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而深處産業當中的人,也一直在傳遞着這種影響。
郭小寒在做演出企劃之餘,也會做即興音樂、實驗音樂的策展,用創新的音樂形式将演出做到校園裡、劇場裡,重新認知自我,“隻有不斷地去推廣,大衆才知道你是誰,你的音樂多厲害。”
陳鴻宇則又回到了線下的演出中,和年輕的歌迷、新老樂迷進行互動。每次演出結束後,他都會站在台上和粉絲合影,每一次現場演出形成的記憶碎片,不經意間又會成為他“博物館”中陳列的一角。
“民謠在路上”繼續發展的同時,盧中強又投入了部分精力到“新樂府”的演出企劃中。他希望通過更多跨界混搭的手段賦予中國戲曲、國樂更多的可能性,更多國際化的傳播和博得更多年輕人的喜歡。
“民謠在路上,我做了20多張專輯,新樂府我做了快43張專輯。”盧中強補充道。
在不被關注的時間裡,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幫助民謠繼續向上生長。而音樂人們也在高低起伏的變化中,繼續練好自己的基本功,接受所有的變化。
“時代在變,但民謠人的坦誠、真實、天真、敏感,始終不變。”郭小寒很喜歡蔣先貴的《金剛不壞大寶劍》,“每個人都有一款屬于自己的大寶劍,幫助我們在這個世界修煉。”
結語
盧中強雖然沒有辦法具體地定義民謠,但他記得一件很“民謠”的事情。
“民謠在路上”巡演期間,盧中強帶着樂隊來到了廣州大劇院音樂廳表演。演出結束後,盧中強滞留了一天,其他音樂人飛回北京,他至今清楚地記得,大家坐的是空客380。
登機時,馬條拍照向盧中強炫耀,“你看老盧,我們坐的是雙層飛機。”
沒想到的是,因為天氣因素,航班備降在武漢機場。當時現場滞留的人數特别多,場面比較混亂,老狼的樂手小彭突然拿出口琴來吹,山人樂隊也拿出了打擊樂,樂團中的人紛紛拿出自己的樂器,然後,沈慶開始抱起了吉他唱歌。
他們真的來了一場完全即興的、不插電的現場演出。這時候,機場很多人都圍過來看這場演出,并參與其中。有人往樂手的帽子裡放錢,還有人跟山人樂隊的小不點(樂手名字)一起跳舞。
“當天夜裡有關這場民謠在機場的演出在微網誌形成了一個傳播事件,我看到現場的大量照片之後,跟張恩超說了一句話,這就是我要的民謠!”
民謠發展的三十年,有高潮有平淡,在與民謠有關的争議、讨論中,郭小寒說,“相信民謠就好。不必懷念過往的時光,往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