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2017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郵發代号1-201
在中國古代,文學天賦的神秘與天才傳奇彙聚成文才尊奉的習尚,富有文才者由此被命名為“才子”,而創作力衰退、文思遲鈍、佳作難覓者也同樣要追根溯源于才,自六朝開始,批評界就将這種創作情勢的變化概括為“才盡”,“江郎才盡”便是其時最著名的典故。圍繞這個傳說,曆代引發了江淹之才是否盡,人之才是否能盡,是什麼因素影響妨礙了才的盡數發揮,維持才情活力的途徑是什麼等諸多話題。很多作家成名之後,創作難以為繼的現象也給人這樣一種感覺:作家的才華類似容蓄在器物之中的物質,随着滔滔不絕的發抒、年深月久的挹取,每一次創作都會形成一定的耗損,如此日漸消磨,終有一日會趨于腹内空空,這就是“才盡”。那麼才到底能不能“盡”呢?本文拟從才為何物出發,參照曆代有關文才的論述與文學實踐的經驗,揭開這一千年公案的謎底。(詳細論述參閱拙著《中國古代文才思想論》,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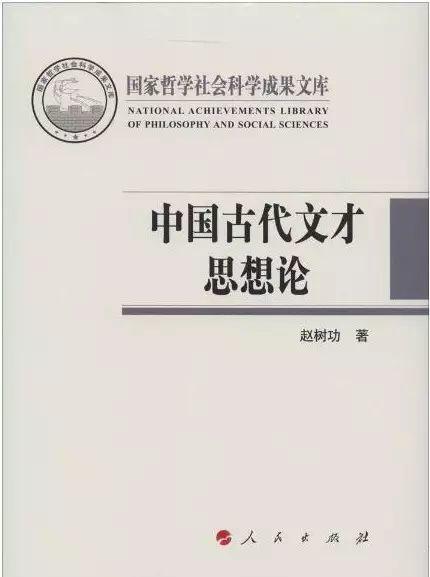
“才盡”說溯源
才是一個先秦時期已經成熟的概念。漢魏之際,随着人才甄選标準的變化與才性哲學的流行,這個概念成為那個時代文化的“關鍵詞”,并完成了其美學範疇化的轉型。有關“才盡”的傳說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誕生的。
文學史上最早的“才盡”傳說集中出現在六朝,分别涉及著名文人鮑照、任昉和江淹。
鮑照才盡說。《宋書·鮑照傳》記載:“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鹹謂照才盡,實不然也。”由于當時的皇帝自認為文才無敵,鮑照乖巧,惟恐不慎露才,顯曝君上無能,是以吟詩作文有意堆垛鄙言累句。時人不明就裡,謂之才盡。
任昉才盡說。《南史·任昉傳》雲:“(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雲‘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于是有才盡之談矣。”任昉博學,王僧孺曾比之為董仲舒與揚雄。時人所謂“任筆沈詩”,是說任昉之才長于散體文章,其中又以不甚講究才情的公文占很大比例;沈約之才則長于詩歌,既講求情感細膩又需要文辭、音韻的兼美。任昉不服,晚年有意棄其所長,欲與沈約在詩歌創作上一較高下。但才情所限,其詩用事過多,殆同書鈔。雖然如此,在一些同調者的刻意吹捧鼓舞下,任昉不僅毫無收斂,反而越發肆力于這種創作,才盡之論由此而來。
江淹才盡說。這個典故首見于鐘嵘《詩品》,其中雲:“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南史·江淹傳》所叙更為詳細: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雲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禅靈寺,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踬矣。又嘗宿于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後世著名的“江郎才盡”典故即是由此而來。以上“才盡”說皆是就文人而發的,結論的得出憑借各自作品所呈現的藝術風貌和水準,主要指向作家創造力較此前的衰退。當然,以上三人所謂“才盡”的表現略有差異:鮑照才盡不是客觀寫照,而是文士的一種韬晦之策。任昉才盡論略顯複雜。“任筆沈詩”的品鑒依據是當時的“文筆之辨”,其中的“文”被從普遍的、功用性寫作(當時名之曰“筆”)中抽離,賦予了藝術審美的身份,這是中國“文學”自覺曆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标志性理論成果。從“詩”(即文)、“筆”相異次元區分任昉、沈約,已經擺明批評界對任昉詩才不優的共識,在這種條件下,其拘攣補衲、掉弄書袋的詩歌寫作正是其本然之才的客觀展現,既然本來就未見卓異,是以所謂“才盡”在此更多指向的是其詩才不優的事實。隻有江淹才盡的傳說更接近一般“才盡”二字的本意,而且也成為三個事典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引發了曆代的關注與讨論,學者們見仁見智,論說紛纭,而其主旨最後集中于江淹之才到底盡還是未盡。
關于江淹的讨論,起初集中于江淹是否才盡,随後敷衍開來,逐漸聚焦于普遍意義的才到底能不能盡這個論題之上,并最終從江淹的個案上升為一個文藝美學論題。這個論題中包納着兩個主要的疑問:文才是否會因為頻繁運使而枯竭?文才是否會随着年齡而凋零?
關于“才盡”說的論争
有關才是否能盡的兩個主要疑問,曆來有着各自不同的回答。
文才是否會因頻繁運使而枯竭?持肯定意見者多如李邺嗣所論:“文人自用其才,亦如用物然,傾其所積而止。”(《耕石近草序》)錢謙益将其表述為:“生生不息者,靈心也,過用之則耗。”(《族孫遵王詩序》)這裡所謂“用”特指“過用”,即終日拈筆,喋喋不休;而“才盡”也具體指向以下三端:撓亂真氣,蹶僵美才,擾塞深思。
杭世駿則對此提出質疑。他首先讴歌才是天地間神妙之物:“乾坤有清氣,山水有清音,融結而為精靈,胚胎而為人物,衷之性情,根之氣骨,散之心脾,造化實鐘美于是,而幸而得之,則才之說也。”如此造化鐘粹者,正可“雕锼肝腎,涵泳飛躍,率意肆口,颠倒反覆而用之”,何曾有竭盡一說?至于某些“為之至于窮悴老病以死而不知厭,或責之或愍且笑之而猶不自悔”的“好之”者,其“铢铢積之,寸寸累之”的情态雖然的确彰顯了才盡之勢,但其實這種情勢與才盡與否毫無關系,因為他們本來就屬于“其為才也亦僅矣”的“無才者”。真正的才不可窮盡,是以杭世駿的結論是:“詩也者,用才之地,而非竭才之具也。”(《何報之詩序》)
相比之下,“文才是否會随着年齡而凋零”這一話題受到了更為廣泛而密集的關注,并形成文才無盡老而彌笃、文才有盡才随年衰兩個對立的觀點。
文才無盡老而彌笃的思想,與《老子》“大方無隅,大器晚成”的觀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苦其心志、空乏其身等人生必經磨砺之論有着一定的關聯。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之說,已經關注到了創作曆程與才華的關系。宋人對于杜甫之論頗為贊賞,是以其時論文才無盡老而彌笃、文人大器晚成者尤多。這種愈晚而詩文益高的現象,後人又稱之為“年益高,功益深”。如此持論的文人,多将文藝創作視為一生的修為,以循階而進為其必然的經驗,是以“中歲所為,或風格未成,波瀾欠老,皆它日遺恨”也便成為文人常态。所謂“它日遺恨”就是指曆代大家多悔少作的現象。有人問宋代王十朋自我今昔文章的優劣,王十朋雲:“新文之進予則不知也,但每閱舊文背必汗焉耳。”(《論文說》)潛台詞就是:才随年進,故能見今是而昨非。悔其少作集中表現于一些著名文人成名之後,大量焚其少作。吳熊和先生《宏觀的中介》一文曾關注這個現象:黃庭堅舊有詩歌千餘篇,中歲焚去近乎三分之二;陳師道自編詩稿,所列皆為三十一歲以後的作品;陸遊刊定《劍南詩稿》之際,四十六歲入蜀以前的詩删存僅有一百餘首。楊萬裡《江湖集自序》坦承:“餘少作有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
另一種意見為才随年衰,即文才随着精神血氣的衰微而逐漸頹靡不振。歐陽修《題青州山齋》講訴了自己如下創作經曆:
吾嘗喜誦常建詩雲:“竹徑通幽處,禅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為己有。于是益欲希其仿佛,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為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強?将吾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為終身之恨爾。
歐陽修遺憾自己難以追摹常建之作,分析原因有兩個:才有其偏限而不能勉強;年老才思衰退。雖然意存兩可,但這種自餒的揣測與其往昔自道《廬山高》等作堪配李杜甚至李杜也難以望塵的氣度已經大相徑庭。朱熹也持此論,他曾自言“人老氣衰文亦衰”;又稱晚年作文,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雲:“人之文章,也隻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朱子語錄》)三十歲在朱熹看來是一個分水嶺,其時血氣已定,文才也基本成熟,此後無大進境。大家碩彥尚且如此,碌碌者也就更加概莫能外了。
那麼,文才到底能不能盡呢?這就要從才的本義及其特征說起。
才的性能統一性、天人統一性與“才盡”說質疑
從文字訓诂考察,才的原始意義衍生于草木的存在狀态。對這個字的訓釋大約有兩個代表說法:
其一,表示草木生長的初始狀态。才的篆字作兩橫一豎,許慎《說文解字》釋雲:“草木之初也。”“|”的上面所貫之“一”為“将生枝葉”;下面的“一”代表“地”。才字既象形也會意,是植物生長剛出地面的形态。南唐徐锴《說文系傳》沿依此說,隻是将上面一橫解釋為“初生岐枝”。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贊成許慎的釋義,并進一步拈出其“凡始”、起初的引申義。
其二,代表樹木伐倒之後所呈現的本然質地。唐代李陽冰先有此說,宋末戴侗《六書故》引其言曰:“在地為木,伐倒為才,象其支根斬伐之餘。凡木陰陽、剛柔、長短、大小、曲直,其才不同而各有所宜謂之才,其不中用者謂之不才。引之則凡人、物之才質皆謂之才。”戴侗也主這一意見。李陽冰等的釋義是對象形“才”字的另一種解讀,尤其側重于“木”、“才”二字之間的形似辨析:生者為木,伐倒之後,斬除大木之旁枝根系則為才,斬伐之後最終顯示樹木主幹的本然質地性質,質地性質不同其用度也便相異,但凡能堪其用者皆可為才。如此既論性質,又兼用度。
以上對才字象形會意了解的不同,出現在不同的時代。許慎之說最早,應該能夠代表東漢之前關于才之本義的基本了解。唐人之說雖然後起,但同樣是從草木存在的狀态着眼,其“才”、“木”關系的考釋對于許慎的解讀具有一定的補充意義。
綜上所述,所謂才,本意是一個時間概念,由于它代表着初始、方将,是以不僅陰陽、剛柔、長短、大小、曲直、清濁等質地蘊蓄其中,未來的走向或發展趨勢同樣涵攝其中,“才”中也便有了“能”的意蘊,是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申其意為:“草木之初而枝葉畢寓焉,生人之初而萬善畢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蘊也。”才就是質地性質,就是質地性質之中透顯出的潛能。才、性本初密不可分,是以才或者性又被統稱之為“才性”。在古代學者看來,“命”、“性”、“才”的本意是一緻的,他們都是“天性”,馮友蘭也認為:“才是天生底,是以亦可謂之為性。”(《新世訓》)才的這種内涵定位,在戰國時代已經全面成熟。
考察古代哲學、美學、文字學的論釋,才呈現為如下兩個重要的特征:性、能統一性,天、人統一性。
先說才的性、能統一性。才的性、能就是才的質地性質與潛能,二者的統一性在許慎、段玉裁等對才的訓釋之中已經鮮明展現。主體實體性的質地性質,對主體未來的發展趨勢具有引領、支援或者預設功用,如此的潛能或潛在優長便涵蓄在如此的質性之中。具體而言:
首先,才有其分,這就是“性分”或“才分”。性分或才分是從才的關涉範圍、特征、程度約定而言的,其理論關注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其時孔子分人為三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所依托的便是主體禀賦。兩漢出于人倫識鑒的需要,于此相關的論述漸漸增多,或由修短言分,如《淮南子·修務訓》雲:“人性各有修短,……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或由品級定才分,如董仲舒承孔子思想,以為性有三品:聖人之性、中民之性、鬥筲之性;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列九等之序以别人才,荀悅《申鑒》于三品之中又各自分出上中下,直至曹魏九品論人法式等等皆是。修短或者品級關乎大小高下,如《論衡·案書》論稱“才有高下”“才有淺深”;《本性篇》亦雲“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
六朝之際,才分論已經進入文藝批評。範晔《獄中與諸甥姪書》曾自言“所禀之分猶當未盡”,他所謂“禀分”,即指其于著述、詩歌創作上的擅長。《文心雕龍》更是屢言才分。人才有其分,則意味着其基本的質性由此獲得相應的規定,彼此不同,各呈其面。
其次,才的不同質地性質彰顯為不同的潛能,這就是“性能”或“才能”。“才能”概念漸興于東漢,王充《論衡》之中已經有了成熟運用,如《書解》雲:“人材有能。”《程材》雲:“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深嫉才能之儒”“材能之士,随世驅馳”。劉邵《人物志》則專設“材能”一篇讨論才之所能與政事所宜:
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有消息辨護之能,有德教師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有司察糾摘之能,有權奇之能,有威猛之能。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
才能不同,能夠從事的政事從類型到大小也便有了差異,雖然備列“偏才”,但因其各有所能仍可謂之“一味之美”。
才有其質性,性有其潛能,但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古代有關質性、潛能的論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每每緻意于性、能的統一。較早論者如張衡《應間》雲:“人各有能,因藝受任。”“人各有能”是說人有各自不同的偏性或獨詣質性,它決定了因能擇業的基本原則。南朝梁際庾元威論書,直接擺明二者關聯:“夫才能則關性分。”後世論才,時常有人局限于能力一維,今天普遍的了解尤其如此,宋末戴侗《六書故》早就于此作出了反思:從禀賦而言,天之降才并不劃一,有着智與愚、賢與不肖的差異,這就是“性分”;如此性分最終所實作的成就,就是性能才能,但性能才能的造詣又必然受到性分的支撐與制約,二者密不可分。司馬光等辨析才德,以才為能,以德論性;二程以性出于天、才出于氣,存在才性相異的嫌疑。如此了解的話,才便成為智術、技能、勇力的代名詞,忽略了才能本乎禀性的基本常識。戴侗以上的質疑,是對脫離材質體性而僅僅以能力論才現象的矯正。
再看才的天、人統一性。如前所述,才的性、能統一之中的“能”是“潛能”,是未來造詣、成就的可能,它與實際的所能不可劃等号。如此質性的具備僅僅是性可以轉化為能的物質基礎與前提條件,其能否激活、能否機軸靈動不絕如縷則需要後天人力的持續投入,隻有這種質性與後天人力實作融合,潛質潛能方可轉化為實際才能。納入美學研究的才,正是這種天人統一的産物。其中的後天人事或人力,在古代哲學美學中經常被納入“學”的考察範圍,相容着讀書、實踐與思考的方方面面。
才這種天人統一性的理論發端同樣要回到儒家的人性思想。早期儒家的性善性惡之論雖然具有一定的沖突性,而從主體完善的手段來看,二者又不約而同地聚焦于後天人事。
孟子的思想可以概括為“複性”。作為性善論的代表,他在排除了人之不善非是才的罪過之後指出:盡才則可以為善。這就是盡才成性,盡才的過程便是學而習之、克己複禮、見賢思齊、三思而行等緻力于學的過程,盡才力學是主體完性成性的唯一通道,最終的境界就在自身,成性完性的過程便是自性的自我釋放與成全。
荀子的思想可以概括為“繕性”。作為性惡論的代表,他以為人性之中附着了原始的諸般欲望沖動,并非清澄無瑕,于是人便不得不通過“僞”——文飾、文化來實作自我的去魅,盡才力學由此同樣成為抵達性的完善的唯一通道,最終的境界超越了自身,性成其“僞”的過程在此也就是自性的彌補與陶冶。
綜上可見,學是德性完足、修美的唯一手段。性對學有着本質的需要,性隻有完足、修美始可最大程度地成其性能,《荀子·儒效》所謂“知而好學然後能才”就是這個道理。才的天人統一性由此奠基,也可以說,在性各有分的前提下,人力是使這種定分得以煥發得以圓足的終極政策。後來漢魏六朝文人繼之對才必待學而成能的道理做出了更為翔實充分的闡釋。
綜合才的性能統一、天人統一特質,我們可以對才作出進一步的描述:作為主體禀賦的描述性範疇,才不是一種單獨确立、個體運轉并發生作用的官能、功能或機能,而是對人性諸般包納性存在的指涉,它以主體禀賦質性的有機融結為基礎,通過人力的不斷參與實作心智結構系統的良性運動。是以我們可以把才定義為“主體禀賦性的完整心智結構系統與人力的統一”。這裡所謂“禀賦性的心智結構系統”包蘊豐富:諸如記憶、感覺、辨識、思維、情懷、聯想、歸納等機能的源泉盡在其中,作為才的根基,這種質性各有其分,不可變易;各有偏優,難以兼通。如此質性上的分野随之在後天的學習磨砺過程中逐漸形成術業所能所宜的不同選擇。對于文才(文學藝術之才)而言,它并沒有超越于一般才所具有的心智結構系統之外,隻是其中突出且具有決定作用的因素與常人相比有着容量或濃度的巨大差異,這個突出且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就是其于感覺、情懷、聯想等心智的獨到,多情而深情、敏銳而幽微的人格,構成了嚴羽所謂“詩有别才”之“别才”的根本。
事實上,所謂“才盡”是一個非常籠統含糊的表達,乍言之略似其實,細究之卻難以确指。從才的系統特征剖辨,對于一個作家詩人而言,作為其潛能發揮、用度施展源泉的“性”是穩定的,也可以說,其特定主體的心智結構系統的構成基礎、氣血基因的組合特質是穩定的,既不會因頻繁的運使而變異,也不會随着年齡衰老而萎縮。但這個“性”的性能——即才能呈示并非是一個持續穩定的狀态,就如同一株花草的生長,不是一顆優良的種子就能決定鮮花能否綻放,它的生長需要一個生态:水分、空氣、肥料、土壤以及周邊雜草的祛除等等,都對其生長有着重要影響。這其中有禀賦質性之中的相關機能是否靈動圓活問題,更有後天人力對于先天激發的力度是否充分問題。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性不可易,能不易續”。
“才盡”說本質:縱才不養則神疲,年進不學則思鈍
如上所述,所謂才盡實為心智結構系統良性運轉機制被破壞,而破壞心智結構系統良性運轉的,恰恰與引發“才盡”說的兩種表現相關:縱才而不養,年進而不學。仔細考察這兩個現象,有助于我們深刻了解所謂“才盡”的本質。
先看無所節制的縱才創作。對于具體的文學創作而言,我們從諸般才子傳奇之中聽慣了所謂興酣筆暢、口吐蓮花的戲說,反而對個中三昧所知不詳。事實上,所謂孜孜不倦無所止歇的寫作往往與苦累相伴。如東漢桓譚《新論》記載揚雄的自述:“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賦,為之卒暴。思精苦,賦成,遂困倦小卧。夢其五髒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揚雄非是不才者,但每逢皇帝興來(不是自己興來)則必奉诏作賦,其困頓可想而知!桓譚引發的思考是:“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王充的勤奮為後人屢屢稱道,《後漢書·王充傳》載其為著《論衡》,“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如此刻苦的回報是成就了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的皇皇巨著,但也換來了“年七十,志力衰耗”的慘淡,即使有“繡虎”與“才高八鬥”美譽的曹植,也有創作不辍而“反胃”之論(蕭繹《金樓子·立言》)。
劉勰認為,從養生衛氣角度而言,如此不明為文之理,“精氣内銷”而“神志外傷”,“銷铄精膽”而“慼迫和氣”,最終結果隻能是“秉牍以驅齡,灑翰以伐性”——寫作成為戕害生命的罪魁禍首。就創作實績而言,無所節制以應文債,左支右绌抛灑才情,“神疲氣衰”必然反映到“文思”之上,落下“文思浮易”的惡疾:起初是“應付供給語塵集楮墨”,通套語彙随處可見;久之“手滑”,便“不耐沉思”,膚淺輕易慣了,反而以覃思深識為畏途;最終必然歸結于才力,“人之才情精神亦複有數,多應酬以分其力,後遇大好題,作之反無力,不得精彩”。文思是文才落實于創作實踐的直接表現,文思浮易不耐沉深,于大題好題無力擔荷,這就是“才盡”之所指(毛先舒《與方渭仁論文書》)。
但如此所謂“才盡”并非才的窮竭與永久喪失,隻是文思的麻痹,它可以重接本源、再振活力。文才能夠斂蓄涵養,則最終激活的是文思鋒芒,有文思的泉湧淋漓,便無所謂“才盡”。劉勰在指出沉疴之際也指明了這一點。古人所謂“慎入慎出”、“取精多用之少”,所謂“才性貴重”、“文德敬慎”,宣揚的皆是這種文思的斂蓄涵養之道。
當然,劉勰等人讨論的養才接近于道家衛生意義的養氣,文藝事業之中所涉及的涵養之道遠不止于此,正如陸遊所雲:“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禦之,淫于富貴,移于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愧,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讵可得哉?”(《方德亨詩集序》)陸遊所論之養更側重于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是配義與道又融合了生命之氣的産物。沒有這種内在志氣的支撐,再強壯的軀體、再鼓蕩的血氣熱情都可能難以轉化為昂揚正大的文思。
再看年進而不學者的創作情勢。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才老彌笃說與才随年盡說的内涵,除了部分個體批評的主觀,會發現以下特征:在批評者眼中,排除情懷深淺、興會有無、體制大小、精神郁暢等偶然因素的影響,很多優秀文人之是以被認為才并未随年而盡,是由于其老不廢學;另外一些文人之是以被視為才随年盡,恰恰因為恃才而不學,其老境頹然,不是才性本身的變化,而是才性發揮作用的生态系統之中維護其生機的後天努力遲滞甚至停滞了,由此造成本自性能統一、天人統一的文才喪失了煥發活力的源泉。
從才非随年而盡之說來看,人力的持之以恒可以成就創作者的功力,可以鍛煉作者的識力,可以積累熟谙文藝的法度利病,可以陶養作者的志氣,可以蘊藉作者的德性情懷,最終由此人力的不倦而抵于神知心靈。于是那些後人眼中才随年進的大家,諸如韓愈、歐陽修、蘇轼、黃庭堅等等,沒有一個不是學随年深的典型。
而對于那些力持才随年盡之論者來說,其所謂才盡,并非才性本質發生了蛻變,而是激發才能現身的機制中辍,說白了,“才盡”實際上是“學盡”的必然結果。曆代關于“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現象的反思皆已警示後人:學而不倦是才性成就才能的根本所在。王安石的《傷仲永》可為其典型:“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于材人遠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受之于天的才性必待受之于人的學習輔助,否則質性隻為質性,永遠不可能轉化為才能,間或有所呈露,終難大放光芒。
出于對以上道理的深刻理會,曆史上很多文人在涉及一些他們眼中才随年盡的事例時往往都預留了一個療救的方案,這就是“學”。無論是否贊成才随年盡,“學以啟才”的思想在當時與後世皆具有代表性,“舍學而用才,其才易匮”是以成為規誡才人的金玉良言。
當然,這裡所謂的“才盡”依然是一個籠統表述,一如鑽砺過分導緻的才盡實指文思衰靡,才随年“盡”或者“不盡”所指的同樣不是文才的整體系統,而是“才思”——出自個體文才禀賦的文思。早在唐代,孫過庭《書譜》就有如下文字:“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作者将老而彌笃者明确定位于“思”——即才思愈老愈貫通。凡因血氣變化而有順滞、有通塞、有敏遲之變者,皆在此文思。既是文思或才思問題,何以便被命之曰“才盡”呢?原來,“才”作為一個模糊性、系統性的概念,由于不同語境的表達需要,具體文獻之中一般不會全面覆寫其本然意涵,而是在才性、才能之間遊移,經常兩端分表,有所側重;加之習慣性意會對于才意義建構、表達的影響,有時甚至會模糊其體與用的範圍,以用論體、以點代面,比如具備良好的記憶力、學習能力從古至今皆命曰有才,但實際上這隻是構成才的心智結構系統之中的質性之一,不是才的整體與全部質性的展現。雖然如此,這種關于才的表述習慣已經化入了漢語的構詞法則,諸如才情、才識、才藻、才學、才力、才器、才氣、才思等範疇,皆可以視為主體之質性、才性通過其情懷、識力、學養、藻彩、德器、氣勢、文思的自我現身,反過來,古人也便經常将富有情懷、識力、學養、藻彩、德器、氣勢、文思之能力等視為有才。由于以用論體、以點釋面的表達傳統,文思的鈍滞、伏匿便被名正言順地表述為了“才盡”。
人工努力并不能夠改變才的天賦,但通過人工努力可以實作本然才力的盡量釋放。有鑒于此,明代錢一本曾指出:
一粒谷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也。(《明儒學案》)
文中的“盡其才”不是指才能消失,而是盡數發揮之意。所謂“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意在警醒世人不可徒恃聰明而不盡人事。論才,最終回到了學而不倦之上,就這個意義而言,明人所謂“天下豈有寡學之才”的結論是頗有見地的。
(作者為甯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