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教授謝泳過去以發掘學人舊事著稱,近年來則緻力于箋解陳寅恪詩。
讀過幾篇就知道,謝泳箋陳詩的方法是這樣的:先看某首陳詩的寫作時間,再查閱同一時間段有什麼引人注意的事件發生,然後就可以論定陳詩與某事有關。
這種方法的讨巧處在于,世間萬事萬物固然紛纭,然而如果非要在它們之間找出一星半點相關性不可,卻也不難。
不能不說這種箋釋方法非常大膽。但是否行得通呢?
且舉最近上海書評所發謝泳《新解》(澎湃新聞2022年4月9日釋出)一文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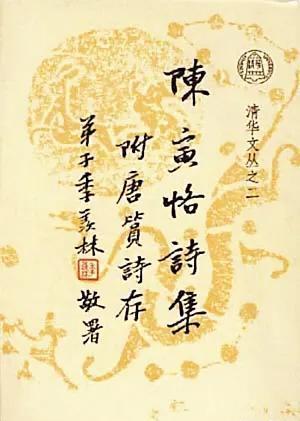
陳寅恪詩集
陳寅恪寫于1956年的《從化溫泉口号二首》全詩如下:
火雲蒸熱漲湯池,待洗傾城白玉脂。可惜西施心未合,隻能留與浴東施。(陳氏自注:醫言患心髒病者不宜浴此泉)
曹溪一酌七年遲(“遲”字,謝泳引用作“休”),冷暖随人腹裡知。未解西江流不盡,漫誇大口馬禅師。(陳氏自注:餘日飲溫泉水一盞)
我以為,按字面之意,這兩首詩就是陳寅恪浴溫泉後的一時遊戲之作。第一首因為心髒病不宜溫泉,是以陳和患有心髒病的妻子開了個玩笑,将其比為“西施”而自居為“東施”。陳寅恪之妻唐筼一生體弱,生長女時因心肌炎誘發為心髒病,幾乎殒命,這在多部陳寅恪的傳記資料中都有記載。第二首則是自嘲。禅師馬祖曾言“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作者借此話頭說自己每天飲溫泉水一盞,徒然以馬祖自誇,卻殊不知西江水是流不盡的。
陳寅恪與家人合影
但衆所周知,中國詩歌有興觀群怨的傳統,字面之外往往有深意存焉。
在謝泳之前,胡文輝等人解釋這兩首詩,最多敢猜與當時的政治文化氛圍有關。謝泳的新解則大進了一步,指實為具體的人和事,認為是指章士钊赴港之行。
謝泳的主要論據和論證如下:就在陳寅恪浴溫泉并作詩的同一年,章士钊曾奉命赴港,為兩岸和平奔走,途經廣州時曾去過從化溫泉,也曾寫過一首詩;章詩有“獨為凝脂謀”的詩句,而陳詩說“待洗傾城白玉脂”,是以謝泳“推測陳寅恪應當知道此詩”,進而認定,陳詩暗示了章士钊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可惜西施心未合,隻能留與浴東施”雲雲,則是陳寅恪對兩岸關系的判斷。
新解石破天驚,可惜論據非常薄弱,論證則近于荒謬。
先看時間。如果陳詩系因章士钊赴港而發,必然是章浴溫泉和賦詩之後。
謝文中說:“章士钊香港行在1956年3月”。其實這年春天,章士钊是否真有赴港之行,并無定論,為章士钊編年譜的朱銘即對此表示懷疑,因為他在查閱了金毓黻、許寶蘅、顧颉剛等人日記之後發現,這一年3至5月,章士钊都有在京的記錄(參見2013年《三聯生活周刊》所刊《是誰将《論再生緣》帶出海外?》一文)。
現在對此姑且不論,先認可章士钊在1956年3月的确有過香港之行。但陳詩寫在什麼時間?胡文輝認為是1956年2月,依據是當時陶鑄曾邀廣州部分教師到從化溫泉參加知識分子座談會,陳寅恪夫婦出席。
胡文輝所舉的這條論據無法否定,那麼2月的陳寅恪怎麼會未蔔先知地為之後的章士钊之行而賦詩?
為了自圓其說,謝泳的解釋是:“在不确定具體月日的情況下,期間有幾個月的時差,推測陳詩作于陳章會面後,應在合情合理範圍。”意思是雖然陳寅恪浴溫泉是在1956年2月,但不代表這兩首詩一定是2月所作。
這種推測真的合情合理?謝泳很可能忽略了舊體詩的一個基本常識。
陳詩标題曰“口号”。何謂口号?古人又稱為“口占”,表示詩人因事生感、随口吟誦,是以口占體都是臨時起興之作。
既然這兩首詩名為“口号”,那麼就一定是陳寅恪2月浴溫泉時的一時興起之作。
再來審視謝泳從章、陳詩中找到的唯一“内證”,看章詩的“凝脂”和陳詩的“白玉脂”究竟有多大的相關性。
泡溫泉想到楊貴妃想到白居易的“溫泉水滑洗凝脂”,這于中國文人豈不是非常自然的聯想?難道陳用“白玉脂”還一定是因為其事先看到了章詩?另外,章士钊詩雲“獨為凝脂謀”,這是在抨擊舊時代溫泉隻能為貴妃等顯貴所享受,而按謝泳所釋,陳在看過章詩之後,有意用“白玉脂”一詞來暗示章的特殊身份,考慮到二人交好且互有唱酬,這怎麼可能?
章士钊自書詩作之一
“詩無達诂”,沒錯,但是不代表沒有束縛。寫舊詩的人必須遵循那一套成熟的句法、章法等規矩,解詩者當然可以發揮奇思妙想,但也一定要在那一套“規矩”之内。
陳的第二首詩,先說“曹溪一酌七年遲,冷暖随人腹裡知”,這分明是寫自己在廣州生活已有七年,那麼後面兩句“未解西江流不盡,漫誇大口馬禅師”可解為一般的生活自嘲,也可能借自嘲的形式暗含了作者對時政的某種觀感。但無論哪一種,“未解”“漫誇”的主語都是作者自己,而不會是另一人。
在一首絕句裡,前面兩句寫自己,後面兩句固然可以跳躍到他人他事身上,但卻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即要麼字面上有過渡,要麼意思上有一定關聯。而這首詩裡顯然缺乏這一條件。
陳寅恪的這兩首詩究竟有無字面之外的深意,深意為何,平心而論,除非召作者本人而問之,沒法得到确解。可見在謝泳之前的胡文輝等人同樣有猜謎的嫌疑。然而由于是比較寬泛的闡釋,也許猜錯,但畢竟還有猜對的可能。
而謝泳所謂“新解”猜對的機率又有多少?坦率地說,如果謝泳的這一套箋詩方法能夠成立,整個中國詩歌史恐怕都要徹底改寫了。
打個比方:某年某月,蘇轼居家飲酒樂甚,欣然賦詩一首,但後來解詩者查了皇帝實錄,發現相近時間段皇帝也曾飲酒,遂認定蘇轼此詩實際是在影射皇帝縱酒荒淫。問其依據,則理直氣壯答曰:兩件事中不都有酒嘛!如此解詩,豈非笑談?
(本文原題《 匪夷所思的“新解”——謝泳《新解》商榷》,作者黃三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