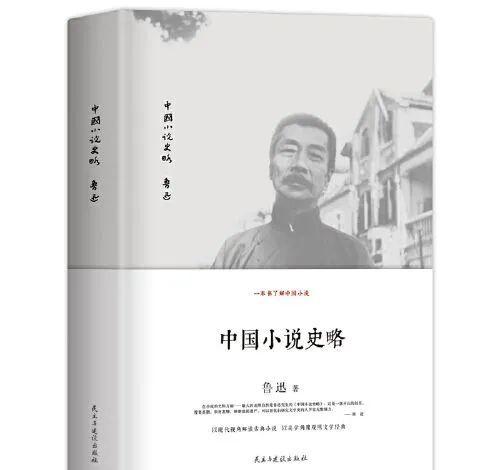
《中國小說史略》是由現代文學家魯迅著作的第一部系統地論述中國小說發展史的專著。這部專著從遠古神話傳說講起,至清末譴責小說為止,完整地論述了中國小說的起源和演變,精當地評價了中國各個曆史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小說作家和作品,深刻地分析了前後期小說之間的内在聯系。
作者在論述中國小說的發展演變時,不僅從文學本身尋找其進行的線索,而且特别注意把小說這種文學現象放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之下,從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以及社會風氣、學術思想等對小說的影響來進行分析,并從其互相關系、作用與反作用的角度,闡明了中國小說發展的規律。其見解精辟,材料豐富、線索明朗而清晰,給中國小說的曆史發展作了言簡意赅的總結。專著取材詳實,分析精當,結構謹嚴,脈絡清楚,内容豐富,填補了小說研究史上的空白
内容概要
全書共二十八篇,書後附有《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一文,是作者1924年7月在西安講學時的講稿。《中國小說史略》對中國小說的發生和發展過程進行了系統的探索。它從遠古的神話與傳說起溯,其後依序論述中國小說發展史的各個階段,從漢代小說、六朝小說至唐宋傳奇,從宋代話本及拟話本、元明的講史小說、明代的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拟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至清代的拟晉唐小說、諷刺小說、人情小說、狹邪小說、俠義及公案小說,直至清末的譴責小說。魯迅運用唯物主義觀點和科學的比較方法,對小說的産生、發展和變遷,對曆代小說興衰變化的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原因,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分析評價,以及各類小說的思想藝術特色,都做出了概括和總結。
中國小說曆來不為文人所重視,不登大雅之堂。作者将上古神話傳說視作魏晉志怪小說的本源,認為小說至唐代有一個較大的變化,到宋代又有一個變化,志怪多欲取信于人,文辭也變得平實,傳奇則拟古而無獨創。宋以後白話小說蔚為大觀,文言的拟晉唐志怪傳奇,也有續作,同時也論述了各類題材小說在近代的發展。
具體地說,該書第一篇《史家對于小說之著錄及論述》,征引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等書目,說明小說之名的起源及曆代對小說的分類與态度,闡述曆來輕視甚至敵視小說的“史家成見”的由來,極力鼓吹小說的重要地位。其餘27篇對中國小說的發生、發展過程進行了初步勾勒,先是追溯遠古神話與傳說,其後論述漢代小說、六朝小說、唐宋傳奇、宋人話本、宋元拟話本、元明講史、明代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拟話本、俠義小說、公案小說及清末譴責小說。其中第二至四篇考述從上古神話傳說至魏晉問假托漢人所撰各種神仙傳記的小說成型史。第五至七篇研究以《搜神記》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說及《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第八至十篇論述唐人傳奇與彙輯各種故事逸聞的“雜俎”。第十一至十三篇考論宋人志怪小說、傳奇、話本與拟話本。第十四至二十一篇評述元、明講史,明代神魔小說與人情小說,附論明代拟宋代市人小說及清人選本與續作。第二十二至二十八篇論析清代拟晉唐傳奇志怪、諷刺、人情、以小說見才學、狹邪、狹義與公案、譴責等七大類型小說。
時代背景
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地位卑微,曆來被視為小道末流、“街談巷語之說”,不登大雅之堂,搞學術的人也不屑于去碰小說。17世紀的金聖歎說《水浒》的文學價值不下于《史記》、《戰國策》,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這一眼光堪稱卓然,但在他那一時代,像他那樣的怪傑絕無僅有。小說的巨大影響力與它在學者心目中的地位絕不相符,反差漸漸到了讓人無法忍受的地步。于是近世梁啟超倡“小說界革命”,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進而把小說擡到一個高得不能再高的地位。即便當時寫小說的人多了,人們也開始重視小說了,但對中國曆代小說的梳理、評述和研究情況卻微乎見微,更遑論專門的中國小說發展史的寫作。
基于這樣的原因,前此無人對中國小說史進行系統研究,該書《序言》開宗明義地說:“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後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于小說仍不詳。”作者卻自幼喜歡小說,受梁啟超等人重視小說功用觀的影響,大力翻譯、研究域外小說,緻力于古代小說的輯佚與整理,決心改變小說無史的現狀,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裡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
創作曆程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作者魯迅就開始了對古代小說的辨僞、輯佚及書目的整理,“正訛辨僞,正本清源”,先後輯校完成了《古小說鈎沉》、《小說舊聞鈔》及《唐宋傳奇集》。《中國小說史略》中所用的資料,就是從以上著作中采撷而來的。《古小說鈎沉》輯校唐以前殘存古小說凡36種,涵蓋了《中國小說史略》從第3至第7篇的主要材料,工作耗時3年,魯迅閱讀了大量古籍,抄錄了大小6000張卡片。《小說舊聞鈔》輯錄宋以後小說41種,參考了明清時的93種書籍凡1570卷。《唐宋傳奇集》從輯錄到出版曆時15年,内收唐宋小說45篇。作者魯迅耗費了大量時間系統地整理古小說資料,作者曾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方困瘁,無力買書,則假自中央圖書館等,廢寝辍食,銳意窮搜,時或得之,瞿然而喜。”(《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
1920年,作者魯迅應邀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授中國小說史,他把講義油印出來散發給學生,是為《小說史大略》。《中國小說史略》便是在《小說史大略》的基礎上修補增訂而成,在一兩年的時間裡,從最初的17篇擴大到26篇,題目也改為《中國小說史大略》。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正式出版,分為上下兩卷共28篇,題目也正式定為《中國小說史略》。
作品影響
作者首次從文體演進的角度,勾勒了中國小說發展的曆史程序,對中國小說從醞釀、發生、發展到成熟的過程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撰寫出了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小說史,填補了小說史研究的學術空白,具有學術開拓性。
首次對中國古代小說全面地進行了類型研究,進而開創了小說批評的新模式。《中國小說史略》對宋代及其以前小說的分類并無太多的新意,基本沿襲了古人的說法;他對小說類型的新設計主要展現在元明清時期各類小說的劃分與界定,如元明之講史,明代之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拟宋市人小說,清代之拟晉唐小說、諷刺小說、人情小說、狹邪小說、俠義小說、公案小說、譴責小說等,這些名稱迄今沿用。
對每類小說的淵源與流變進行了系統地考述。如第二十六篇關于狹邪小說的分類與源流、第二十八篇關于譴責小說的理論界定與例證闡釋,即為顯例
正面評價
胡适:在小說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析别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的精力。
郭沫若: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璧,不僅是拓荒的工作,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的成就,一直上司着百萬的後學。
蔡元培:著述最謹嚴,徒非中國小說史。
馮至:這門課名義上是《中國小說史略》,實際上是對曆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
阿英:《中國小說史略》的産生,不但結束了過去長期零散評論小說的情況(一直到“五四”前夜的《古今小說評林》),否定了雲霧迷漫的“索隐”逆流(如《紅樓夢索隐》、《水浒傳索隐》,以及牽強附會的民族論派),也給涉及小說的當時一些文學史雜亂堆砌材料的現象進行了掃除(如《中國大文學史》)。最基本也最突出的,是以整體的、“演進”的觀念,披荊斬棘,辟草開荒,為中國曆代小說,創造性的構成了一幅色彩鮮明的畫圖。
陳平原:迄今(2000年)為止,小說家之撰寫小說史,仍以魯迅的成績最為突出。一部《中國小說史略》,乃無數後學的研究指南。
鄭振铎:我在上海研究中國小說完全像盲人騎瞎馬,亂闖亂摸,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減少了許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中國小說研究的基礎。
蕭相恺:迄于今(2002年),還沒有一部真正從整體上全面超過《中國小說史略》的著作出現。
錢玄同:“此書條理明晰,論斷精當,雖編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中國小說史出現。他著此書時所見之材料不逮後來馬隅卿(廉)及孫子書(楷弟)兩君所見者十分之一,且為一兩年中随編随印之講義,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實可佩服。”
(日)增田涉:受此書(《中國小說史略》)刺激或啟發,不斷出現中國小說史的新發現和新研究,原著在中國小說研究上可稱為是劃時代的。
不足之處
胡适:論斷太少。
劉文典:魯迅不懂佛學,更不懂印度學術,是以他把中國的小說源流說不清楚。
劉揚忠:“總的看來,魯迅對中國小說曆史變遷,偏重于從政治文化背景上去尋找原因,而忽視了藝術形式自身發展的原因和其他文化形态對小說藝術的影響。
王平:此書的确有應補阙拾遺及辨訛疏證之處,如說《聊齋志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似乎并未辨明《聊齋志異》與六朝志怪的本質差別;再如對《水浒傳》繁本、簡本孰先孰後的辨析似乎也存有疑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