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錦池太累了。他的仙逝,是上天不忍,招呼他小憩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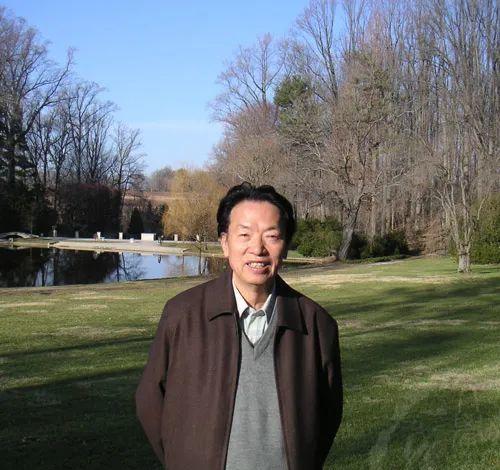
張錦池先生
從2020年9月27日17點55分以來,學生們親友們的懷念文字已足以彙編成書。那是張錦池本傳,是正史。我的瑣憶,是雜記,是對本傳的零落鑿實的注釋。
忝為大師姐
錦池與我和陶爾夫畢業于同一所大學。同系,同專業,同師父,同樣幸運地聆聽了五十年代前期院系調整後彙聚到北大的二十幾位老北大、老清華、老燕京、老中山、老科學院文學所國家級文史大家系統缜密的課堂講授,又先後遭遇了渴望讀研卻暫停招研的教育氣候,還先後滿腔熱血,投身邊疆,在黑龍江兩所省屬院校任教,深深植根在美麗富饒卻并不富裕的黑土地上,嘔心瀝血,至死不離不棄。
錦池與我也有顯見的不同。
這不同,不是指我比錦池早入學四年,且癡長一歲,而是說,論天賦,論志向,論勤勉,論學術成就,即我與錦池的生存狀态,相去甚遠。我類似金庸、古龍筆下恪守傳統、尊師憐才、功夫正宗卻謹慎拘泥的看家女徒,錦池則是生機勃發、不懈進取、挑戰自我、獻身江湖的少年精英。
是思想自由相容并包的校訓,把兩個不同性情的人绾結在一起的。
劉敬圻教授
我第一次認識錦池是在1964年聯考評卷的一次大型對話會上。那年的作文題目是《幹菜的故事》,給考生提供材料,讓寫一論說文。
閱卷開始的第一天,複查(顧問)組發現,在掌握評分标準上出現了嚴重分歧。于是便召集全體閱卷人會議,以同一張考卷為例證,展開對話。那份作文卷的最高分是90多,具體分數記不清了,但90分以上是确鑿無疑的。閱卷人恰恰是哈師大青年助教張錦池。
最低分是50分左右,也不記得具體數字了,但不及格而且遠離及格線也是确鑿無疑的,閱卷人是另一高校的青年教師。對話中,錦池毫不掩飾他的銳氣,對這份作文的認知能力和文字水準贊賞不已。給了低分的閱卷老師也認為考生的文字能力不錯,但整篇文章有否定三面紅旗之嫌。對話中還出現了第三種第四種意見,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試卷被送到沈陽“東北三省評卷指導小組”(那個年代,有這樣的臨時性機構),結果是指導小組給予近90分的成績,并提出如何恰切把握評分标準的幾點要求,讨論就此結束。
張錦池先生青年時期
正是這場讨論,我才知道哈師大新來了一位校友,教齡不過一年。也是第一次見識了這位校友善于思辨勇于堅持的張力。
我與錦池第一次晤面的時間地點緣由統統不記得了,隻記得進入中老年之後,錦池在輕松愉快的場合中,經常重複下面一段話:
大師姐第一次看到我就用質問的語氣說,你是張錦池啊,聽說你很傲?我回答她說,要看對方的眼睛長在哪裡。如果長在這兒(指着自己的眼睛),我一點也不傲。如果長在這兒(指着自己的額頭),我的眼睛就長到天靈蓋上去了。
這段話,像警句似的,被學生收進《張錦池教授語錄》中去了。其實,數十年的往來足以說明,錦池的傲,是性格亮點之一。他很懂得尊重一切人,不說硬話,不說閑話,不說大話,不說胡話;他更努力踐行自尊自重自愛自強的古訓。他能恰到好處地把握個中分寸。
《張錦池先生八秩稱觞集》
“和而不同”“美美與共”
錦池喜歡講述兩個故事。
其一,他常常以無比崇敬的口吻,複述他至為崇拜的吳組缃、何其芳兩位前輩學者,圍繞薛寶钗的階級階層定位互不妥協徹夜舌戰,然後愉快地共享吳師母美味早餐的經典佳話。吳何兩位恩師的風格,正是錦池對朋友之間師生之間美好學術關系的憧憬,那便是:和而不同,美美與共。
錦池知道我喜歡吳先生的性格,喜歡聽吳先生講課。吳先生因公出境的時候,總是請何先生代課,而且一旦返校,重登講台,必定幽默地說,何先生向你們散布了什麼毒素?我來肅清一下。同學們哄堂大笑。
錦池也清楚地知道,我對吳何兩位先生的研究思路一向兼收并蓄,各美其美。
《史詩紅樓夢》,何其芳著,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
隻是在個别藝術典型的解讀方法上受何先生影響較大。這種兼收并蓄、美美與共的接受習慣,與1956年的燕園氛圍息息相通。
1956年,北京大學創造性地恭請了吳組缃何其芳兩位先生共同開設《紅樓夢》系列專題講座。把“和而不同”同中有異的學術見解和研究方法清澈磊落地傳遞給學生。一時瑜亮(同學們興奮的把兩位先生比喻為周瑜和諸葛亮),神采飛揚,氣薄雲天,頗具震撼力。燕園學子對吳何兩位先生的高貴境界,代代相傳,至今神往。
錦池1958年入學之後,自會通過各種管道,特别是吳組缃先生課上課下的學術啟蒙中,熟知了當年吳何兩位摯友之間課堂論辯各抒己見的故事。他不厭重複且樂在其中的傳遞這個美麗的故事,正是提醒自己,提醒學生,千萬記住吳何兩位前輩。記住他們的做人品質,記住他們的治學風尚。無論為人為學,都要做堂堂正正的人。
《紅樓夢的藝術生命》,吳組缃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錦池熱衷傳播的另一個故事是凡人瑣事,是哈師大中年以上的教工耳熟能詳的傳奇。當事人是錦池早年的鄰居,一對善良和美的夫妻。
這裡用得上那句老話,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鄰居家的不幸竟然來自顔值。他倆的長相有點“困難”,以緻讓他們對生兒育女充滿壓力,唯恐兒女的模樣不能适應這個看臉的時代。
誰能想到,這對謙恭到自卑的夫妻,孕育出一個白雪公主般的女兒,讓他們像祥林嫂一樣,逢人便說,親生的,親生的。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個童話世界賜予的女嬰長到也會用套話寫作文的時候,更加出落得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人見人愛了。
講到這兒,錦池都忍不住點題:可見,基因,不決定一切。它在遺傳過程中産生變異。
盡管比喻是蹩腳的,鄰居的故事還是有啟發性的。即使從單純承傳的角度講,也可以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做學生做學問就更有能動性了。
任何不夠完美的前輩身上,你都可以發現優質的東西。善于選擇的人可以把老師們的優質元素吸納到自己的知識庫中,揚長避短,博采衆長,點石成金,出類拔萃的新生代就有望脫穎而出了。
一次走心的談話
大約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與錦池有過一次十分走心的對話。主旋律是研究方法。
錦池以調侃口吻坦率地問我,大師姐不少文章的标題和行文中,總是“補論”“補論”的,我怎麼覺得你的補論,似乎是針對我呢?
我不覺得突然。也模仿他的口吻誠實地回答了他。我說,平時你總說大師姐是你的知音,你的知音原來這麼小家子氣?吭哧癟肚一兩年才炮制一篇文章,竟然是為了對付你啊?那豈不是太耗費光陰?錦池不由得笑了。
我拽着錦池的思路,與他共同捋了捋我寫作那些“補論”的時間表。讓他知道,我不是不想承繼與模仿吳何兩位恩師的風範,把我與他在研究方法上的大同小異梳理出來,公之于衆。但我們好像還沒有這種底氣吧,沒有足夠的資曆這樣做。再說,那些“補論”真的沒有一篇是被錦池的見解激出來的。
《明清小說補論》(增訂本)
比如《宋江性格補論》是被我們仰視的李卓吾《忠義水浒傳叙》中一個結論引發出來的。《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曹操性格》是被“聖人”魯迅的一句話引發出來的。“林黛玉補論”(《林黛玉永恒價值再探讨》)是被我們喜愛的前輩大家何其芳先生《論紅樓夢》中的一個見解引發出來的。
《薛寶钗一面觀及五種困惑》(也算補論吧)是想寄給吳組缃先生審閱的,吳先生曾說過要為薛寶钗落實政策,我想請教吳先生,這麼寫,算不算落實政策?但膽怯,惶恐。不是怕自己挨罵,是怕吳先生生氣傷身體。于是直接給《紅樓夢學刊》了。
每一篇補論的誘因和由頭,都在每一篇的開頭,各自指名道姓毫無遮攔地供出來了。錦池有空,也可以撥冗再翻翻看。
錦池不時地插話,或質疑,或補充。越交流越坦誠越興奮越透明甚至放肆了。
我順手拿出來不久前錦池給我的新作《巧姐漫議》手稿,贊歎說,這篇大文思路新巧流暢,格調也清雅别緻。你有沒有輕快愉悅的感覺?(參見《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2輯後記)
《紅樓夢考論》
錦池說我轉移了話題。
他談興尚濃。說讨論研究方法,是個大工程。我們再找一個大塊兒時間,繼續磨牙。
我和錦池在“自由思想,相容并包”校訓的勉勵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和諧互補了近四十年。
三次“首屆”紅樓夢研讨會
20世紀最後的20年間,哈爾濱師範大學先後主辦(或承辦)了三次大型紅樓夢研讨會。且均為“首屆”。為中國紅樓夢研究史留下令人贊歎令人驚喜令人仰視的三座豐碑。張錦池的心血灌注其間。
1980年7月,在結束“四人幫”橫行之後的那個科學的春天,在哈爾濱松花江畔的友誼宮,舉行了全國首屆紅樓夢研讨會。這是一次莊嚴鄭重的大會。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和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全力支撐着這次會議。
會前,文學所與紅研所各自派出博學笃行的資深中青年學者鄧紹基、劉世德、胡文彬等與哈師大校系主管上司和張錦池一道,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四樓和二樓會議室内,作精細周詳的準備工作。并成立了“首屆全國紅樓夢研讨會籌委會”。
哈爾濱國際紅樓夢研讨會合影
錦池是籌委會重要成員,也是落實、組辦、主持此次研讨會的重要踐行者。閉幕式上鄭重宣布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推薦北大教授吳組缃先生任首屆會長(後因身體原因堅辭)。
時過六年,1986年6月,依舊在哈爾濱友誼宮,哈師大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聯合舉辦了中國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讨會。由馮其庸任會長的中國紅學會為此次會議成立了由各方相關人士參加的籌委會。中國大陸,港澳台,境外七個國家的一百二十餘位代表出席了研讨會,送出論文一百一十餘篇(是研究會最大亮點)。
會議期間,同步展示了三項精美的“盛宴”:紅樓夢版本與文獻文物博覽會;紅樓夢藝術節;紅樓夢講習班。盛況難再。
錦池的角色定位如下:籌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研讨會中外兩主席的助理,藝術節組織委員,講習班特邀主講人。自然是第一忙人。
十年以後,1996年1月,在台灣紅學家熱心推動下,哈師大主辦了“乙亥年海峽兩岸紅學研讨會”。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盛會。地點依舊是哈爾濱,但會場卻選擇在遠離松花江的哈爾濱西南地區,因為,松花江兩岸到處矗立着冰燈和雪雕,簇擁着大江南北長城内外前來領略冰雪節的歡快遊客。
張錦池先生在乙亥年海峽兩岸紅學研讨會上發言
台灣學者建議在隆冬季節相聚,自當與冰雪節有緣,而年長學者的應邀北上,無疑是《紅樓夢》自身的永遠魅力了。如著名小說家王蒙,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馮其庸,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希凡,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文學及曆史系教授周策縱等。他們不僅不畏嚴寒,而且以情趣盎然的學術演講,豐富和溫暖着每一位與會學人。
作為東道主,錦池的服務精神一如既往,累腦累心累手累腳,腳打後腦勺兒。兩岸朋友和南北同行,無不感佩。
“到黑大去!”烏托邦的幻滅
錦池有個口頭禅:陶爾夫有功底,劉敬圻有靈氣,而我是拼命三郎!三個人绾在一起,不能為“第三世界”的黑龍江争一口氣嗎?這是他意欲調往黑大的初心。萌發這一念頭的時間,是他被借調北京完成使命之後。
上世紀70年代後期,錦池被借調到馮其庸先生那裡,參與《紅樓夢》新校本的校訂工作,持續了兩年左右。在此期間,錦池與幾位資深學者及中青年才俊有了較多聯系。視阈開闊了,潛在的學術熱情開始活潑潑湧動。他的第一本紅樓夢論文集正在孕育中。他真的向往為黑龍江多做一些讓今人振奮對後人有益的事情。
《紅樓十二論》
陶爾夫反響靈活。這個正宗四川人與那位正宗江蘇人幾乎同聲同氣。但當時的大氣候不适合進行具體運作。在錦池癡迷于《紅樓夢》的日子裡,陶爾夫不聲不響開始了大工匠式的細小工程,夯實着研治詞史的根基。
1978年到1979年,我重返母校,在吳組缃先生指導下,用了兩個學期,較系統的閱讀元明清筆記,完成了《嘉靖本中的曹操性格》與《嘉靖本與毛本校讀劄記》,分别刊登于《文學評論》(1980年第2期)與《求是學刊》(1981年1-2期),引起相關學界的關注。
錦池的《紅樓十二論》與陶的《宋詞百首譯釋》等先後出版并多次重印。
錦池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四大古典小說論稿》與《六大古典小說識要》源源不絕的推出,為他晚年的四大學術名著考論奠定了堅實基礎。陶的《北宋詞壇》與《南宋詞史》也得到同行專家的鼓勵(《南宋詞史》獲首屆全國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
《中國六大古典小說識要》
錦池和我先後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号及省内首批國務院津貼。
那是一個夙興夜寐宵衣旰食的時段。在這樣的背景下,錦池初衷不改,從1980至1996,十五年間前後三次向兩校校長和省教委(教育廳前身)誠懇地言說心志:到黑大去!為偏遠黑龍江省的古代文學傳播與承揚多做幾件有益的事兒。
三次申述,每一次都受到尊重和禮遇,讓錦池充滿希望。但結果卻是一次又一次失敗。
在黉門主管的心目中,這種結局,再正常不過了。
黑大校長但凡清醒,不會“入室搶劫”同根相煎。
哈師大校長但凡清醒,不會把自家的“鬥戰勝佛”拱手相讓。
省教委主任但凡懂得規矩,不會做“上級主管部門的主管”也倍感棘手躲躲閃閃的事。
作為知情人,我僅以最後一次申報過程中的一次校長對話會為力證,看看張錦池教授的可愛和公立地方性大學用人體制的可悲。
那是1996年夏,錦池第三次提出“到黑大去”的心志。
9月23日,黑大主管科研與研究所學生工作的副校長(海歸,哲學博士、教授)去錦池家中探望,然後接他來到學校,與主管學科建設的副校長(實體學教授)一道,坦誠商讨相關事宜,再次表達學校對錦池的敬重與感激。
緊接着,黑大校長委托哲學博士出身的副校長(兼《求是學刊》主編)寫信,完成了一份情感充沛邏輯綿密的商調張錦池教授陳情表,呈送省内各相關部門。
緊接着,我家座機接到了省教委主任的電話。中心意思是,錦池教授在哈師大是否受了委屈?我斬釘截鐵告訴對方,就我所知,錦池沒有委屈,他是哈師大萬分珍重的人才。他希望來黑大的動機就像他說的那樣單純透明。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實的。你們應該相信他對黑龍江的感情。
教委主任是哈工大出來的理工男,不是玩弄權術打官腔的人。他說教委也就是一個職能部門,無權給哈師大校長下指令,但他可以進行協調。他說他已經向主管省長彙報了,主管省長将召開一個小型的但有權威性的對話會議,讓兩校校長面對面協商。
慶祝張錦池先生從教五十五年學術報告會
緊接着,這個小型對話會就召開了。是1996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兩校各出席3個人:校長,主管副校長,主管處處長,另有當事人張錦池,知情人劉敬圻,共8人。原說主管省長主持,開會時間到了卻通知說主管省長接待北京來人,一時難以脫身,讓教委主任代他主持。
兩校4位校長均有充分準備。各自态度明朗,磊落坦蕩,材料翔實,條分縷析,各自陳述張錦池教授對本校學科建設不可或缺的學術位置。他們的使命感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讓人感動。但他們的這一場對話,也是無用功。
對話的結果,自然是沒有結果。
錦池的兩次發言,依然是“到黑大去”。
就在這次對話的第二年五月,錦池的知音陶爾夫猝發心疾,撒手而去。烏托邦設想,從此徹底化作曆史。
《南宋詞史》
“賢伉俪”的N次方
認識張錦池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不遺餘力負重前行。這印象是沒有誤差的。可是你知道嗎?在而立之年,他幸運地遇到一位秀外慧中文靜沉穩的青年女醫生。從那時起,他超負荷的人生壓力就被這個優秀女孩兒分擔了一半。她的名字叫于珊媛。
珊媛不是尋常意義上的賢内助,她是外表安詳,内心強大,事業家庭兩不誤的隐性女神。
珊媛幼失怙恃,跟着長姊于撫媛安貧若素的長大成人。在她79歲生日的家宴上,長姊深情的把她定位為“四好才女”,好學生,好醫生,好母親,好妻子。還能寫一手漂亮的催人泣下的文章。
珊媛第一次聯考,被錄取到北廣。後因慢性疾患辍學。次年又以優異成績被哈爾濱醫科大學錄取。這是她的唯一志願。五十餘年在四個醫院從醫,醫德醫術深受患者及其家屬推重,是省林業醫院總院暨省紅十字醫院神經内科主任,在同行專家中享有盛名。
她與錦池的初識,是經朋友介紹的,屬異地交往狀态。加上兩人性情青澀内斂,起始階段互不主動,若即若離。不久,珊媛家境發生意外突變,她出于自尊,更冷落了與錦池的交往。錦池得知珊媛的不幸,當即慨然挺身,誠摯地向珊媛求婚,在一方危難中完成了這樁美滿姻緣,畢生相濡以沫,休戚與共。
張錦池先生伉俪情深
一雙兒女是錦池的驕傲,但兒女的健康成長卻更多地滲透了珊媛的心血汗水。一日三餐吃什麼?一年四季穿什麼?周考、月考、期末考,中考,聯考,考研,考博,留學,擇業,結婚生子,多少環節?多少麻煩?多少責任?于珊媛,一攬子挑在柔弱的雙肩,為了給那個癡迷于站講台、寫文章、出席并承辦各種學術會議的老公,騰出更充分的時間和空間。
珊媛的話很少,可思維嚴密,理家周詳。是名實相副的“内閣總理”。珊媛卻總是推功攬過,說粗茶淡飯難不倒我,留親友吃飯,做招牌菜,上檔次的宴品,必須錦池掌廚,比如冰糖水晶肘子,很複雜呢。
的确,我和不少學生都享用過錦池做的水晶肘子。錦池教育孩子也有他的高招兒,他會在關鍵的點上給孩子以鼓勵。他的經典語錄是:好孩子都是誇出來的。
盡管如此,可我總是把珊媛視為錦池的政委。
耳順之年以後,珊媛的政委身份愈益顯豁。用錦池的話說,凡學校學院的頭頭找我商量事兒,我盡量請他們晚上來,或珊媛休班的時候來。她能聽明白來訪者的談話意向,她能幫我做出最恰當的回應。
《三國演義考論》
到了晚年,珊媛不僅僅是政委了,她竟然成為錦池修訂那一整套“考論”特别是最後一冊《三國演義考論》的學術助手了。
那是一段十分艱難的歲月。珊媛的身體也逐漸衰弱,醫院返聘後的工作一時間還不能徹底辭絕,她嘗到了内外交困、心力交瘁的滋味兒。但她依舊堅韌地挺着,她不能讓錦池看到她身體的變化。
在校訂《三國演義》論文的那些日子裡,錦池的記憶力每況愈下。晚上,他抓住珊媛,見縫插針,讓她把需要增改的字句段落寫到某頁某行某句的旁邊。次日淩晨卻又抓住她說,昨天修訂的地方錯了,應該把它們挪到某頁某行某句的上邊(或下邊)。珊媛幾乎崩潰了。
她不是為自己擔憂,她是為錦池的狀況悲哀。她是神内專家啊。她心痛了,但她必須若無其事的安詳甯靜地挺着。
2020年8月11日淩晨4時,于珊媛因久患神經系統肌無力症,病逝于家中。錦池被護工侍奉在另一個寬敞的房間内,對珊媛的辭世毫無察覺。
台灣《詩經》郵票
她比她的先生早走46天零13個小時。
珊媛的恒心,感動了同齡的女人和男人,也感動了年輕的學生。一位青年博士在為師母撰寫的小傳中,借用《詩經·小雅·蓼莪》中追慕雙親撫育子女之德的名句,紀念恩師師母之間同心同德相扶相依的伉俪深情:
我德有阙,君實匡之;
我生多難,君扶将之;
我有疑事,君榷君商;
我有賞心,君寫君藏。
珊媛沒有看到錦池安詳往生的模樣。她先去了無病無災的天國,為疲憊已極的錦池,做小憩的準備去了。
2021年3月
上下滑動檢視注釋
注釋:
李贽《忠義水浒傳叙》中把宋江定位為“忠義之烈”,拙文《宋江性格補論》用梳理文本的方法質疑這一著名結論。錦池在《未定稿》1983年第20期上發表的《水浒傳是一部宣傳忠義的小說》中對宋江的認知,被拙文作為“學者共同肯定的論點”與“繼續讨論宋江形象的前提”。
寫作《嘉靖本中的曹操性格》的由頭,是魯迅的一句名言:“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演義》,更而想到戲台上那一位花面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拙文認為,小說中的曹操與戲台上的花面奸臣還是有較大差別的。魯迅說這句話的時候,可能還沒有時間涉獵嘉靖本(弘治本)。
我的确多次對錦池說,他早年論及林黛玉的文字有拔高之嫌,但到拙文《林黛玉永恒魅力再探讨》面世的時候,林黛玉已不是學界關注熱點,拙文的寫作,是因為突然發現了何其芳先生遠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一個見解:“……至于林黛玉性格特點,如果隻用籠統的叛逆者來說明,那就更過于簡單了。”何其芳先生在提出并高揚“叛逆說”的同時,就提醒讀者評家,過多地關注“叛逆”,對一個豐滿典型的解讀就未免單薄貧瘠了。于是有了“林黛玉補說”那篇重新梳理和檢討自己的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