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池太累了。他的仙逝,是上天不忍,招呼他小憩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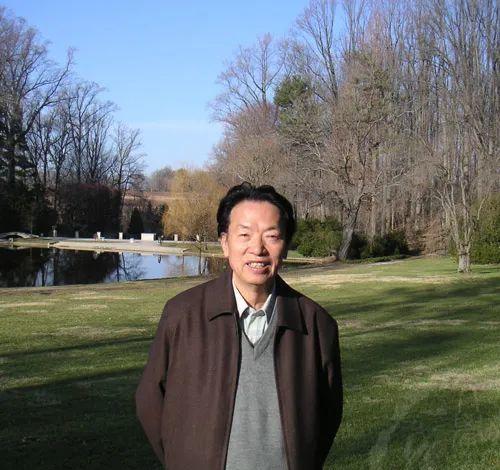
张锦池先生
从2020年9月27日17点55分以来,学生们亲友们的怀念文字已足以汇编成书。那是张锦池本传,是正史。我的琐忆,是杂记,是对本传的零落凿实的注释。
忝为大师姐
锦池与我和陶尔夫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同系,同专业,同师父,同样幸运地聆听了五十年代前期院系调整后汇聚到北大的二十几位老北大、老清华、老燕京、老中山、老科学院文学所国家级文史大家系统缜密的课堂讲授,又先后遭遇了渴望读研却暂停招研的教育气候,还先后满腔热血,投身边疆,在黑龙江两所省属院校任教,深深植根在美丽富饶却并不富裕的黑土地上,呕心沥血,至死不离不弃。
锦池与我也有显见的不同。
这不同,不是指我比锦池早入学四年,且痴长一岁,而是说,论天赋,论志向,论勤勉,论学术成就,即我与锦池的生存状态,相去甚远。我类似金庸、古龙笔下恪守传统、尊师怜才、功夫正宗却谨慎拘泥的看家女徒,锦池则是生机勃发、不懈进取、挑战自我、献身江湖的少年精英。
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把两个不同性情的人绾结在一起的。
刘敬圻教授
我第一次认识锦池是在1964年高考评卷的一次大型对话会上。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干菜的故事》,给考生提供材料,让写一论说文。
阅卷开始的第一天,复查(顾问)组发现,在掌握评分标准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于是便召集全体阅卷人会议,以同一张考卷为例证,展开对话。那份作文卷的最高分是90多,具体分数记不清了,但90分以上是确凿无疑的。阅卷人恰恰是哈师大青年助教张锦池。
最低分是50分左右,也不记得具体数字了,但不及格而且远离及格线也是确凿无疑的,阅卷人是另一高校的青年教师。对话中,锦池毫不掩饰他的锐气,对这份作文的认知能力和文字水平赞赏不已。给了低分的阅卷老师也认为考生的文字能力不错,但整篇文章有否定三面红旗之嫌。对话中还出现了第三种第四种意见,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试卷被送到沈阳“东北三省评卷指导小组”(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临时性机构),结果是指导小组给予近90分的成绩,并提出如何恰切把握评分标准的几点要求,讨论就此结束。
张锦池先生青年时期
正是这场讨论,我才知道哈师大新来了一位校友,教龄不过一年。也是第一次见识了这位校友善于思辨勇于坚持的张力。
我与锦池第一次晤面的时间地点缘由统统不记得了,只记得进入中老年之后,锦池在轻松愉快的场合中,经常重复下面一段话:
大师姐第一次看到我就用质问的语气说,你是张锦池啊,听说你很傲?我回答她说,要看对方的眼睛长在哪里。如果长在这儿(指着自己的眼睛),我一点也不傲。如果长在这儿(指着自己的额头),我的眼睛就长到天灵盖上去了。
这段话,像警句似的,被学生收进《张锦池教授语录》中去了。其实,数十年的往来足以说明,锦池的傲,是性格亮点之一。他很懂得尊重一切人,不说硬话,不说闲话,不说大话,不说胡话;他更努力践行自尊自重自爱自强的古训。他能恰到好处地把握个中分寸。
《张锦池先生八秩称觞集》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锦池喜欢讲述两个故事。
其一,他常常以无比崇敬的口吻,复述他至为崇拜的吴组缃、何其芳两位前辈学者,围绕薛宝钗的阶级阶层定位互不妥协彻夜舌战,然后愉快地共享吴师母美味早餐的经典佳话。吴何两位恩师的风格,正是锦池对朋友之间师生之间美好学术关系的憧憬,那便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锦池知道我喜欢吴先生的性格,喜欢听吴先生讲课。吴先生因公出境的时候,总是请何先生代课,而且一旦返校,重登讲台,必定幽默地说,何先生向你们散布了什么毒素?我来肃清一下。同学们哄堂大笑。
锦池也清楚地知道,我对吴何两位先生的研究思路一向兼收并蓄,各美其美。
《史诗红楼梦》,何其芳著,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
只是在个别艺术典型的解读方法上受何先生影响较大。这种兼收并蓄、美美与共的接受习惯,与1956年的燕园氛围息息相通。
1956年,北京大学创造性地恭请了吴组缃何其芳两位先生共同开设《红楼梦》系列专题讲座。把“和而不同”同中有异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方法清澈磊落地传递给学生。一时瑜亮(同学们兴奋的把两位先生比喻为周瑜和诸葛亮),神采飞扬,气薄云天,颇具震撼力。燕园学子对吴何两位先生的高贵境界,代代相传,至今神往。
锦池1958年入学之后,自会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吴组缃先生课上课下的学术启蒙中,熟知了当年吴何两位挚友之间课堂论辩各抒己见的故事。他不厌重复且乐在其中的传递这个美丽的故事,正是提醒自己,提醒学生,千万记住吴何两位前辈。记住他们的做人品质,记住他们的治学风尚。无论为人为学,都要做堂堂正正的人。
《红楼梦的艺术生命》,吴组缃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锦池热衷传播的另一个故事是凡人琐事,是哈师大中年以上的教工耳熟能详的传奇。当事人是锦池早年的邻居,一对善良和美的夫妻。
这里用得上那句老话,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邻居家的不幸竟然来自颜值。他俩的长相有点“困难”,以致让他们对生儿育女充满压力,唯恐儿女的模样不能适应这个看脸的时代。
谁能想到,这对谦恭到自卑的夫妻,孕育出一个白雪公主般的女儿,让他们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亲生的,亲生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童话世界赐予的女婴长到也会用套话写作文的时候,更加出落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人见人爱了。
讲到这儿,锦池都忍不住点题:可见,基因,不决定一切。它在遗传过程中产生变异。
尽管比喻是蹩脚的,邻居的故事还是有启发性的。即使从单纯承传的角度讲,也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做学生做学问就更有能动性了。
任何不够完美的前辈身上,你都可以发现优质的东西。善于选择的人可以把老师们的优质元素吸纳到自己的知识库中,扬长避短,博采众长,点石成金,出类拔萃的新生代就有望脱颖而出了。
一次走心的谈话
大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与锦池有过一次十分走心的对话。主旋律是研究方法。
锦池以调侃口吻坦率地问我,大师姐不少文章的标题和行文中,总是“补论”“补论”的,我怎么觉得你的补论,似乎是针对我呢?
我不觉得突然。也模仿他的口吻诚实地回答了他。我说,平时你总说大师姐是你的知音,你的知音原来这么小家子气?吭哧瘪肚一两年才炮制一篇文章,竟然是为了对付你啊?那岂不是太耗费光阴?锦池不由得笑了。
我拽着锦池的思路,与他共同捋了捋我写作那些“补论”的时间表。让他知道,我不是不想承继与模仿吴何两位恩师的风范,把我与他在研究方法上的大同小异梳理出来,公之于众。但我们好像还没有这种底气吧,没有足够的资历这样做。再说,那些“补论”真的没有一篇是被锦池的见解激出来的。
《明清小说补论》(增订本)
比如《宋江性格补论》是被我们仰视的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中一个结论引发出来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性格》是被“圣人”鲁迅的一句话引发出来的。“林黛玉补论”(《林黛玉永恒价值再探讨》)是被我们喜爱的前辈大家何其芳先生《论红楼梦》中的一个见解引发出来的。
《薛宝钗一面观及五种困惑》(也算补论吧)是想寄给吴组缃先生审阅的,吴先生曾说过要为薛宝钗落实政策,我想请教吴先生,这么写,算不算落实政策?但胆怯,惶恐。不是怕自己挨骂,是怕吴先生生气伤身体。于是直接给《红楼梦学刊》了。
每一篇补论的诱因和由头,都在每一篇的开头,各自指名道姓毫无遮拦地供出来了。锦池有空,也可以拨冗再翻翻看。
锦池不时地插话,或质疑,或补充。越交流越坦诚越兴奋越透明甚至放肆了。
我顺手拿出来不久前锦池给我的新作《巧姐漫议》手稿,赞叹说,这篇大文思路新巧流畅,格调也清雅别致。你有没有轻快愉悦的感觉?(参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2辑后记)
《红楼梦考论》
锦池说我转移了话题。
他谈兴尚浓。说讨论研究方法,是个大工程。我们再找一个大块儿时间,继续磨牙。
我和锦池在“自由思想,兼容并包”校训的勉励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和谐互补了近四十年。
三次“首届”红楼梦研讨会
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哈尔滨师范大学先后主办(或承办)了三次大型红楼梦研讨会。且均为“首届”。为中国红楼梦研究史留下令人赞叹令人惊喜令人仰视的三座丰碑。张锦池的心血灌注其间。
1980年7月,在结束“四人帮”横行之后的那个科学的春天,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友谊宫,举行了全国首届红楼梦研讨会。这是一次庄严郑重的大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全力支撑着这次会议。
会前,文学所与红研所各自派出博学笃行的资深中青年学者邓绍基、刘世德、胡文彬等与哈师大校系主管领导和张锦池一道,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四楼和二楼会议室内,作精细周详的准备工作。并成立了“首届全国红楼梦研讨会筹委会”。
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合影
锦池是筹委会重要成员,也是落实、组办、主持此次研讨会的重要践行者。闭幕式上郑重宣布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推荐北大教授吴组缃先生任首届会长(后因身体原因坚辞)。
时过六年,1986年6月,依旧在哈尔滨友谊宫,哈师大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由冯其庸任会长的中国红学会为此次会议成立了由各方相关人士参加的筹委会。中国大陆,港澳台,境外七个国家的一百二十余位代表出席了研讨会,提交论文一百一十余篇(是研究会最大亮点)。
会议期间,同步展示了三项精美的“盛宴”:红楼梦版本与文献文物博览会;红楼梦艺术节;红楼梦讲习班。盛况难再。
锦池的角色定位如下: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研讨会中外两主席的助理,艺术节组织委员,讲习班特邀主讲人。自然是第一忙人。
十年以后,1996年1月,在台湾红学家热心推动下,哈师大主办了“乙亥年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盛会。地点依旧是哈尔滨,但会场却选择在远离松花江的哈尔滨西南地区,因为,松花江两岸到处矗立着冰灯和雪雕,簇拥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前来领略冰雪节的欢快游客。
张锦池先生在乙亥年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上发言
台湾学者建议在隆冬季节相聚,自当与冰雪节有缘,而年长学者的应邀北上,无疑是《红楼梦》自身的永远魅力了。如著名小说家王蒙,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及历史系教授周策纵等。他们不仅不畏严寒,而且以情趣盎然的学术演讲,丰富和温暖着每一位与会学人。
作为东道主,锦池的服务精神一如既往,累脑累心累手累脚,脚打后脑勺儿。两岸朋友和南北同行,无不感佩。
“到黑大去!”乌托邦的幻灭
锦池有个口头禅:陶尔夫有功底,刘敬圻有灵气,而我是拼命三郎!三个人绾在一起,不能为“第三世界”的黑龙江争一口气吗?这是他意欲调往黑大的初心。萌发这一念头的时间,是他被借调北京完成使命之后。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锦池被借调到冯其庸先生那里,参与《红楼梦》新校本的校订工作,持续了两年左右。在此期间,锦池与几位资深学者及中青年才俊有了较多联系。视阈开阔了,潜在的学术热情开始活泼泼涌动。他的第一本红楼梦论文集正在孕育中。他真的向往为黑龙江多做一些让今人振奋对后人有益的事情。
《红楼十二论》
陶尔夫反响敏捷。这个正宗四川人与那位正宗江苏人几乎同声同气。但当时的大气候不适合进行具体运作。在锦池痴迷于《红楼梦》的日子里,陶尔夫不声不响开始了大工匠式的细小工程,夯实着研治词史的根基。
1978年到1979年,我重返母校,在吴组缃先生指导下,用了两个学期,较系统的阅读元明清笔记,完成了《嘉靖本中的曹操性格》与《嘉靖本与毛本校读札记》,分别刊登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与《求是学刊》(1981年1-2期),引起相关学界的关注。
锦池的《红楼十二论》与陶的《宋词百首译释》等先后出版并多次重印。
锦池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四大古典小说论稿》与《六大古典小说识要》源源不绝的推出,为他晚年的四大学术名著考论奠定了坚实基础。陶的《北宋词坛》与《南宋词史》也得到同行专家的鼓励(《南宋词史》获首届全国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
锦池和我先后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及省内首批国务院津贴。
那是一个夙兴夜寐宵衣旰食的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锦池初衷不改,从1980至1996,十五年间前后三次向两校校长和省教委(教育厅前身)诚恳地言说心志:到黑大去!为偏远黑龙江省的古代文学传播与承扬多做几件有益的事儿。
三次申述,每一次都受到尊重和礼遇,让锦池充满希望。但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失败。
在黉门主管的心目中,这种结局,再正常不过了。
黑大校长但凡清醒,不会“入室抢劫”同根相煎。
哈师大校长但凡清醒,不会把自家的“斗战胜佛”拱手相让。
省教委主任但凡懂得规矩,不会做“上级主管部门的主管”也倍感棘手躲躲闪闪的事。
作为知情人,我仅以最后一次申报过程中的一次校长对话会为力证,看看张锦池教授的可爱和公立地方性大学用人体制的可悲。
那是1996年夏,锦池第三次提出“到黑大去”的心志。
9月23日,黑大主管科研与研究生工作的副校长(海归,哲学博士、教授)去锦池家中探望,然后接他来到学校,与主管学科建设的副校长(物理学教授)一道,坦诚商讨相关事宜,再次表达学校对锦池的敬重与感激。
紧接着,黑大校长委托哲学博士出身的副校长(兼《求是学刊》主编)写信,完成了一份情感充沛逻辑绵密的商调张锦池教授陈情表,呈送省内各相关部门。
紧接着,我家座机接到了省教委主任的电话。中心意思是,锦池教授在哈师大是否受了委屈?我斩钉截铁告诉对方,就我所知,锦池没有委屈,他是哈师大万分珍重的人才。他希望来黑大的动机就像他说的那样单纯透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你们应该相信他对黑龙江的感情。
教委主任是哈工大出来的理工男,不是玩弄权术打官腔的人。他说教委也就是一个职能部门,无权给哈师大校长下命令,但他可以进行协调。他说他已经向主管省长汇报了,主管省长将召开一个小型的但有权威性的对话会议,让两校校长面对面协商。
庆祝张锦池先生从教五十五年学术报告会
紧接着,这个小型对话会就召开了。是199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两校各出席3个人:校长,主管副校长,主管处处长,另有当事人张锦池,知情人刘敬圻,共8人。原说主管省长主持,开会时间到了却通知说主管省长接待北京来人,一时难以脱身,让教委主任代他主持。
两校4位校长均有充分准备。各自态度明朗,磊落坦荡,材料翔实,条分缕析,各自陈述张锦池教授对本校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学术位置。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让人感动。但他们的这一场对话,也是无用功。
对话的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
锦池的两次发言,依然是“到黑大去”。
就在这次对话的第二年五月,锦池的知音陶尔夫猝发心疾,撒手而去。乌托邦设想,从此彻底化作历史。
《南宋词史》
“贤伉俪”的N次方
认识张锦池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不遗余力负重前行。这印象是没有误差的。可是你知道吗?在而立之年,他幸运地遇到一位秀外慧中文静沉稳的青年女医生。从那时起,他超负荷的人生压力就被这个优秀女孩儿分担了一半。她的名字叫于珊媛。
珊媛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贤内助,她是外表安详,内心强大,事业家庭两不误的隐性女神。
珊媛幼失怙恃,跟着长姊于抚媛安贫若素的长大成人。在她79岁生日的家宴上,长姊深情的把她定位为“四好才女”,好学生,好医生,好母亲,好妻子。还能写一手漂亮的催人泣下的文章。
珊媛第一次高考,被录取到北广。后因慢性疾患辍学。次年又以优异成绩被哈尔滨医科大学录取。这是她的唯一志愿。五十余年在四个医院从医,医德医术深受患者及其家属推重,是省林业医院总院暨省红十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在同行专家中享有盛名。
她与锦池的初识,是经朋友介绍的,属异地交往状态。加上两人性情青涩内敛,起始阶段互不主动,若即若离。不久,珊媛家境发生意外突变,她出于自尊,更冷落了与锦池的交往。锦池得知珊媛的不幸,当即慨然挺身,诚挚地向珊媛求婚,在一方危难中完成了这桩美满姻缘,毕生相濡以沫,休戚与共。
张锦池先生伉俪情深
一双儿女是锦池的骄傲,但儿女的健康成长却更多地渗透了珊媛的心血汗水。一日三餐吃什么?一年四季穿什么?周考、月考、期末考,中考,高考,考研,考博,留学,择业,结婚生子,多少环节?多少麻烦?多少责任?于珊媛,一揽子挑在柔弱的双肩,为了给那个痴迷于站讲台、写文章、出席并承办各种学术会议的老公,腾出更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珊媛的话很少,可思维严密,理家周详。是名实相副的“内阁总理”。珊媛却总是推功揽过,说粗茶淡饭难不倒我,留亲友吃饭,做招牌菜,上档次的宴品,必须锦池掌厨,比如冰糖水晶肘子,很复杂呢。
的确,我和不少学生都享用过锦池做的水晶肘子。锦池教育孩子也有他的高招儿,他会在关键的点上给孩子以鼓励。他的经典语录是: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
尽管如此,可我总是把珊媛视为锦池的政委。
耳顺之年以后,珊媛的政委身份愈益显豁。用锦池的话说,凡学校学院的头头找我商量事儿,我尽量请他们晚上来,或珊媛休班的时候来。她能听明白来访者的谈话意向,她能帮我做出最恰当的回应。
《三国演义考论》
到了晚年,珊媛不仅仅是政委了,她竟然成为锦池修订那一整套“考论”特别是最后一册《三国演义考论》的学术助手了。
那是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珊媛的身体也逐渐衰弱,医院返聘后的工作一时间还不能彻底辞绝,她尝到了内外交困、心力交瘁的滋味儿。但她依旧坚韧地挺着,她不能让锦池看到她身体的变化。
在校订《三国演义》论文的那些日子里,锦池的记忆力每况愈下。晚上,他抓住珊媛,见缝插针,让她把需要增改的字句段落写到某页某行某句的旁边。次日凌晨却又抓住她说,昨天修订的地方错了,应该把它们挪到某页某行某句的上边(或下边)。珊媛几乎崩溃了。
她不是为自己担忧,她是为锦池的状况悲哀。她是神内专家啊。她心痛了,但她必须若无其事的安详宁静地挺着。
2020年8月11日凌晨4时,于珊媛因久患神经系统肌无力症,病逝于家中。锦池被护工侍奉在另一个宽敞的房间内,对珊媛的辞世毫无察觉。
台湾《诗经》邮票
她比她的先生早走46天零13个小时。
珊媛的恒心,感动了同龄的女人和男人,也感动了年轻的学生。一位青年博士在为师母撰写的小传中,借用《诗经·小雅·蓼莪》中追慕双亲抚育子女之德的名句,纪念恩师师母之间同心同德相扶相依的伉俪深情: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
我生多难,君扶将之;
我有疑事,君榷君商;
我有赏心,君写君藏。
珊媛没有看到锦池安详往生的模样。她先去了无病无灾的天国,为疲惫已极的锦池,做小憩的准备去了。
2021年3月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注释:
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把宋江定位为“忠义之烈”,拙文《宋江性格补论》用梳理文本的方法质疑这一著名结论。锦池在《未定稿》1983年第20期上发表的《水浒传是一部宣传忠义的小说》中对宋江的认知,被拙文作为“学者共同肯定的论点”与“继续讨论宋江形象的前提”。
写作《嘉靖本中的曹操性格》的由头,是鲁迅的一句名言:“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到戏台上那一位花面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拙文认为,小说中的曹操与戏台上的花面奸臣还是有较大区别的。鲁迅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时间涉猎嘉靖本(弘治本)。
我的确多次对锦池说,他早年论及林黛玉的文字有拔高之嫌,但到拙文《林黛玉永恒魅力再探讨》面世的时候,林黛玉已不是学界关注热点,拙文的写作,是因为突然发现了何其芳先生远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见解:“……至于林黛玉性格特点,如果只用笼统的叛逆者来说明,那就更过于简单了。”何其芳先生在提出并高扬“叛逆说”的同时,就提醒读者评家,过多地关注“叛逆”,对一个丰满典型的解读就未免单薄贫瘠了。于是有了“林黛玉补说”那篇重新梳理和反省自己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