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頭琴
文/孫昌國
一
耿長福是被從雪野水庫的工地上擡回家的。
為了趕進度,要在水庫底下打樁子,長福和村裡一塊去的幾個青年報名參加了突擊隊,數九寒天的,砸開冰碴子光着腿就下去了。半小時一次輪班,兩個班沒輪完,長福就覺得兩腿不聽使喚了,工友們把他擡到工棚裡,歇息了兩天,眼見着兩個膝蓋子腫得和大饅頭似的,活是幹不了了,公社便派人給送了回來。
本以為是凍着了,開了春暖和了就好了,熬過一個寒冬,長福的腿卻絲毫不見消腫的迹象,兩個膝蓋子也開始發黑,村裡的赤腳大夫配的止疼藥也不管用了,每天就像刀剜似的疼,好好的一個後生眼看着就癱在了床上。
上有小腳的老娘,下有四個嗷嗷待乳的孩子,一個家瞬間天就塌了。看着媳婦一個人忙裡忙外伺候一家老小,自己卻啥忙也幫不上,長福恨得直抽自己耳刮子,脾氣也一天天暴躁了起來。
麥子黃梢的時候,忽然起了“運動”,上邊要求村村都要唱“樣闆戲”,就用最熟悉的萊蕪梆子。一輩子土裡刨食的泥腿子們可犯了難,以前别說唱了,聽也很少聽啊,好在上邊了解各村的難處,就從大劇團裡每個村裡都給派來了老師,唱念做打、鑼鼓家什一點一點地教。
想學的歇了工就在長福家門口的破廟台子前排練,每天聽着他們咿咿呀呀的倒腔,長福心裡也癢癢,奈何自己動不了,就每天趴在窗台上聽他們學。
這眼見着麥子入了倉,梆子戲也學了個七拉八拉,莊稼人的膽子也是大,塗塗抹抹居然也就搭起來戲台子,“适才呀,聽得司令講……”的唱了起來,一招一式也算有模有樣。就是剛開始幾場的時候,有劇團的老師闆着胡琴,聽不出一二三,待到老師們一走,這胡琴就卡不進槽裡了,弦不對,唱得挺好的戲詞瞬間也沒了章程,眼瞅着上邊審查的日子是一天天近了,氣得村長在戲台子上貓三狗四的直罵娘。
孩子們回來和長福學村長罵人的樣子,長福覺得好笑,又挺急人,自己在炕沿上坐着聽了這個把月,快慢梆子、光才光,緊垛子、頂簾子,來回那幾個調調都印在耳朵裡了,怎麼老師手把手教的學不會呢。
正好後院的二愣子來找他拉呱,又說起村長罵娘的事兒,長福怯生生地說:“要不你們把我擡過去我試試……”,二愣子是真愣了:“長福,這腿腳不好了,腦子也壞了嗎,那東西是個人就能拉,要老師教幹啥,你可真行……”,說歸說,第二天,全莊上的人都知道長福病得說胡話了。
誰也沒拿長福的話當真,他們甚至認為他的話比村長跳着腳罵娘還招笑。過了兩天,村長卻找上門來了:“小爺爺,你真能拉胡琴”?看着比自己小兩輩的村長,長福也不敢說大話:“整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胡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長啥樣,不過我在這炕頭上坐着聽,倒是覺得沒啥大巧處,不瞞你說,我聽着那胡琴響,腿都不覺得疼了,我能試試”。“行,小爺爺,我信你,我這就回去拿胡琴,你拉拉我聽聽……”
第二天,看戲的人陸陸續續又圍了大半個戲台子,鑼鼓家什敲罷,流水轍子轉開,一聲悠揚的胡琴聲鎮住了場子。他們驚訝地發現,拉胡琴的分明是一年多沒出門,癱在炕上的長福。
二
最開始的時候,由于在炕上呆了這年數,到了戲台以上,長福根本就坐不住,一天演個三場五場的,他都是跪在側台子那裡拉,哪一天下來都是大汗淋漓渾身濕透了。長福欣慰的是,仿佛那個胡琴就是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拿在手裡一點也不陌生,那旋律、那韻味似乎就是血液裡流淌出來的。
轉眼間,又過了大半年。由于長福的胡琴,他們村裡的小劇團一時間名聲大噪。
村裡也認可他的付出,給他每天記十分工,十分工,這可是整勞力的價值,每每想到這,想到家裡那幾張吃飯的嘴和辛苦勞作的媳婦,長福的胡琴拉得就更有味道了。
年底的時候,長福姐姐家的女婿,村裡的赤腳醫生大春捎回來一個好消息,他打聽到周村有個地方能治他的腿。
但看着這一屋子老的老小的小,長福隻是苦笑了一下。大春看出了長福的無奈,說:“舅,你放心吧,開了春我和你去看,看不好,咱不回來……”。人和人之間的緣分就是這樣,一個熱心腸的外甥女婿,用獨輪車推着長福,幾百裡的路程,輾輾轉轉大半年,竟然就把這該死的腿疾除了根。
于是,那段時間關于長福的傳說越說越神,有人說劇團的老師在教拉胡琴的時候晚上給他開小竈了;有人說他從娘胎裡生下來就會拉胡琴;還有人說腿不能走的他受到了神經袒護,賜給了這一手拉胡琴的本事……一時間,十裡八鄉跑來聽拉胡琴的人比看戲的還多。長福,俨然成了這個土戲台子上最硬的角兒。
“運動”依舊如火如荼的進行着,樣闆戲也年複一年的唱着。耳濡目染的作用吧,長福發現,家裡逐漸長起來的幾個娃娃,好像也對梆子戲有特别的興趣。自打腿好了以後,每天不用人攙扶了,他似乎也有了底氣,再到唱戲的時候,他也喜歡把孩子們帶上去湊湊熱鬧了。漸漸的,他發現老大的胡琴已經拉的和他不相上下了,二小子唱的小生那叫一個脆聲;大姑娘能在串場的時候跑跑龍套了,二姑娘也成了《穆桂英挂帥》裡的主角;最小的兩個娃娃也學啥像啥的……
長福是看在眼裡喜在心裡,孩子們一天天長大,日子也一天天見好,真有點苦盡甘來的感覺。
秋收的時候,長福在山上踅摸了一個香椿的樹根,在村頭的河溝裡泡了大半年,回來煙熏火烤一番,又挂在屋檐下曬了大半年。等收了秋,閑暇了,樹根也風幹透了,長福便取下來,拿着個破鐮頭一點點地掏空打磨,又馬尾、松香、棉線、竹子的搗攏了大半月,成型了,孩子們才知道他做了把胡琴。
這也一直是他的一個願望,拉了幾年胡琴卻沒有一把是屬于自己的,再者,買來的那些胡琴總覺得哪個地方不對付。
待到再開鑼唱戲的日子,人們發現,長福的大兒子已經和他并排坐在一起拉弦了,手裡抱着的正是長福用過的胡琴,而長福自己抱的,卻是一把看起來有點土裡土氣還有點别扭粗糙的胡琴,不過拉出來的韻味倒是更好了。
後來,老大問他:“爹,你這是一把啥胡琴啊”?長福笑了笑:“我看着怪像個老虎來,要不叫虎頭琴吧”!
三
從張羅着給老大娶媳婦開始,長福的“虎頭琴”就挂在了牆上。
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那一年,在廣西當了五年兵的老大複員回了家,到村裡的國小當了代課老師。到了年底,村裡也不讓唱“樣闆戲”了,說是要一心一意搞生産,長福也不明白搞生産和唱戲有什麼沖突,不讓唱就不唱吧。不過,過年的時候,都是把胡琴拿下來擦的锃亮,還上了一層松油。
轉過年來開了春,爺倆開始領着一幫弟弟妹妹托土坯,宅基地早就批下來了,他們得趁着魚水來臨之前把土坯準備好,給老大蓋房子,老大要娶媳婦了。一想到自己馬上就要抱上孫子,長福心裡的喜悅絲毫不亞于要娶媳婦的兒子。
這一年是辛苦勞累的,又是快樂喜悅的。茶餘飯後,興緻來了長福便會取下虎頭琴,和孩子們在院子裡一拉一唱,每個人撿拿手的來上一段,街坊四鄰聽見了也都樂意往這兒湊,懂的不懂的都圖個熱鬧,順便還有一點羨慕加嫉妒的目光。
日子也就在這一唱一和中不緊不慢的過着。這不緊不慢中,長福蓋起了五套獨門獨院的房子,全套的圓房嫁俱打發走了兩個出閣的姑娘;這不緊不慢中,長福又收獲了第三代的三個孫子、兩個孫女,還有外孫外孫女;這不緊不慢中,長福也從年富力強到了花甲之年;這不緊不慢中,牆上的虎頭琴,也和這不緊不慢的歲月一樣,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塵土。
有的時候,吃罷飯,長福就和老伴兒互相望着發呆。擡頭看一眼牆上的虎頭琴,總是回來一句:“這老夥計,也不知道還能拉出聲兒來不”?
到了長福六十六大壽的日子了。平常的日子,就是過年,人也沒這麼齊整過,看着一屋子二十幾口子人,長福滿是褶子的臉上樂開了花。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忘記了是誰提出來的了,長福還真就從牆上取下了虎頭琴,咿咿呀呀地拉了起來,早已過了不惑之年的老大順勢拿起一把鍋鏟配合着老爹打起了過門,小臉喝得紅撲撲的老二敞開衣襟也敞開了嗓子:“穿林海,跨雪原,氣沖霄漢……”,接着就是你一嗓子我一小段,每個人盡力地拿捏着自己曾經最拿手的唱腔。日子,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土戲台子上,又回到了那個一家人幹完活的仲夏夜,回到了爹爹上工娘做飯的無憂無慮的時刻。
長福的心醉了,或許是酒,或許是這胡琴聲。他知道,他的胡琴雖然蒙了塵,但是孩子們回來一擦,就敞亮了!
每年過生日的時候,一家人湊一塊兒唱念做打的情景,持續了好多年。
四
過了八十大壽不久,一個老夥計找上門來了:“小爺,現在國家又讓搞啥文化遺産了,咱這萊蕪梆子也算,鄰莊今年已經唱開了,昨兒個我去看了看,直接不像樣,咱也唱吧,給他們打個樣”!長福笑了笑:“多大年紀了都,你也六十好幾了吧,那蟒銬花翎還穿得起嗎,我都八十了,胡琴拉不動了”。“算了吧,頭天你過生日不是拉得一包勁啊”,“行,你張羅吧,人湊起來了,我就去拉胡琴”……
剛出正月,村裡傳出一個消息,老劇團的那幫老夥計要重新登台唱戲。
還是那個土戲台子,還是那幫老夥計,那必須得看啊,誰也不會想到,到了真正演出的那天,來的人,比當年唱樣闆戲的時候還多。
水牌子還是粉筆寫的:《穆桂英挂帥》,《趙公明下山》,《打金枝》,《鍘美案》……長福又抱着虎頭琴上場了,台子地下一陣嘩然:“呀,還是當年那個拉弦的,這麼大年紀了,看着還是那麼精神,今兒可算來着了”,聽着他們的話語,長福也犯嘀咕:“嗐,還是當年那幫看戲的啊,挑了一輩子毛病了,也知不道今回還挑不”……
那次的演出計劃唱一天,愣是被強拉着唱了三天,台子底下光“加官”的煙酒就堆了足足一小車,過去了好些日子,長福和他的老夥計們還意猶未盡:唱穆桂英的塗了幾層粉還蓋不住臉上的皺紋,去給周瑜吊孝的諸葛亮上台了跪不下愣是坐着哭了一回,下山的趙公明讓老虎絆了個趔趄。他們知道,演得好不好已經無所謂了,關鍵是那個場面還在,就和長福懷裡頭的虎頭琴一樣,不管放多少年,一拉還是那個響。
又過了兩三年,孩子們再聚的時候,不再提拉胡琴的事兒了。一者,老頭拉不動了,二者,老伴兒還有和老頭一起拉胡琴的老大都先他一步走了。更多的時候,孩子們不再提拉胡琴的事,甚至連萊蕪梆子的話題都不說了。
長福也一天天老去,也許,那把虎頭琴他真的拉不動了。
八月十五,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吃罷團圓飯,長福罕見的非要孩子們把虎頭琴給他,擦幹淨灰塵,架起弓弦,卻再也沒拉出聲來。
第二天,孩子們送飯的時候,長福抱着那把虎頭琴,已經去了。鄰家的嫂子說,昨夜裡,仿佛聽見萊蕪梆子的過門,拉了一整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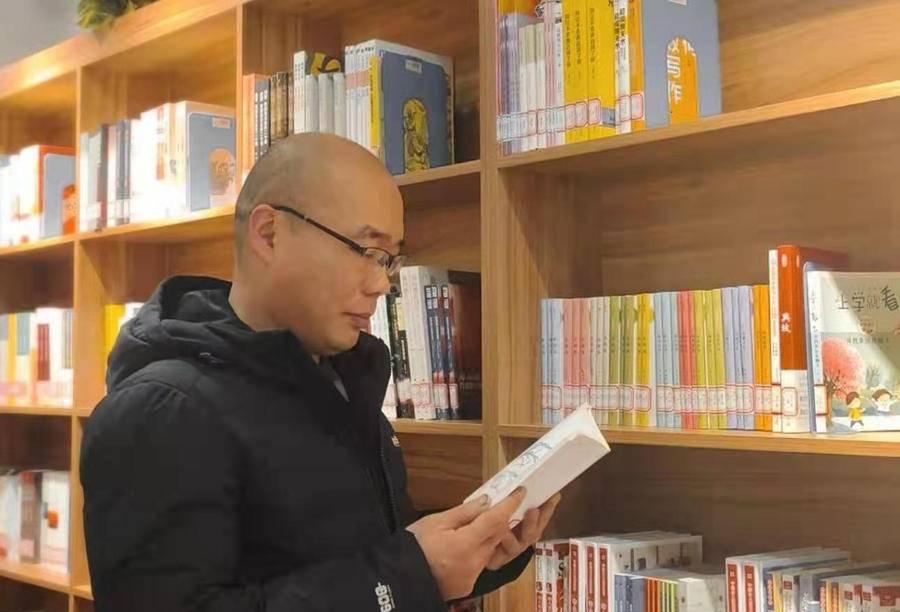
作者簡介:孫昌國,筆名大木,八零後。濟南市萊蕪區人,現居淄博市博山區。博山區作協第三屆副主席,淄博市作協會員。有散文、詩歌作品十幾萬字發表在各級報刊雜志及網絡平台,抗疫詩歌《七律 靜夜思》由淄博市圖書館收藏,散文合集《散文十二家》(第五輯)由黃海數字出版社出版。
【博山區作協】佳作選
壹點号博山區作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