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代文人篆刻的興起
(一)八思巴文在官印中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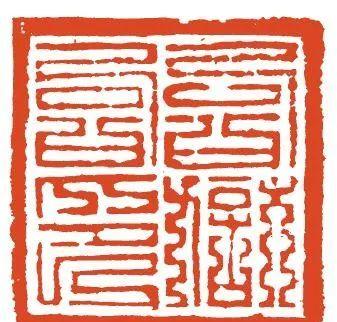
元官印 司獄司印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權,前後近百年(1271——1368)。元代官印除用漢字外,還有八思巴文。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命國師八思巴創立拼音文字,即八思巴文。八思巴文頒行以前,元代官印主要使用九疊篆,如“司獄司印”等印,印文均為标準漢文九疊篆。八思巴創立的新字是從藏文發展而來,吸收了宋印九疊篆整齊勻稱、棱角分明的特點,但并不像遼、金、西夏文字那樣與漢字有一定淵源,如“陝西四川蒙古軍都萬戶府印”等印。八思巴文官印的一大特點就是背款皆為漢字,這是我們識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據。
此外,元代官印印邊比較寬闊,此為元代官印印面構成的一大特點。隋唐官印及宋初官印,印文與印邊往往等寬,宋代中後期印邊開始加寬,至元代竟達印文筆畫寬度的數倍甚至十倍,如“陝西四川蒙古軍都萬戶府印”即為代表。
(二)吾丘衍與趙孟頫的曆史貢獻
明代朱簡曾在《印章要論》言:“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漢,濫于六朝,而朱淪于唐、宋。然而代有作者,其人莫傳。如元則有吾竹房、趙松雪輩,描篆作印,始開元人門戶。國初尚研故習,衰極始振。”明代甘旸《印章集說》言:“至正間,有吳丘子衍,趙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時尚朱文、宗玉箸、意在複古。”以趙孟頫、吾丘衍、王冕為代表的印人,在元代發起了一場複古運動,力挽魏晉以來印章的靡弱之風。
趙孟頫印
在元代,趙孟頫無疑是朝野公認的藝術界乃至整個文壇的盟主,其不僅官居一品,而且在詩文、繪畫、書法等方面均成就斐然。在元代篆刻史上,趙孟頫亦占據着重要地位,他的印學理念不僅影響了有元一代,對後世篆刻的發展亦影響深遠。明代甘旸《印章集說》言:“趙子昂擅朱文、皆用玉箸篆,流動有神,國朝文太史仿之。”(韓天衡《曆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 年)陳琏《印說》言:“圓朱文,元趙松雪善作此體,其文圓轉妩媚,故曰圓朱。要豐神流動,如春花舞風,輕雲出岫。”(此概為“圓朱文”一稱之由來)。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宮道人,中年曾作孟俯,湖州(今屬浙江)人。其書法諸體皆工,被後世稱為“趙體”,其用印多親自配篆由印工镌刻,與吾丘衍風格為近,世稱“吾趙”,二人開創的印章風格,後世稱為“元朱文”。這種字形婉約流美、章法緊湊合度的印風,成為明清文人篆刻創作中的一種重要印式。
吾衍私印
趙孟頫在元代文藝界具有極大的号召力,篆刻上他崇尚“古雅”“質樸”,反對“新奇相矜”“不遺餘巧”的形式流俗,這與其在繪畫上提倡的“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是工無益”的觀念是十分一緻的。(《自跋畫卷》)清代畫家張紳曾言:“大德間,館閣諸公名印皆以趙子昂(孟)為法,所用諸印皆以小篆填廓,巧拙相稱。其大小繁簡,俨然自成本朝制度,不同漢、唐、宋、金相同。”趙孟頫在理論上強調複古,以漢魏印章為法則,但真正反映其篆刻水準的卻是他所開創的元朱文印風,其中滲透了他的審美傾向,元朱文印流暢爽勁的審美效果與其醇和秀麗的書風和頗有古意的畫風相符合。他的朱文印沿用了唐宋官印所通用的那種類似玉箸篆的線條,在強化筆畫的運動感的同時,印文每與印邊相連,并能于疏朗之中捕捉樸茂之氣,給人以穩定和飽滿之感。清代印學家孫光祖在《古今印制》中說:“秦漢、唐、宋皆宗摹印篆,無用玉箸者。趙文敏(孟)以作朱文,蓋秦朱文瑣碎而不莊重,漢朱文闆實而不松靈,玉箸氣象堂皇,點面流利,得文質之中。明以作玺,尤見規模宏壯。”
布衣道士
貞白
與趙孟頫同時的吾丘衍,也是篆印高手,篆書有“當代獨步”“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之下”的盛譽。當時吾丘衍與趙孟頫一起呼籲印章複歸漢魏印式,但從對漢印風格的倡導來說,吾丘衍較趙孟頫更為實際,其為教授弟子所著的《學古編》多由實踐而來,并明确提出以漢印為皈依,讨論了印章中的篆法與章法等具體的操作問題。吾丘衍(1272——1311),一作吾衍,字子行,号竹房,别署布衣道士,開化(今屬浙江)人,寓居杭州。吾丘衍自幼受家學影響,在篆刻方面,其主要精力集中在對漢印的研究上,“吾衍私印”“魯郡吾氏”“布衣道士”和“貞白”都是他的自用印,其中“吾衍私印”采用滿白文處理手法,“魯郡吾氏”和“布衣道士”也可看出對平正渾樸的追求。趙孟頫和吾丘衍均自篆印稿,這自然與二人在篆書上的造詣分不開,且二人所開創元朱文印風,很快成為文人作印的模式,這直接提升了篆刻的文化品位。
魯郡吾氏
(三)吾丘衍和趙孟頫倡導下的元代篆刻
在元代朱文印的演進過程中,端賴吾丘衍和趙孟頫的倡導,元代文人篆刻得到較大發展,尤其是吾丘衍開館授徒,培養了許多弟子,使文人篆刻延續不斷,并在明清兩代成一時風氣。吾丘衍的弟子中,較著名的有趙期頤、葉森和吳叡等,而吳叡最為著名。吳叡(1298——1355),字孟思,号雲濤散人,别署青雲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晚居昆山。吳叡在其師的基礎上又向前跨進了一步,做到了書印合璧,我們可以看到其十餘方自用印,其中朱文印都是圓朱文風格,且篆與刻的水準都相當高,他把小篆“上緊下松”的特色表現的十分突出,且筆畫的提按恰到好處,開了後世鐵線篆的先河。
王冕私印
與吳叡同時的印人還有王冕,其首創以花藥石(即花乳石)刻印。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農,諸暨(今屬浙江)人,出生農家,後從韓性遊,遂為通儒。王冕墨梅最為後世所稱道。王冕又工刻印,明初劉績在《霏雪錄》(卷上)中言:“初無人以花藥石刻印,自山農始也。”軟硬度适中的石材的出現,是元朱文風格得以完美表現的關鍵。郎瑛《七修類稿》載:“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王冕以花乳石刻之。”花藥石易于奏刀,王冕自篆自刻,其印金石氣很濃。
趙氏子昂
吳孟思章
吳叡私印
除王冕外,元代很多畫家都介入了篆刻的創作,如柯九思、虞集、張雨、黃公望、倪瓒、楊維桢、朱德潤、魏元裕、鮮于樞、陸居仁等,均采用吾丘衍和趙孟頫的方法。從他們的印章中可以看出,元朱文印的形式已然确立:印文取小篆、朱文細線、文字連邊……元代文人印流傳下來的很少,但是在篆刻史上的意義十分重大。文人的參與,是中國印章确立藝術立場的标志,是篆刻藝術和實用印章分野的裡程碑,而這種重要的曆史性轉變在元代完成。
四、集古印譜的出現及意義
濮陽
雖然在唐代已有關于“玺譜”的記載,如《舊唐書》之《韋述傳》、姚察《傳國玺》、徐景《玉玺正錄》等,但一般認為集古印譜的出現是在宋代。宋代是大陸金石學的發轫時期,集印成譜即受考古和金石學的影響而興起。清代桂馥在《續三十五舉》中言:“古印無圖譜,宋(仁宗)皇祐初,命太常摹曆代印書為圖。”此後又有楊克一《集古印格》,而《宣和印譜》則成書于稍晚的宣和年間(1119——1125),此譜是奉命官修的一部大型集古印譜。此外還有顔叔夏《古印譜》、姜夔《集古印譜》等。
頫仰自得
漢廣平侯之孫
唐宋時期的集古印譜,僅作為古器物譜錄中的一種,還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審美意識,更沒有對篆刻藝術的指導目的。與文人篆刻同步,元代集古印譜的編輯目的多指向了藝術,趙孟頫在《寶章集古》的基礎上“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彙為譜錄,曰《印史》。元代文人篆刻在強有力的理論指導下,又有為數甚多的集古印譜作為典範,更有一代又一代有識之士的艱辛實踐和大膽嘗試,最終使元代文人印章形成了兩大格局:一是仿漢印式,一是元朱文印風。仿漢印式主要是指仿漢白文印,元代篆刻家在創作這一類印時大都能追求漢印的原本效果,其中集古印譜起了很大的中介作用,在吾衍《古印式》和趙孟頫《印史》之後,又有楊遵《楊氏集古印譜》、吳叡《漢晉印章圖譜》、葉森《漢唐篆刻圖書韻釋》等多種集古印譜行世,這些集古印譜的編輯本就帶有目的性,則其對印壇的指導示範意義也就更為明确、更為具體。應該說元代篆刻家完成了由古到今、由技術到藝術創作這些實質性的轉換,為明代篆刻藝術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李剛田、馬士達主編《篆刻學》,202頁——203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
五、風格特殊的元代花押印
聊消搖兮容與
在元代的私印中,還有一類被稱之為“花押”的印章頗具特色,花押是一種專門用以簽押的書體。元末明初的陶宗儀說:“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按:周廣順二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辭位,诏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字用印之始也。”(明許令典《甘氏印集·叙》,轉引自黃惇《中國古代印論史》,149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
王元章
會稽佳山水
花押其實就是代表身份的一種符号,是以有簽字畫押之說。花押在宋朝以前就已出現,如著名的韋陟“五朵雲”。(據陶宗儀所說,花押入印始于五代時的後周)宋以後,上至天子,下至百姓,花押被廣泛運用,并逐漸入印。而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後,由于對于漢字的運用不能熟練無礙,故而隻能以印代之,這大概就是元代押印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元押的格式常見的有正方形、長方形、圓形等形狀,還有葫蘆、鐘鼎、花瓣、魚、兔等形,其中長方形的元押與秦漢半通印大小相近,上為楷書,下為花押,或雜以八思巴文的“記”字,印文多作朱文,其印章的紐制也變化多端。總的來說,元押盡管是沿着實用印章這一路線發展的産物,但其藝術和審美價值并不在宋元文人印章之下。(李剛田、馬士達主編《篆刻學》,119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