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世說新語》(下稱《世說》)研究史上,楊勇的《世說新語校箋》無疑有着極重要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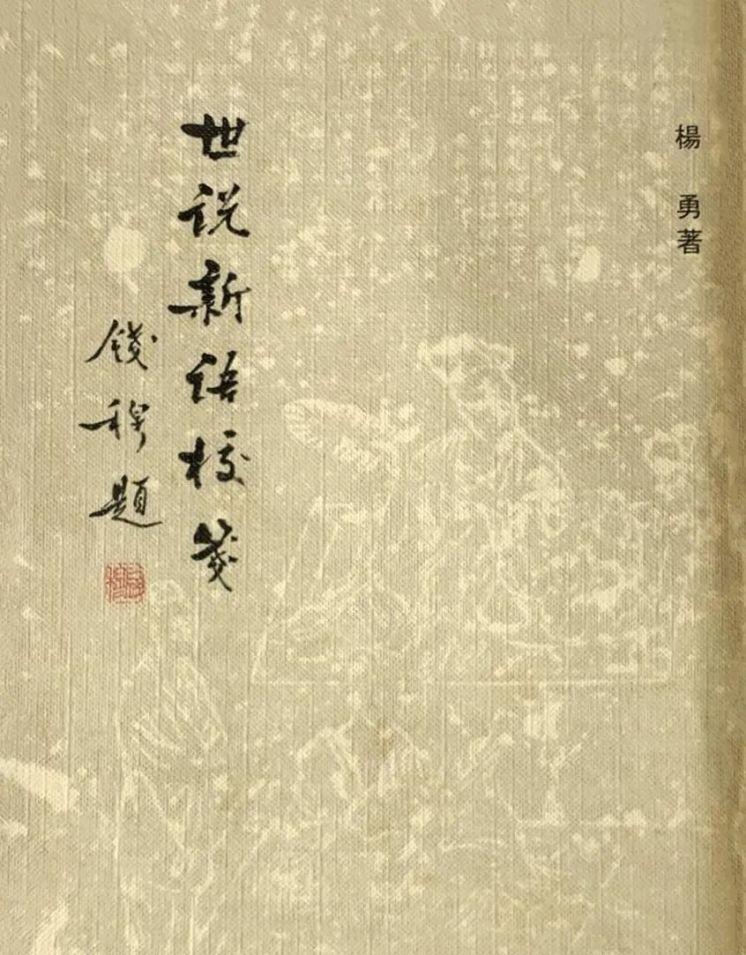
香港大衆書局版《世說新語校箋》
1969年,正值大陸的“文革”運動山呼海嘯、如火如荼,學術研究幾告停滞之時,此書在香港悄然問世,旋即在港台及海外漢學界掀起了一波“世說熱”,一時洛陽紙貴不說,還帶動了海外的《世說》翻譯及研究。比如,飽受争議的法國漢學家布魯諾·貝萊佩爾(Bruno Belpaire)的法譯本(1974年),以及好評如潮的美國漢學家馬瑞志(Richard B.Mather)的英譯本《世說新語》(1976年),便是在楊著出版的基礎上先後完成的。而差不多十四年後,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1983年)及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1984年)才陸續在大陸出版。
從《世說》研究及傳播史上來看,楊著《世說新語校箋》可謂導夫先路,獨領風騷,謂其當代之臨川功臣、《世說》羽翼,不為過矣。
楊勇(1929-2008),字東波,浙江溫州永嘉人。早年曾讀過私塾,成年後做過國小教員、永嘉警察局文員,後考入江西陸軍軍官學校,國共内戰時參加過平津戰役,被俘後遣散回鄉。1951年3月赴香港求學,師從錢穆、伍叔傥、饒宗頤諸大師,1959年畢業于香港私立新亞書院中文系,獲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1968年獲香港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嗣後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曆任助教、副講師、講師、進階講師及台灣高雄師範大學研究所教授等職。一生于古籍校勘最為用力,著有《世說新語校箋》《陶淵明集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楊勇學術論文集》等。
楊勇先生
1
楊氏《世說新語校箋》(下稱《校箋》)于1969年9月由香港大衆書局印行,一度引起轟動。著名學者饒宗頤為之作序,稱其書“服膺二劉,寝饋六代,旁鸠衆本,探赜甄微,網羅古今”;鄭骞稱其“取材宏富、體大思精”;[1]柳存仁謂其“巍然巨編”、“精宏之作”[2];周法高謂其“出版最早,有開創之功”;[3]美國學者馬瑞志(Richard B.Mather)稱其為“裡程碑式的傑作”[4];好評盛贊,不一而足。
兩年後,1971年10月,台灣明倫出版社再度印行。1976年,台北正文書局又加翻印,《出版說明》稱此書“訂正注解,用力勤堅,徹底恢複了原書的面貌。……實為近年來學術界之絕大貢獻。問世以來,将近七載,翻印盜版,不下數萬冊,頗為學術界所喜誦”。[5]2000年5月,台北正文書局又出修訂版。2006年,北京中華書局又引進正文書局版權,于是年6月出版,首印4000套,未及一年售罄;2007年5月又重印。
中華書局版《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
研尋楊氏《校箋》的幾個版本,加上2003年正文書局出版的《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6],可窺楊氏“世說學”之整體風貌。以下概要言之。
相比以往的《世說》著述,楊氏《校箋》之貢獻略有三端:
其一,體例創新,讀者稱便。
衆所周知,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動筆在先,成書更早,然若以出版順序言,楊氏《校箋》可謂後來居上,捷足先登,故客觀上成了對《世說新語》的首次完整校勘和箋注。是書問世于香港,沐浴時風,故在體例上頗有創變:
(一)《世說》劉孝标注文,一向與正文參行,而楊氏《校箋》則将正文與注文分開排印,對于讀不慣古書的一般讀者而言,确實更為簡便易入。
(二)充分利用新式标點符号,如在每條正文之上,一律加上阿拉伯數字表明其次第,号數之起迄,則以本篇為機關。同時,又于注文之上,加[一][二][三]等依次标明其位置;如此全書一千餘條及每篇條數一目了然,檢索浏覽頗為友善。
(三)是書又把《世說》劉注中“别見”“已見”之例,一一注明出某篇某條,如《德行》第2條劉注“子居别見”,楊氏注雲:“别見《賞譽篇》1注。”又如《政事篇》第1“陳仲弓為太丘長”條,劉注“陳寔已見”,楊箋曰:“陳寔已見《德行篇》6注一。”便于讀者前後互見。
楊氏并闡明其注例說:“孝标注《世說》,有‘已見’、‘别見’及‘已别見’例。已見者,其人行事已詳見于前也。别見者,其人行事别在後詳之也。已别見者,必有二人以上,或已見于前,或别詳于後也。……全書如此,其例嚴密,法自《漢志》,孝标仍之。”[7]
此一段說明,深思密察,不唯發明孝标之注例于千年之後,同時亦開啟楊氏《校箋》一大體例,對于《世說》箋注學不啻為一大貢獻。
《楊勇學術論文集》
其二,校箋詳贍,不避繁難。
《世說》之校注,代不乏人,成果顯著,蔚為大觀。近代以來,先後有李慈銘、劉盼遂、李審言、程炎震、沈劍知諸家,次第箋注,雖各擅勝場,然除餘嘉錫外,鮮有通校通注全書者。
楊著初版即參考征引各類古籍及相關研究文獻二百四十餘種,校箋凡二千八百餘處,約二十五萬言;2000年修訂本由台北正文書局出版時,又“修訂九百餘處,新增三萬言”;2006年中華書局再版,“又改正增益八十餘處”,書後附有汪藻《世說新語人名譜校箋》《世說新語人名異稱表》《世說新語人名索引》等資料,足稱完備。
數十寒暑間,楊氏幾易其稿,可謂孜孜矻矻,鞠躬盡瘁,此一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治學精神令人動容,極可欽佩。
其三,考釋精審,足資借鏡。
楊著雖不以考史見長,考辨亦頗精審可觀。其初版《自序》稱“晦則明之,略則詳之;或疏義慶之奧,或釋孝标之滞;集先賢之成說,申未竟之緒餘”,洵非虛語。
如《德行》45“吳郡陳遺”條,孝标于陳遺下,自注“未詳”。楊箋則引《南史·吳逵傳》:“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辄錄其焦以贻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随。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号咽,母豁然即明。”此亦可補劉注之失。
正文書局版《世說新語校箋》
楊著對詞語的考釋亦頗可觀。如《文學篇》第41條“劇談”一詞,楊箋曰:“劇談,窮之以詞,苦相诘難,輕薄之詞也。”又引《宋書·謝靈運傳》《史通·言語篇》《酉陽雜俎》諸文獻以證之,得出的結論亦令人信服。再如《德行篇》第14條釋“私起”、同篇第33條釋“阿奴”、《言語篇》第40條釋“隐”等,皆可見其學識。
其書又廣征博引古籍新著,以為考史論世之資,于魏晉六朝人文名物之分疏,社會風習之研判,多有前人未發之覆。柳存仁稱:“本書之成就,據愚見所及,似箋尤勝于校。”“其于研究中國中古時期社會生活,文化活動,語言風尚,宜可多所取資”。[8]确為平情之論。
2
然而,與其獲得的巨大成就和影響力适成對比的是,楊氏《校箋》存在的問題也不容無視。特别是作者在校勘上采取的方法及造成的缺憾,尤須秉承實事求是之精神予以揭示及評骘,如此方可辨明是非,以裨後學。
竊以為,楊氏《校箋》至少在以下諸方面大可商榷:
其一,徑增條目,淆亂原著,有違版本整理之通則。
衆所周知,今傳《世說》善本,無論影宋本還是明袁褧本,全書條數皆1130條,并無差異。《世說》劉注雖遭宋元人删削,而《世說》正文,則“尚稱全璧”。清人葉德輝曾廣覽類書,輯得《世說佚文》八十餘則;劉盼遂亦曾“于葉輯外,複得若幹則,皆今本所無,予舊依類編入《世說》各篇”;然,自唐寫本《世說新書》殘卷問世後,足證這些所謂“佚文”,“必非臨川原本,實出于注語及臨川别書矣。然不得唐本,迄難能證成此說,此寫本可以破從來佚文之謬說也”。[9]
《百鶴樓校箋批注古籍十七種》
楊氏自然讀過葉、劉二氏之書,然其《校箋》初版時,卻根據日本前田氏所藏宋本書後所附汪藻《世說考異》,增補四條材料入《世說》正文[10],分别是:
1、王丞相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為之祈禱者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窟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見《校箋·德行》48。楊箋曰:“勇按:右條宋本不見,《考異》有,而與本篇29混;今分置之,姑系于此。并見本篇29校箋。”又,《德行》29校箋:“勇按:《考異》當是宋代另本如此,必有據。今錄其異者另作一條,置于篇末。”)
2、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歔欷,人有懷土之切;向晚,又吹,賊并棄圍而散走。或雲是劉道真。(見《校箋·雅量》43。楊箋曰:“勇按:右條正文、注文,宋本皆無,《考異》有,并雲:‘右前卷所無,邵本收在《雅量門》。’今據錄,姑系于此。”)
3、祖士少道王右軍:“王家阿菟,何緣複減處仲?”(見《校箋·賞譽》157。楊箋曰:“勇按:右條宋本無,《考異》有,雲:‘又前卷所無。’今度其語意,當入《賞譽篇》,姑系于此。”)
4、王大将軍初尚主,豫武帝會,既升殿,覺上不平,如坈穽中行。乃顧看四坐,無出其右者,意尋得定。(見《校箋·纰漏》9。楊箋曰:“此條宋本《世說》不見,《考異》載之,并雲:‘右前卷所無者。’當是宋時别本有此,而晏、董所據者無此。今當錄入。度其文意,姑系于《纰漏篇》。”[11])
洪氏出版社版《世說新語校箋》
如此一來,則《世說》正文憑空多出4條,共計1134條(見楊著初版《自序》)。而事實上,汪藻的《世說考異》,非考《世說》正文之異文,乃考史敬胤《世說》選注宋代各本之異文也。“前卷”乃指十卷本的前九卷即《世說》正文,而第十卷則是作為“附錄”系于書後的史敬胤《世說》選注。故此,楊箋所增入的四條,與《世說》祖本毫無關系[12]。
楊氏将其闌入原著,實在太過武斷而大膽。以《德行篇》所增第48條為例,此則本出劉義慶《幽明錄》,語涉志怪,與《世說》體例殊乖,以之增入本文,猶南轅北轍,去之是以更遠。今有學者亦引用楊著增補的四則以為《世說》本文,亦不考之甚。
楊著此一做法,屬于鄭樵所謂“以今之書,校古之書”(《通志·校雠略·編次必謹類例論》),本無理據,學術上亦冒極大之風險。本來寄希望于楊氏能在修訂時一改此誤,無奈修訂版唯将妄增之《德行篇》第48條删去而已,其餘三條依然故我[13]。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其二,輕改原文,臆增劉注,有違古籍讎校之通例。
楊著初版後,學界贊譽頗多,如柳存仁稱其“巍然巨編”,“雖以唐宋本為其校雠之底本,其取決一本客觀之推斷,而無佞唐宋之用心于其間。其自序雲:‘苟是矣,雖則類書小本不敢遺;有所未安,則雖唐卷宋本不敢信。’其忠于真理之态度如此。”[14]何敬群稱其書“嚴正了《世說》的文字,擴大了《世說》的領域”,“恢複了二劉原來的面貌”,“雖不能說是絕後,實可說是空前的佳作”。[15]
《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
然揆諸事實,這些評價未免過于溢美。
首先,楊氏雖然在《凡例·二》中明言以宋本和唐寫本殘卷為“底本”,參校他書;又在初版《自序》雲:“卒依朱子《韓文考異》之法,一以《世說》文章之平淡清遠,及他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類書小本不敢遺;有所未安,則雖唐卷宋本不敢信。”
“不敢遺”、“不敢信”固然可嘉,但在具體操作中,卻變成了“大膽改”與“斷然增”,這就不能說是“一本客觀之推斷”了。本來以宋本唐卷作底本,已存在底本不一的問題,二者同為底本,則校勘的結果隻能是形成一個非唐非宋的新版本。
不過話又說回來,據唐卷改宋本,畢竟尚有版本依據。如《規箴》第22:“王大語東亭:‘卿乃復倫伍不惡。那得與僧彌戲?’”“倫伍”,宋本作“論成”,楊箋據唐卷改,并加按語曰:“倫伍者,品論人物之次第也。時人品論人物高下,猶軍伍之有先後也;故有難兄難弟之言。”此種改訂,有理有據,值得肯定。
唐寫本《世說新語》殘卷
但根據與《世說》無關的其它文獻來擅改《世說》原文及劉注,就實在讓人匪夷所思了。如《德行篇》第1“陳仲舉言為士則”條,劉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裡赴吊。常豫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幹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鬥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酹酒畢,留谒即去,不見喪主。”
楊箋則據《後漢書·徐稚傳》注引《謝承書》,徑改三處:将“及其死,萬裡赴吊”改作“有死喪,負笈赴吊”;将“徑到所赴冢隧外”,“赴”改作“起”;又于“以水漬綿”後,增“使有酒氣”四字。
又如《賞譽》第55條:“大将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楊箋則據《晉書·王羲之傳》,改為“汝是我家佳子弟”,多一“家”字,與“佳”同音,語義反不如原著,類似擅改,殊無謂也。
本來此種問題,隻要忠實底本,再加校記說明之,并不難解決,即使要在原文上修訂,亦可采取原文與改文并存之方式。
查楊著《凡例·五》,亦稱:“宋本及唐卷中之誤文,有保留價值而不得删去者,則将訛誤之文用小一号字加圓括号排列;改正之文,則用同号字排列于誤文之下,并加方括号以别之。”若真能如此,亦可避免徑改原文之弊。
日本尊經閣藏宋本《世說新語》
可奇怪的是,泛覽楊著全書,卻幾乎看不到“用小一号字加圓括号排列”及“方括号以别之”的情況,大部分倒是徑改原文,于校箋中加以說明而已。如《方正》20宋本作:“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曰卿之不置。”楊著則徑删“曰”字,僅在校箋中說:“庾下,宋本有‘曰’字。袁本無,今從袁。”讓人懷疑此一凡例究竟是被作者忘記了,抑或本來就是寫與人看,自己根本不屑為之呢?
夫校雠之學,自有家法,要在尊重古本原貌,考鏡異同,辨明源流。劉向《别錄》釋“校雠”說:“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雠也。”(《太平禦覽》卷六一八引)
著名史學家陳垣在談及“對校法”時說:“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别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16]
“校異同,不校是非”、“不參己見”,唯有如此方能異同立見,是非立判。
《校勘學釋例》
胡适亦曾指出:“校勘學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異同,然後考定其是非。是非是異文的是非,沒有異文,那有是非?向來中國校勘學者,往往先舉改讀之文,次推想其緻誤之由,最後舉古本或古書引文為證。這是不很忠實的記載,并可以迷誤後學。其實真正校書的人往往是先見古書的異文,然後定其是非。他們偏要倒果為因,先列己說,然後引古本異文為證,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測而忽得古本作印證似的,是以初學的人看慣了這樣的推理,也就以為校勘之事是應該先去猜想而後去求印證的了。”又說:“一代有一代的語言習慣,不可憑借私見淺識來妄解或妄改古書。”[17]
以這些觀點移諸對楊氏《校箋》的考察,常有“不幸言中”之感。
楊氏《校箋》存在的問題,早前已有論者指出。如徐道鄰《評世說新語校箋》一文,便羅列楊著的八個問題,其中就有涉及版本校勘的,可惜并未擊中要害[18]。
比較有力的批評來自唐翼明。在《評英譯本》一文中,唐氏順帶指出楊勇徑改原文的缺失兩處:
一是《言語篇》第31條記周顗的慨歎,宋本作:“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楊箋據《藝文類聚》《太平禦覽》《景定建康志》所引《晉書·王導傳》《敦煌本殘類書》新亭條等資料改為:“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但‘正自有山河之異’并非不通,宋本必有所承,擅改難免武斷之譏。最好是兩說并存。Mather譯本,正文仍據宋本,而在注解中指出其他材料作‘舉目有江河之異’。”
一是《文學篇》第六條:宋本作“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楊箋據《北堂書鈔》《太平禦覽》所引古說,定為:“晏聞弼來,乃倒屣迎之;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這當然很有道理,但其中也頗有令人為難的地方,因為所引五段引文沒有兩處是完全相同的,結果隻好由校箋者折中酌定了。對于校訂古籍而言,這樣做不能不說包含着某種風險。Mather譯文該條仍據宋本,未作改動,這種慎重态度是可貴的”。[19]
《太平禦覽》
唐氏還指出,楊著“常常太果于判别,以己意斷之,對原文徑加增改。這在校勘學的角度來看,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風險”。[20]
遺憾的是,這些非常中肯的批評意見,并未引起楊氏的重視。是書于2000年在台灣、2006年在大陸兩度再版,先後修訂近千處,作者時而自歎“視初出面目一新矣”,時而感慨“比前作又勝一籌矣”,卻終未能打破舊局,再創新篇。
或許楊氏自己未嘗不感到壓力,故其在修訂本《卷前》新增《世說成書及其改删之迹》一節,闡述其校勘之理路雲:
樂天出版社《世說新語校箋》
唐卷自《規箴》4孫休好射雉條起,至《豪爽》13桓玄西下條止,凡四篇五十一條,正文與宋本異者有數十字,注文異者尤多。《規箴》6注引《管辂别傳》,唐卷多出七十餘字,《規箴》26注多出二百六十餘字,《夙慧》2多出五十餘字,《夙慧》3注多出九十餘字,以及其他零星散見者,合約五百餘字。若以此推,唐卷被删者全書不下萬言。則知今傳《世說》非二劉之原作明矣。
然唐卷雖為古,傳鈔已二百餘年,訛誤累累,又不得視為本真。此不獨文字之誤奪雲然,而其門第亦數變矣。宋初此等卷子比多,晏殊諸人所藏者,即當時之足本善本也。唯唐卷之可貴,為未經宋人之增損,文字清新,能見六朝人神韻。如《規箴》14“郡家事”被改為“郡事”,22“倫伍不惡”被改為“論成不惡”,24“諷誦”下增“朗暢”二字,不惟有失原意,而文章風神亦全變矣。最為可惜。雖然,前田氏藏宋本仍不失為今傳《世說》之最佳本也。
隻可惜,楊氏明知“唯唐卷之可貴,為未經宋人之增損,文字清新,能見六朝人神韻”,宋本“不失為今傳《世說》之最佳本”,自己又以唐卷宋本為底本,卻還是犯了宋人改删增損古本之錯誤,未能遵守古籍整理之基本原則,緻使留下一部輕改臆增之“楊氏本”。雖然其用力不可謂不深,初衷不可謂不善,然終究讓人在參考引據時手足無措,如今兩岸學者在征引《世說》本文時,大多以嚴格忠實于古本的“餘疏”、“徐箋”為據,就是明證。
正如有人戲稱的,“明明可以更新檔加更新檔,何必非要拆線?”對于一生以古籍校雠為職志的楊氏而言,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明倫出版社版《世說新語校箋》
3
其三,楊氏對于《世說》古本面貌,亦有誤判失考之處。
楊氏《世說新語“書名”“卷帙”“闆本”考》一文,論及《世說》書名時,對餘嘉錫所謂“世說”乃“世說新書”之“省文”一說不以為然,認為:“今義慶之書,既非據向書而成,則其不得為‘《新書》’明矣。其《史通》《酉陽雜俎》《通典》以及《禦覽》《廣記》中所引,或作‘《世說》’,或作‘《新書》’者,則據錄之本不同耳。”[21]此說甚是。
然楊氏又加按語稱:
“《新書》”之名,殆起自梁陳之間,宋本《世說新語》附汪藻《叙錄》曰:李氏本《世說新書》,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顧野王撰。
如此一來,憑空又多出一部顧野王所撰的《世說新書》來![22]而事實上,楊氏顯然斷句有誤,而這個錯誤實來自王利器的《跋唐寫本殘卷》[23]。
《唐寫本世說新書注 宋本世說新語注》
考汪藻《叙錄》“顧野王撰”四字之後,尚有“顔氏本《跋》雲:諸卷中或曰《世說新書》,凡号《世說新書》者,第十卷皆分門”,共二十七字。細玩文義,蓋指顧野王所撰顔氏本跋語也。因為認定有一部顧野王所撰的《世說新書》,楊氏緊接着的一個判斷更加“大膽”:
蓋《隋志》所錄者,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标《世說注》十卷,必屬分别單行之本,故而分别入錄;今顧野王所撰,則将孝标注散附義慶書中,使兩書合行,通為三卷之本,故名“《世說新書》”,今唐寫本《世說新書》殘卷款式即然。
楊氏又說:
《南史·劉義慶傳》雲“所著《世說》十卷”,此乃梁陳間,有合二劉書撰為《新書》者,唐世頗多十卷之本,《南史》殆是據《新書》入錄。《新書》既将孝标注散入義慶書中合行,民間流傳,寖不知有孝标單行本矣。[24]
而事實上,《隋書·經籍志》稱“《世說》十卷,劉孝标注”,并非“劉孝标《世說注》十卷”,也就是說,并不存在楊氏所謂“孝标單行本”。
“《世說》十卷,劉孝标注”這一表述,實已隐含着這是一個《世說》正文和劉孝标注文合而為一的版本,孝标當初作注時也肯定是随文加注,不可能自己單獨謄抄一部不含《世說》本文、隻有注文的名為《世說注》的“單行本”。當然就更輪不到顧野王來“将孝标注散附義慶書中,使兩書合行,通為三卷之本”,且以《世說新書》冠名以與原書相差別了![25]
啟業書局版《世說新語校箋》
對《世說》卷次的判斷,楊氏亦有失誤。如其嘗曰:“汪藻《叙錄》尚有二卷本、九卷本、十一卷本、三十八篇本、三十九篇本、四十五篇本,殆皆藏書家好奇标新,合并附益之事。”而事實上,根本不存在所謂“四十五篇本”。[26]
此說最早見于宋紹興八年(1138)董弅《跋》語,其文說:“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厘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餘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今按:此處“四十五篇”,蓋指敬胤所注且與前九卷“重出”的四十五事,非門類之謂也。汪藻引王仲至《跋》雲:“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載,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糾缪。右二章小異,故出焉。”可證。此意王能憲已有揭示,惜乎楊氏未察也。[27]
第四,楊氏認為“清談原是談嘲”的觀點,亦極難成立。
楊氏晚年耽思清談之起源問題,2002年夏,撰成《論清談之起源、原義、語言特色及其影響》一文,收入《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中,其論證清談起源于戰國談嘲,要點如下:
唯一書業中心版《世說新語校箋》
1、“滑稽”一名,既為清談之同義詞,其始則見于《史記·滑稽列傳》。(第16頁)
2、總上而言,清談初名當是“滑稽”,其意在諷谏規勸,其辭則俳優。後又名之曰“戲”者,以其語存嘲啁、諧谑之色也。……其視今人常言“清談老莊”或“魏晉清談”之意,特雲泥之别矣。(第20-21頁)
3、陳寅恪曰:“世之所謂清談,實始自郭林宗,而完成于阮嗣宗也。”……餘以為《世說》中所見清談實錄,除談玄學及人物評論外,尚有滑稽、诙啁一類,時人謂之“清談”者,當是指此也。(第32頁)
4、又湯用彤《讀人物志》曰:“魏初清談,上接漢代之清議,其性質相差不遠。其後乃演變而為玄學之清談。蓋談論既久,由具體人物以至抽象玄理,乃學問演變之必然趨勢。”此亦不知清談原是談嘲,而以談玄為人物評鑒之後發事耳。其誤解與陳寅恪同。(第32頁)
在2006年校箋《再版序》中,楊氏再申此說:“夫清談,原是談嘲,起自戰國初年之淳于髡,太史公以其滑稽多辯,喜隐語,乃與楚之常以談笑諷谏者優孟,與秦之善于言笑者優旃合為《滑稽列傳》,謂足以和悅人主,談言微中,亦以解紛亂也。”“其意與滑稽全同,則清談即是談嘲無疑也”。[28]又論湯用彤、陳寅恪二氏以談玄及人物評鑒為清談,稱:“二公之說似可商榷。今以清談發展之事實言,則清談并不出于清議,而清議适出于清談也。”[29]
如此“自鑄偉詞”之論說,新則新矣,銳則銳矣,卻也将清談之是以為清談,及其促其産生之時代背景和思想淵源,一概抹殺了。楊氏此說,蓋為論證清談早于清議,然以談嘲排調一脈概括魏晉一代學術文化思潮及其精彩表現,實在難免以偏概全、過度闡釋之譏。
《世說新語研究史論》,劉強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要言之,楊氏《校箋》可謂筚路藍縷,草創艱難,其有功于《世說》學之光大自不待言,這是我們必須肯認的事實。
但由于作者撰作伊始,便為個人的再造善本的抱負所指引,而後又因“交相稱美”的現實[30],而未能反躬自省,善納雅言,終于使其勞瘁半生的學術成果瑕瑜互見,給人以“盡美矣,未盡善也”的觀感。
楊氏《世說》學的得失利弊,不免讓人産生著書立說“談何容易”之歎。往者已矣!筆者草撰此文,非為唐突前賢,求備一人,實亦用以自警自勵,并與知者共勉也。
上下滑動檢視注釋
注釋:
[1] 鄭骞書評,原載台北《學苑》第七卷第六期,1970年6月。參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台北:正文書局,2003年,第103頁。
[2] 柳存仁書評,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華文化研究學報》第三卷第一期,1970年。參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05頁。
[3] 周法高:《讀世說新語劄記》,原載台北《書目季刊》第24卷第2期,1980年9月16日。參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33頁。
[4] 參見馬瑞志:《法譯本審查報告》,範子烨譯,《讀書》2002年第4期。參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65頁。
[5]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76年,第1-2頁。
[6] 最早知道楊勇先生,是通過範子烨先生的《世說新語研究》,後者對楊氏多有征引且執弟子禮,讓我對楊先生心生敬意。2002年3月,正在複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我收到一份厚厚的郵件,打開一看,竟是子烨先生贈送給我的一部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封面已經脫落不見,扉頁上有兩行鋼筆字:“子葉同學參用/楊勇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四日。”這是我得到的第一部楊勇先生的校箋本(2013年又從陳尚君老師處獲贈1971年10月台灣明倫出版社印行的本子),如奉拱璧。2003年3月間,不意又收到楊先生寄自香港的《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兩冊,并附一函雲:“劉強博士大鑒:頃接範子烨博士來函,知先生正在撰寫《世說新語研究史》一書,十分難得。并囑寄上近作《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以為佐治《世說》之用。查此書研者甚多,真知灼見者少,拙編或可提許多資料,請先生選擇。我有修訂本乙函(兩冊)前已寄存貴校,亦可參考。匆此并祝/文祺 楊勇三月十二日。”“另乙冊贈貴校圖書館,請回信收據。勇又及。”拜讀這封原子筆寫于便條上的來信,深為楊先生提攜後進之忱所感動,先生手迹,至今珍藏。
[7]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45頁。
[8] 柳存仁書評。參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10、113頁。
[9] 參劉盼遂:《唐寫本跋尾》,《清華學報》2卷2号,1925年。
[10] 《凡例·十一》雲:“《考異》中有三條正文為宋本所無者,此系宋時别本《世說》所有,其出于二劉原書無疑,不能廢棄。今度其文意之相近,系于《雅量篇》《賞譽篇》《纰漏篇》之末。”加上《德行篇》增入一條,正好是四條。
[11] 引文據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再版本。
[12] 詳參拙文《史敬胤的選注》,曾在2016年廈門大學舉辦的第十二屆文選學年會上宣讀。見拙著《世說新語研究史論》第一章第一節,複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13] 按:此條是以被删,源于柳存仁書評的商榷。然柳氏不僅未曾指出楊著妄增原書之失,反順着楊氏的思路說:“疑此《考異》别出之五十字系錯簡,當在‘併當箱箧’及‘長豫亡後’兩句間。”(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08頁)楊氏雖在修訂版中改《初版自序》“一千一百三十四條”為“一千一百三十三條”,卻不僅沒有如柳氏所建議在該條正文中增補此段,且又在《德行篇》末尾删去了這莫須有的第48條。足見楊氏亦未必以柳氏之說為然。遺憾的是,楊氏并未将另外增補的三條也一并删去,以緻永久留下了版本上的一大瑕疵。
[14] 柳存仁書評,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05頁。
[15] 何敬群書評,原載《香港珠海書院學報》第四期,1971年7月。參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 第114頁。
[16] 轉引自胡适《元典章校補釋例序》一文。參陳垣:《校勘學釋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頁。
[17] 胡适:《元典章校補釋例序》,見陳垣《校勘學釋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4頁。
[18] 徐道鄰:《評》,原載《香港明報月刊》82期,1972年5月。參楊勇編著《論文集》,第123-126頁。
[19] 唐翼明:《評英譯本》,《讀書》1986年第2期。參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58頁。
[20] 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武漢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頁。
[21]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41頁。
[22] 關于《世說》書名,竊以為台灣學者馬森所論最為詳明:“臨川王與劉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後,向為元王五世孫,義慶為向兄陽城節侯安民十八世孫。義慶書成,即以其先世亡書之名以名之。至劉孝标做注時,猶稱《世說》。以顧野王撰顔氏本《跋》觀之,梁、陳間又有題作《世說新書》者行于世。以劉知幾《史通》所言觀之,則隋唐之際或有題作《世說新語》者行于世。蓋自是三名并行,故唐、宋人修史稱《世說》,唐寫本及段成式《酉陽雜俎》稱《世說新書》,劉知幾《史通》稱《世說新語》。”參馬森:《世說新語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圖書館藏,1959年碩士論文未刊稿,第1頁。
[23] 原載《圖書季刊》新6卷1-2期合刊,1945年。
[24] 以上三段引文,均參見楊勇:《〈世說新語〉書名、卷帙、闆本考》,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第8卷第2期,1976年。亦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41、43、44頁。
[25] 按:楊氏的這一誤判也影響了後來學者的判斷,蕭虹就采用了楊氏的說法,稱:“早期書名《世說新書》依汪藻之見,始自梁代顧野王(519-581)。”(《世說新語整體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頁。)範子烨亦曾征引楊氏觀點并指出:“據此,創造《世說新書》這一書名并将劉注本《世說》改編為三卷的,可能就是顧野王。……可能是顧野王對《世說》原書作了一次整理,而為與原本相差別而仿效劉向校書慣例的結果。”參見《〈世說〉〈續世說〉〈世說新書〉》,《書品》2001年第2期。
[26] 按:受楊氏影響,蕭虹也以為“有過四十五篇本,末卷大抵重複以前内容”。見蕭虹《世說新語整體研究》,第18頁。
[27] 王能憲按雲:“此本四十五事中有二事為前九卷所無。又據汪氏《叙錄》,另有他本第十卷凡五十一事,其中三事為前九卷所無。”見氏著:《世說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頁。
[28]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一冊,第13-14頁。
[29]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一冊,第16頁。
[30] 今按:楊氏在《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的《後記·餘言》中說:“我的《世說新語校箋》有這麼九位高賢一緻肯定,交相稱美,其書品位不問可知。也着實增加了我書之聲價。”而事實上,九篇文章,專門的書評僅有鄭骞、柳存仁、何敬群、車柱環、徐道鄰五篇,其中徐道鄰書評主要持批評意見,唐翼明的文章也頗有微詞,實在談不上“交相稱美”。又,何敬群、車柱環的書評都提到《言語篇》53條:“庾稚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雲雲。楊箋曰:“庾稚恭,當作庾叔預。武帝,當作成帝。《晉書·庾翼傳》翼卒于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五十一。則武帝在位(265-289)期間,翼尚未出生,不得以毛扇獻之明矣。”兩人都認為這是楊勇的考訂成果而大加稱賞。實則這條考證出自劉盼遂的《世說新語校箋》,王利器《世說新語校勘記》亦承之,且庾翼的年齡,劉、王二氏所校不誤,皆作年四十一,楊箋則誤作五十一。楊氏對此一“謬贊”未作任何解釋,亦可見其當時之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