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訪談錄》收錄了20年漫長歲月中的18篇訪談文章。在這些訪談中,石黑一雄将自己的創作過程與自我認知演變闡釋得一清二楚。在離鄉三十年後的1989年,石黑一雄回到日本,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過一場十分精彩的對談,涉及閱讀寫作、東西方文化等話題,兩人你問我答,交流真誠而熱烈。對談文章也收入了訪談錄中,本文為書中節選,以飨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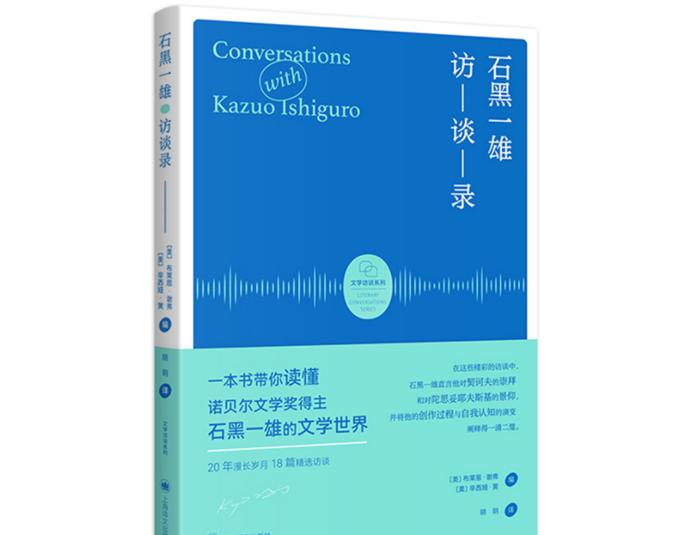
《石黑一雄訪談錄》,[美]布萊恩·謝弗 辛西娅·黃 編,胡玥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石黑一雄、大江健三郎
大江:你這麼問很有意思,因為我覺得你的獨特之處正在于你很好地掌控了與作品所展現的年代和人物間的距離。這些作品全都有着鮮明的風格,雖然從更深的層面來說,它們彼此關聯。是以很感謝你對于我作品中筆調和距離的評價。
我認為你剛剛提及的幽默問題非常重要。這是我差別于三島由紀夫的地方之一。
三島由紀夫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學傳統中,而且還是傳統的中心——東京或者京都之類的城市傳統。
我來自更偏遠的傳統,是四國島那樣的偏遠角落。那是個極其古怪的地方,有着悠久的虐待傳統,屬于傳統文化鞭長莫及之地。
我認為我的幽默就是居住在那樣一個地方的人才會有的幽默。
三島由紀夫對于他的幽默信心滿滿,那麼準确來說,他的幽默是中心的幽默,而我的幽默是邊緣的幽默。
三島由紀夫
石黑:你對三島由紀夫的感受讓我覺得很有意思。在英國,經常有人問到我三島由紀夫——應該說是一直,記者們都會問。因為我的日本背景,他們指望我是三島由紀夫專家。三島由紀夫在英國家喻戶曉,或者說在整個西方都是如此,主要因為他的死亡方式。
但是我也懷疑,這是否因為三島由紀夫在西方的形象證明了西方人對于日本民族的某些成見。這就是我說他更容易被西方讀者接受的部分原因。他符合某些特征。當然,其中反複提到的就是切腹自殺。他在政治上非常極端。
問題在于三島由紀夫在西方的整體形象并不能讓西方人對于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形成正确的認識,反而讓人們固守偏見,不肯改掉對日本人非常膚淺的刻闆印象。許多人似乎在某種意義上把三島由紀夫視作典型的日本人。
當然,我從來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因為我本人對三島由紀夫也知之甚少,對現代日本知之甚少。但這就是我得到的印象——在西方,他被用來印證一些相當負面的成見。
我想知道你對三島由紀夫和他的死亡方式的看法。這對日本人民來說意味着什麼?對于你這樣一位聲名顯赫的作家來說又意味着什麼?
大江:你剛剛關于三島由紀夫在歐洲接受情況的評論非常準确。三島由紀夫整個一生,當然包括切腹自盡的死亡方式,就是一種意在展現日本人典型形象的表演,并且這一形象不是日本人自發的心态,而是歐洲視角對日本人的膚淺勾勒,是一個幻想。
三島由紀夫真實地上演了這一形象。他嚴格按照這一形象創造了自我。那是他生活的方式,也是他死去的方式。
愛德華·薩義德教授用“東方主義”來指稱歐洲人對東方人的看法。他堅持認為,東方主義就是歐洲人的觀點,與真實生活在東方的人毫無關系。但是三島由紀夫的觀點截然相反。他說你眼中的日本人就是我。
我想,他是希望通過完全按照這一形象生和死來展現出一些東西。他就是那樣的人,那也是他在歐洲和整個世界享有文學聲譽的原因。
但是三島由紀夫事實上呈現的是虛假的形象。導緻的結果就是,大多數歐洲人對于日本人的看法有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三島由紀夫,另一個極端是像索尼董事長盛田昭夫那樣的人。在我看來,兩個極端都是錯誤的。
但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我們上哪才能找到日本民族更準确的形象呢?
《浮世畫家》,石黑一雄 著,馬愛農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回到你的作品《浮世畫家》裡,書的結尾場景中有許多年輕的日本職員,畫家小野滿懷欣慰地注視着他們。我認為真正生活在日本的就是這樣一群年輕人,是一群能給日本經濟帶來繁榮的人。當然,三島由紀夫沒有讨論過他們。而像我這樣的作家,由于對日本持有負面的觀點,也沒有捕捉到他們。是以我認為你的小說在改善歐洲對日本人的看法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就像是一種針對三島由紀夫形象的解毒劑。
我想問一個問題。無論是讀你的作品還是和你聊天,人們完全不會覺得這是個在日本出生的人。就我最喜愛的作家康拉德而言——在我看來,他是個完美的小說家——人們會強烈感覺到他是個真正的英國作家,也是個真正的歐洲人。
在你赢得布克獎的那天,日本媒體報道了你對薩爾曼·魯西迪的評論。(注:在布克獎的獲獎演說中,石黑一雄提道:“今晚最好不要忘記薩爾曼·魯西迪,忘記他發現自己身處的令人驚恐的境地和苦難。”)
薩爾曼·魯西迪及其作品《午夜之子》初版封面
很多人都被那些評論打動,其中就包括我自己。我們覺得他是真正的歐洲作家,有着真正的歐洲性格,這就是真正的歐洲智慧。
日本人自己希望被看作是愛好和平的、溫順的,就像日本藝術,比如風景畫之類。他們不希望被看作經濟帝國主義者或者軍事入侵者。他們希望别人想到日本的時候會聯想到花卉畫,一種非常恬靜美麗的東西。
當你的書第一次在日本出現時,它們就是那樣被介紹的。你被形容成一位安靜而平和的作家,是以是一位非常日本化的作家。
但是從一開始,我就對此表示懷疑。我認為這是一位堅忍且有智慧的作家。你的風格始終都是雙重結構,有着兩個或者更多的彼此交融的内容。事實上,你的作品一次次地證明了我的想法。我同時覺得這種力量并不十分日本化,相反,這個人應當來自英國。
石黑:好吧,我沒有試圖要做一名安靜的作家。這實際上是技巧問題,而不是别的。
我的作品表面上看起來風平浪靜——沒有很多人被殺之類的事情發生。但是對我來說,它們并非安靜的作品,因為它們探讨的是最讓我困擾的内容,最讓我擔心的問題。它們對我來說絕非恬靜。
至于身為歐洲作家的問題,我想一部分原因是我對日本不甚了解。是以我被迫以更為國際化的方式寫作。
如果1960年我離開日本後經常回去,在成長的過程中更加了解日本,我想也許會深感自己肩負更大的責任,要去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再現日本人民,換句話說就是成為日本在英國的某種代言人。
但事實是,我沒有回日本。這是三十年裡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對于現代日本所知甚少,但是我仍然在創作以日本為背景的作品,或者是可能以日本為背景的作品。
在我看來,正是因為我缺少對日本的權威性和認識才迫使我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想象,同時把自己視作一個無家可歸的作家。我沒有明顯的社會角色要去扮演,因為我既不是非常英國的英國人,也不是非常日本的日本人。
因而我沒有明确的角色,也沒有社會或者國家要去代言或為之書寫。沒有任何人的曆史是我的曆史。我認為,這必然推動我嘗試國際化的寫作方式。
我起初就是利用曆史。我會在曆史書籍中搜尋,就像電影導演為自己已經寫好的劇本尋找外景地一樣。我會在曆史長河中找尋最契合我的寫作目的或者我想書寫的曆史瞬間。我明白自己對曆史本身并無太多興趣,我利用英國曆史或者日本曆史隻是為了講清楚自己關注的東西。
我想,這使得我成了不真正屬于任何一方的作家。無論是日本曆史還是英國曆史,我都沒有強烈的情感關聯,是以我可以利用它服務于我的個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