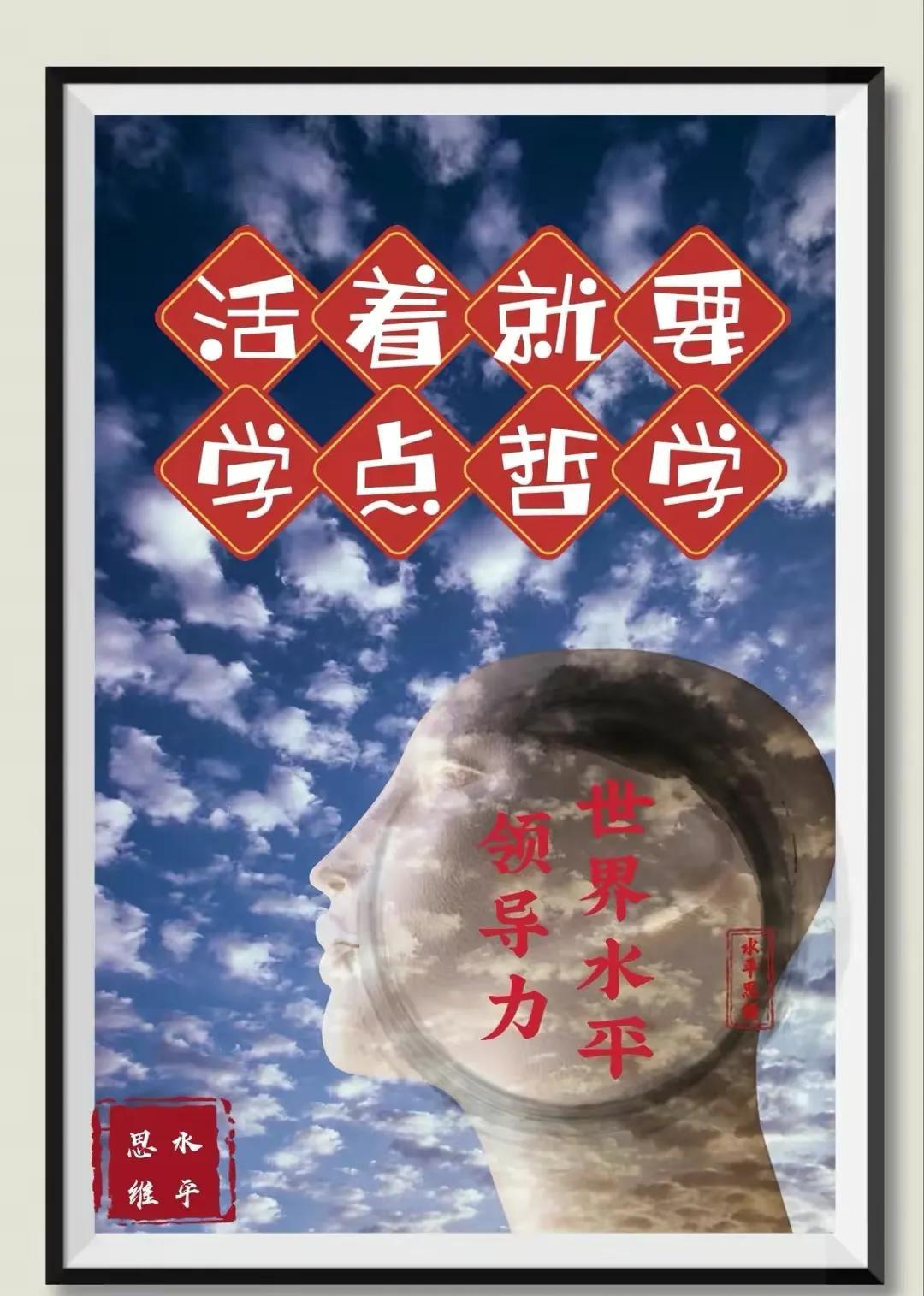
經營管理需要哲學!
一、 什麼是現象學
現象學是20 世紀的“ 顯學” , 它由胡塞爾(E· Husserl,1859—1938) 創立, 中經舍勒(M · Scheler) 、 海德格爾、 薩特、 格 洛 龐 蒂 (Merleau Ponty) 、 伽 達 默 爾 (H ·Gadamer) 、 利 科 (P · Ri- coeur) 、 茵 加 爾 頓 (R ·Ingarden) 等人的弘揚, 蔚然而成頗為壯觀的現象學運動, 執歐陸哲壇之牛耳達數十年之久。 可以說不弄清現象學, 20 世紀歐陸哲學的發展史就還是一筆糊塗帳, 但究竟什麼是現象學卻也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就可弄清的事情。 在現象學家之間對什麼是現象學就有種種的争執與分歧, 即使在胡塞爾本人那裡, 現象學是什麼也并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以奉告。 他的幾本有代表性的著作皆以“ 導論” 的面目出現: 《觀念: 純粹現學的一般導論》 (1913) 、《笛卡爾的沉思: 現象學的一個導論》 (1913) 、《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驗現象學: 現象學哲學的一個導論》 (1936) 。 我們在胡塞爾經典性的導論之外, 不可能給出一個更好的導論來, 我們的介紹隻能算是他本人現象學導論的一個導論而已。1859 年胡塞爾出生于摩拉維亞的一個猶太人家庭。 他本來是學數學的, 并拿過數學博士學位。 後來在布倫塔諾(F·Brentano) 的影響下對哲學産生了興趣。 他先在哈勒大學任哲學講師, 1900 年至1901 年胡塞爾發表了兩卷本的《邏輯研究》, 借此被哥廷根大學聘為副教授, 直到他47 歲時才擔任教授。 這時在他的周圍已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學生與朋友,史稱“ 哥廷根學派” 茵加爾頓、 舍勒、 斯坦因(E· Stein) 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們定期聚會, 熱衷于闡發胡塞爾的對象理論, 他們堅守《邏輯研究》 中的“ 面向事物本身” 的原則,對各種各樣的對象加以現象學的描述。
在慕尼黑也有一個類似的學派即慕尼黑學派, 主要成員有: 道伯特(J· Daubert) 、普凡德爾 (A · Pfander) 、 賴納赫 (A · Reinach) 、 蓋格爾(M · Geiger) 。 1913 年胡塞爾與他的追随者一道創辦了《哲學和現象學研究年鑒》, 他的《觀念: 純粹現象學的一般導論》 即刊登在《年鑒》 的第一期上。在他的哥廷根與慕尼黑的追随者看來, 這部著作嚴重偏離了《邏輯研究》 的方向, 從中立的對象描述滑向了先驗唯心主義。 許多追随者是以而離他而去。從1916 年起直到退休, 胡塞爾一直擔任弗萊堡大學的哲學教授, 1938 年去世。 晚年的胡塞爾生活得并不開心, 他的一個兒子死于戰争, 另一個則終身殘疾。 他的猶太身份吓走了許多朋友。 他的很多作品隻能在國外發表。 他甚至被禁止使用大學的圖書館。 令人感慨的是, 他在這張禁令的背面也寫下了他的研究筆記。 在他冷冷清清的喪禮中, 弗萊堡大學哲學系隻有一個人以私人身份出現。 他生前一度最得意的弟子—— 海德格爾竟連面都不肯露。胡塞爾生前發表的著作并不多, 但死後卻留下了45000頁的手稿, 這些手稿由範· 布瑞達 (Van Breda) 利用外交途徑秘密運出國外, 得以免遭納粹之手的毀滅。 1939 年範·布瑞達在比利時盧汶大學建立了胡塞爾檔案館, 它與後來建立的科隆大學胡塞爾檔案館合作于1950 年開始整理出版《胡塞爾全集》, 至1992 年為止已出至第28 卷。那麼, 現象學究竟是什麼?在20 年代現象學剛剛傳入法國不久, 當時法國的思想家雷蒙· 阿隆(R · Aron) 指着一盞雞尾酒杯向他的好友薩特神秘兮兮地說: “ 我的夥計, 如果你是現象學家, 你就能談論這個酒杯, 而這就是哲學。”就讓我們從酒杯談起吧。我們看到桌子上有一個酒杯, 或許我們會因其樣子古怪而端在手裡瞄幾眼, 或許隻不過當作炊酒的器皿而毫不留意。
我們和朋友一起沉醉于傾心的交談中。 當然我們知道杯子在桌子上, 桌子當然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煙灰缸啦, 小花瓶啦等等。 實際上說我們知道也并不準确, 我們拿起酒杯小啜一口并不是先要進行一番認知活動, 看看杯子, 用手對準它, 然後才端起來。 端杯子與飲啜都是自然而然地進行的, 這一切活動都是“ 日用而不察” 。 這種直截了當的信受态度就是“ 自然的态度” , 我意識到一個世界, 它在空間中無盡延展, 在時間中無限變化。 我把它當作一直存在着的東西, 當下直接地經驗到它。 當然我們有時也會做夢, 有時也會産生一些幻覺,不過我們很快就會知道自己在做夢, 也能輕易地将幻覺與現實分開。 我們是生活在井然有序的日常世界之中, 這個世界是大家共有的, 習以為常的。 我們在咖啡館的桌子邊一坐下,把手一招, 咖啡館侍者就會走過來, 一切都仿佛達成了默契一樣。 付帳的時候, 我們會不自覺地把手伸進口袋裡, 掏出錢包, 我們并不是先想一下口袋在哪裡、 錢包在哪裡才這樣做的。 自然态度的世界是如此實在以緻于沒有人去留心它的實在性。 當然我們知道我們所知覺的這一切并不是十分精确的, 我們知道桌子上的酒杯能盛一定量的酒, 但究竟能盛多少那要靠實體學的測量, 我們知道這酒是由葡萄釀成的, 但這酒的具體成分那要靠化學的測試。 自然科學并沒有否定我們的自然态度, 它隻不過對我們日常态度的進一步精确而已。就此而言, 自然科學的态度依然屬于自然的态度。然而, 當我看到一個酒杯時, 我究竟看到了什麼呢? 我看到了它的杯底了嗎? 當我看到侍者向我走來時, 我看到了侍者的背面嗎? 我當然意識到這是一個酒杯, 但這酒杯究竟如何被意識到呢? 這酒杯呈現于我的意識之中難道是像桌子在咖啡館中一樣嗎? 這突兀的問法對自然态度的人們來說簡直就是一記當頭悶棍: 這是哪門子問法? 杯子難道沒有杯底?侍者難道沒有背後? 這一問即是現象學的一問, 即是出自檢討态度的一問。
自然态度的人因其自然興趣而一頭紮進了對象之中, 現象學态度将種種自然之趣擱置起來, 它由對象向後審視, 看一下這對象究竟是如何呈現于我眼前的。 是以現象學的檢討态度不再關注對象是什麼, 而是關注于對象如何是, 關注于對象如何呈現為對象的。 現象學态度是對自然态度的總體的掙脫, 現象學家并不像笛卡爾那樣懷疑自然世界的存在, 不, 他對這自然态度所設定的世界存在與否根本就不感任何興趣, 他将人類日常的習慣與種種的理論知識系統括在了括弧裡。 加括弧并不意味着日常習慣與科學知識是值得懷疑的, 更不是要與它有意過不去, 胡塞爾一再聲明他對人類的知識系統頗為敬佩與贊賞。 加括弧隻是意味着存而不論, 通過加括弧所有從屬于自然觀點本質命題統統失去了作用, 進而使得一直被自然觀點所遮蔽的東西披露出來, 這就是“ 現象學懸擱” 的基本含義。 是以現象學懸擱并沒有否定任何東西, 相反它使在自然态度為而不名的東西擺到了亮處。通過懸擱, 穿在事實身上的觀念之衣被加以“ 剝脫” 與“ 拆卸” , 最終值得我們面向事實本身, “ 面向事實本身” 便成了現象學方法論的第一原則。 事實本身即是在明證性、 在絕對的所予中給出的東西。 是以現象學不構造任何的理論體系,不進行任何的抽象思辨, 它隻是忠實于他所見到的一切現象,并将現象依其自身呈現的樣子而如實描述出來。我見到一個酒杯, 這個杯子究竟真地存在與否, 它有多重, 它的體積有多大, 它的化學構成如何這一類的常識與科學的習慣統統被存而不論了, 我隻留心它如何呈現于我的意識之中的。 我從不同角度看它, 看到的東西并不盡一樣, 我還可以閉上眼睛, 回憶一下剛才看到的酒杯的樣子, 在這關于杯子的種種意識活動中, 杯子作為對象突現出來。
實際上意識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 想總要想點什麼, 看點要看點什麼, 愛總要愛點什麼, 恨總要恨點什麼……意識活動總要牽涉到一個意識對象, 意識的這種屬性即是“ 意向性” 。 意向性(intentionality) 源于“ intentio” , 原與箭術有關, 指箭指向靶子的行動, 後來成了中世紀經院哲學的一個術語。 胡塞爾的老師布倫塔諾首先将它帶進了現代哲學中。 他提出意向性概念以差別實體現象與心理現象, 實體現象比如一塊岩石即是一塊岩石, 不多也不少, 它即是它自身; 而心理現象比如“ 我感覺” 、 “ 我想象” 、 “ 我愛” 、 “ 我怕” 等等它總要牽涉到不是它自身的一個某物, 這個某物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 我怕鬼” , 盡管鬼不存在。 胡塞爾借助布倫塔諾的意向性概念來指意識行為的特征。 他認為在意向行為中尚存在一種非意向的感覺與料。 比如說我看到面前這個乳白色的酒杯, 在這一意向行為中“ 乳白色” 隻是一“ 實在的感覺與料” , 我實際看到的是這感覺與料之外的酒杯本身。 這個使實在的非意向的質料産生作用的因素就叫“ 意向作用” , 由意向活動所産生的對象就叫“ 意向對象” , 非意向的質料與意向作用是意識體驗的實在部分, 意向對象則是意識體驗的理念部分, 它并不是自然界中實際存在的對象, 果園中的蘋果樹可以燒掉, 但被知覺的蘋果樹卻不能燒掉。 這樣整個意向行為的存在地位也就一清二楚了: 質料與意向作用是實在的 (real) , 它們實實在在地存在于具體的意識行為之中; 意向對象則理念的(ideal) ,它是意向地(intentionally) 存在于意識行為之中; 外界的對象則是實際的 (actual) , 它實際地存在于自然态度下的自然界中, 它與意向行為無關, 已被現象學懸擱所擱置。通過現象學懸擱所披露出來的即是此意向性的領域, 是純粹的意識之流。
由于我們已把常識與科學系統擱置一邊, 這使我們第一次得以将意識現象作為意識來描述。 我們再也不必關注意識的生理基礎, 更不會将意識歸結為自然的物事, 懸擱使一切實體化的思維、 使一切将意識自然化的沖動均被抑制住了。 現象學家便可在原初的意識現象領域, 依意向對象極與主體極兩方向對意向性加以描述與分析。意向對象并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東西, 後者是自然态度設定的東西, 現象學對之并不感興趣; 意向對象也不是心理活動中實在的東西, 酒杯的顔色對我目光的吸引, 酒杯中散發出的酒香對我嗅覺的刺激, 這些都是心理活動的實在的東西, 然而當我說“ 這是一個酒杯時” , 我并不是在報道我的目光與嗅覺的實際狀态, 就像我說1 +1= 2 時也并不是在報道我本人的内在心理的計數活動, 意向對象是超越具體的内在心理活動之流的。意向對象不受具體的、 個别意識行為的制約, 相反一切具體的個别意識行為都受到其相應的對象類型的規導。 我見到一個酒杯, 酒杯作為對象類型便規導着我進一步的意識行為的展開, 我盡管隻看到的一面, 但我預期它的背面如何如何, 它的底部如何如何, 這個“ 如何如何” 安全是由酒杯之對象類型預先規定好了的。 對象類型作為本質的規定性是由當下直覺直接把握到的。 我并不是先看到一堆純粹知覺, 然後将這堆知覺與以往關于杯子的知覺加以比較, 發現它們有某種相同性, 然後才說“ 我見到了一個酒杯” 。 不, 本質是直覺到的, 本質直覺當然要借助個别事例, 但卻并不局限在上面。 在本質直覺中想象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可以想象一個杯子, 它沒有杯把, 當然它仍然是一個杯子, 我們還可以想象一個杯子它的口部相當寬而它的底部又出奇地窄,在我關于杯子的自由想象的變更中, 杯子的具體部分可以不斷變換, 杯子仍不失為一個杯子。 但這其中有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 一旦越過這個界限, 杯子就不再是杯子了。
正是在這種自由想象的變更中, 這個界限得以顯示出來, 這個界限即是杯子的本質。 事物如果缺乏這本質它就不是該事物了。 是以現象學描述并不關心具體的經驗事實, 現象學盡管也描述具體的意向行為, 但這種描述完全是作為本質描述的一個“ 範例” 而已。 由經驗事實向本質領域的轉移就叫“ 本質還原” 。還是讓我們回到酒杯上來。 當我們見到一酒杯時, 我們實際知覺到的隻是它的一個側面。 即使我看到了整個杯子, 這一看見也是透視的, 比如說杯子的内壁靠底的部分就沒有實際看到。 為了看到整個杯子, 就得繞它一圈, 或者幹脆把它放在手裡把玩一番, 我的透視方向不斷變化, 杯子的其他側面便不斷呈現于我意識之中。 是以作為意向對象之杯子要比在任何具體的給予方式的顯現之物有更多的東西, 然而“ 這個更多的東西” 并不是随意的想象, 它受一定的規則支配, 它有一個預先描劃出來的可能性, 這就是“ 界域” 。 我見到一個待者向我走來, 我實際所見的隻是他的正面, 他的背面我并沒實際見到。 但在“ 界域” 中他的背面與其正面被我的意向行為共同指向了, 我預期到他有一個如此這般的背面、 它不會是樹的背面, 也不會是酒杯的背面。 當然我的預期意向也有落空的時候, 本來我見到待者向我走來, 但他一轉身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背後竟是一堆機械的物事, 他的動作也不像人那樣自然, 原來它根本就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機器人。 這時我原先意識中人的意向便落空了, 一個新的意向即機器人的意向便産生了, 進一步的意識行為将充實這一新的意向。由此可見, 由于空間性的品格, 物的給出總是在輪廓(adum- bration) 中進行的, 它總是單方向給出的。 在一個側面的實際給出外, 還有一個尚未完全确定的共同給予的“ 界域” , 這就使新的知覺成為可能。 物的給出是“ 不充分的”(adeguate) , 總有可能被進一步的經驗變更或取消其已被設定的存在。
物隻是一假定的存在(presumptive) , 物的給出必以意識行為的和諧統一為前提。 既然物的給出總是暫時的、 不充分的, 我們總可以設想未來的經驗會取消以前的經驗, 我們甚至可以設想所有呈現“ 物” 的各種意識行為完全互相沖突無法和諧相處, 經驗“ 爆炸” 了, 這時物也就根本無法呈現了。 世界無比的設想總是可能的, 但意識不存在的設想卻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 物的存在是相對的、 依他的, 意識的存在是絕對的、 自律的, 世界的呈現完全依賴于意識, 世界是由意識構成的。這是一個容易讓人誤解的命題。 說世界是由意識構成的并不像是說酒杯是由玻璃構成的, 自然态度下所講的構成均是因果性的。 實體性的, 桌子是由木頭構成的, 是說木工通過對木頭加工制成了一張桌子。 現象學懸擱已将此自然态度徹底抑制住了, 是以, 我們千萬不要從自然态度來揣摸胡塞爾的思想。“ 構成” 完全是在現象學意義上的, 說物是由意識構成的無非是說物是在意識中得以顯現、 出場的。 顯現也并不是說先有現成的物這個東西在幕後, 又有現成的意識舞台,物之顯現即是從幕後走向舞台。 物之為物恰恰是在顯現于意識的過程中呈現為物的。 在物呈現為物的過程中, 意向行為已發生種種賦予意義的作用了。 是以說物呈現于意識中, 并不是像說鋼筆在文具盒中一樣, 物是構成于意識之中的。 談論意識之外的物自體如同談論圓的方是一樣荒謬的。 同樣,“ 意識” 也必須在現象學的意義上得到了解, 意識完全被剝脫了世間性的品格, 它不再與任何世間的生理與心靈的實在發生關系, 它完全是純粹的絕對的先驗意識。 為了獲得此純粹絕對的先驗意識就必須實施“ 現象學的先驗還原” 。“ 還原” (reduction) 一詞源于拉丁語“ re- ducere” 意為“ 傳回到源頭” 。
現象學還原就是從現成的知識系統與日常習慣傳回到源始的現象。 還原實際上是“ 解構” 與“ 剝脫” , 它将一切意識構成的對象加以層層拆卸, 透過意向行為造成的“ 意義積澱” , 而直逼意義的源頭—— 先驗自我及其前謂詞的遭遇。那麼, 什麼是先驗自我呢? 先驗自我是所有意向行為的輻射源, 它是意向行為的主體極。 它不是機體的我, 也不是經驗自我, 甚至也不是心理自我, 先驗自我完全與世間性的機體、 經驗、 心理毫不相幹, 後者完全是在世界之中的物事,是實體化的東西。 先驗自我不是世界中的對象, 不是世界中的一部分, 毋甯說世界是它的對象, 先驗自我是世界的主體。在還原之先是物轉我, 在還原之後, 是我轉物。 先驗自我生存于不斷變化的純粹意識之流中, 它并不是一個空虛的同一極。 每一自我的意向行為都在先驗自我中留下“ 痕迹” , 我可以如此這般做出決定, 但這一決定一旦作出, 我就是做出這種做定的自我, 我即是這些行為積澱的載體, 這些積澱的習性構成了我行為的巨大界域。是以先驗自我的純粹意識生活并不是雜亂無章的, 它有一個内在的時間結構, 先驗自我的本質即是“ 時間性” 。 “ 時間性” (Tem- porality) 不是常識說的時間 (time) 。 常識的時間是一維的, 現象學的時間性是三維的, 每一現在的意識都擁有一過去與未來的界域意識。 比如說我聽一首音樂, 如果沒有三維的時間意識, 我們隻能聽到一個個孤立的聲響, 我們之是以能聽一首有着完美旋律的音樂完全應歸功于時間性: 在我聽到當下聲響同時, 已過去的聲音作為記存(retenBtion) 纏繞在我當下意識的周圍, 這個記存是原發的, 它與次發的主動的回憶(recollection) 不同; 同時, 我當下的意識也向未來開放着, 未來的預存(protention) 也纏繞在我當下意識的周圍, 這個預存也不同于主動的預期(expectation) 。
實際物的呈現也有賴于先驗自我的時間性, 如果沒有時間性, 我們隻能看到一個個不連續的感覺印象, 正是由于時間性, 盡管每一個當下我實際所見到的隻是酒杯的一個側面, 但這個當下的實際所見卻擁有一過去記存與未來預存的界域, 這使得我們說: 我看到了一個酒杯。 先驗自我發出的每一個意向行為都不是孤立的, 都在時間性與别的意向行為交織在一起進而形成一綜合意識之流。 于是先驗自我在其意向生活流動不居的多樣性中與被意謂的對象一道構成了“ 單子自我” 。 單子自我囊括了我的整個意向生活, 先驗主體性是普遍的又是絕對具體的, 是“ 可能意義的宇宙” , 所有的意向行為以及意向行為的對象都最終是由先驗自我構成的。 這樣每一可設想的意義, 每一可設想的存在都最終落入了先驗主體領域内。 任何将真實存在的整體設想為外在于可意識、 可能知識、 可能明證整體之外的嘗試都是荒謬的。 先驗自我成了最後的根基,成了可以設想的最高的合理性, 任何再向先驗自我背後還原的努力都是徒勞與荒謬的。 現象學達到了最終的徹底性, 達到了最後的源頭, 現象學成了一門“ 自我學” , 成了“ 第一哲學” , 成了“ 先驗唯心主義” 。人們要問: 現象學還原将一切還原至“ 自我本具的領域” , 他人何在? 世界之客觀性何在? 這豈不是一種唯我論嗎?我們應先明了在自然态度他人存在, 世界是客觀的、 公共的,這是不成問題, 胡塞爾對此也并不感興趣。 問題是如何在先驗意識中呈現出另一個先驗意識, 這個問題有相當的難度。 他人的給出與物的給出不同, 物總是以單面的直呈與其他側面的附呈 (appresented) 給出的, 通過我身體的運動這一附呈的側面便會轉化為原初的直呈; 他人無疑也是以其身體直呈于我的, 他的意識生活則附呈的于我的, 然而這附呈的東西永遠無法轉化成我原初的直呈, 因為如果那樣的話他與我就無别了, 他就不是他了。 這倒真正成了唯我論了。
他人給出是如此之特殊, 一方面他必須在我的意識中得到構成, 另一方面, 他又必須被構成為有着先驗意識的他人。為此胡塞爾指出一非心非物亦心亦物的身體來解決此難題。 身體(Body) 不是物體(body) , 身體乃充滿心之身, 乃意志之身, 我能随意地舉起我的手這與我用手舉起某物體根本有别。 當我看到一個與我身體相似的他人, 藉能類感通(empathy) 我當下領悟到他與我擁有類似的意識生活。 能類即能身體之類, 感通即感精神之通。 正是有此能類感通, 我才能聽懂他人之肺腑之言, 而不是純粹的聲波振動, 我才能看他人莞爾而笑而不是臉上的皺紋的位移。“ 互動主體性” 的領域便是以而敞開了, 世界的客觀性也是以有了着落。現象學的最初目标是“ 面向事實本身” , 事實即是當下呈現于直覺的明證性。 他随着現象學意向分析的進展, 胡塞爾發現自我的許多操作行為并非當下直接呈現于我, 它可能離當下直覺有一時間之間距, 而這個過去的時間間距本身也有一積澱的界域結構。 這樣看來早先的從自然态度直接還原到自我笛卡爾式的做法不免給人以空乏之感, 對所有含在被構成物中意義的不斷逆溯的意向解釋也就是以而付之阙如。 晚年的胡塞爾于是動手寫下最後一個現象學導論《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驗現象學》, 在這本影響深遠的著作中胡塞爾提出了“ 生活世界” 的概念。 這部著作被認為是胡塞爾思想發展中的一大轉折, 實際上他本人的先驗現象學的旨趣并沒有變。 回到“ 生活世界” 隻是回到先驗主體性的中間站而已。 生活世界是前科學的知覺世界, 是主觀相對的世界, 是日常生活的世界。 生活世界是先于科學産生的。 科學世界的抽象化、 觀念化必須借助于生活世界中的物事才能進行, 而生活世界的明證性則使所有科學的觀察與驗證成為可能。
但是科學世界中的客觀主義者忘恩負義, 他們把從生活世界得到的種種好處忘得一幹二淨, 竟然将自己觀念化方法與實際存在本身等同起來, 緻使科學出現了意義方面的危機。 為了發現被科學主義所障蔽的真正意義之維, 就必須對科學世界實行現象學懸擱, 回到生活世界中來。 回到生活世界中并不就萬事大吉了, 真正現象學分析的工作才剛剛開始呢。 通過對生活世界的“ 内在思考” , 發現一度被掩設的“ 根源” , 原來先驗自我才是“ 所有有效性的操作者” , 世界、 科學、 自然生活都是通過“ 先驗主體” 的“ 意識生活” 才獲得其内容與有效性。 自我成了縱貫整個曆史發展中的“ 目的論” 與“ 絕對理性” 的載體, 是以他就必須依内在的目的論與絕對理性構成自己的生活, 克服生活世界的相對性, 達至普遍理性的大同世界。看來胡塞爾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先驗自我及其意識生活。科學世界也罷, 生活世界也罷, 說到底都是先驗自我構成的。對先驗哲學沒有好感的人早就會問了: 世界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如何能構成整個世界? 這豈不是說世界的主體部分吞下了整個世界及它自身? 這豈不是天大的荒唐? 這不是“ 荒唐”(absurdity) 而是“ 悖論” (paradox) , 胡塞爾說, 不解決這個悖論就意味着“ 實際的普遍與徹底的懸擱是根本無法實作的” 。 胡塞爾的解決倒很簡單明了: 經驗自我原本即是一先驗自我, 隻不過毫無覺察而已。 隻有通過先驗之維的揭示, 我才發現, 作為一個先驗自我, 我也是在世俗個人自我的同一自我。 違是衆生, 悟是佛。 問題是: 在自然态度下, 先驗自我蔽而不現, 人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處在自然态度中, 隻有通過懸擱才能認取先驗自我, 這就是說要突破自然态度就必須有一先驗自我來檢討, 而要認取先驗自我就必須對自然态度進行懸擱, 結果出現一個邏輯怪圈—— 還原的前提是必先有先驗自我的覺醒, 而先驗自我之覺醒的前提則必先進行還原。 理性終于碰到了自己的界限, 在理性無能為力的地方, 非理性便登場了: 現象學還原猶如“ 改宗” , 從經驗自我到先驗自我乃是出于信仰上的“ 跳躍” (leap) 。這一跳便離存在主義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