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學是如今最成功的科學理論,但它也是一個“問題兒童”,這個充滿悖論與神秘色彩的理論潛藏着許多無法直覺闡述的東西。它的一個“症狀”便是:當我們越深入地了解現實,反而卻更不知道如果描述現實——比如我們去問,“粒子是什麼?”,可以得到許多不同的答案。甚至可以說,量子力學動搖了我們對現實本質的看法,而對其诠釋會上升到對科學本質看法的分歧,例如回答“自然世界是否對立于我們意識存在?”,“我們是否可以了解并描述這些性質?”等問題。百年來,實體學家們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本文作者,理論實體學家、圈量子引力理論創始者之一李·斯莫林(Lee Smolin)給出了“是”的答案,與愛因斯坦一樣,他們被稱為現實主義者。另一派以玻爾(Niels Bohr)為首,屬于反現實主義者(其中包括量子認知主義者和操作主義者),他們在20世紀的實體學發展中占據上風。顯然,這并不能讓現實主義者滿意,斯莫林希望建構一個更為真實的描述微觀世界的理論。
《量子力學的真相:愛因斯坦尚未完成的革命》(Einstein’s Unfinished Revolution:The Search for What Lies Beyond the Quantum)一書就介紹了兩派不同的觀點,全書主要分三部分:量子力學的基本概念;20世紀50年代後現實主義者的工作,例如玻姆和貝爾等人(返樸曾推送《玻姆力學——教科書外的量子理論》);一些作者和他人的新的嘗試。本文即從基于約翰·惠勒(John Wheeler)“萬物源于量子比特”的資訊角度闡述量子力學,介紹了“關系性量子力學”的基本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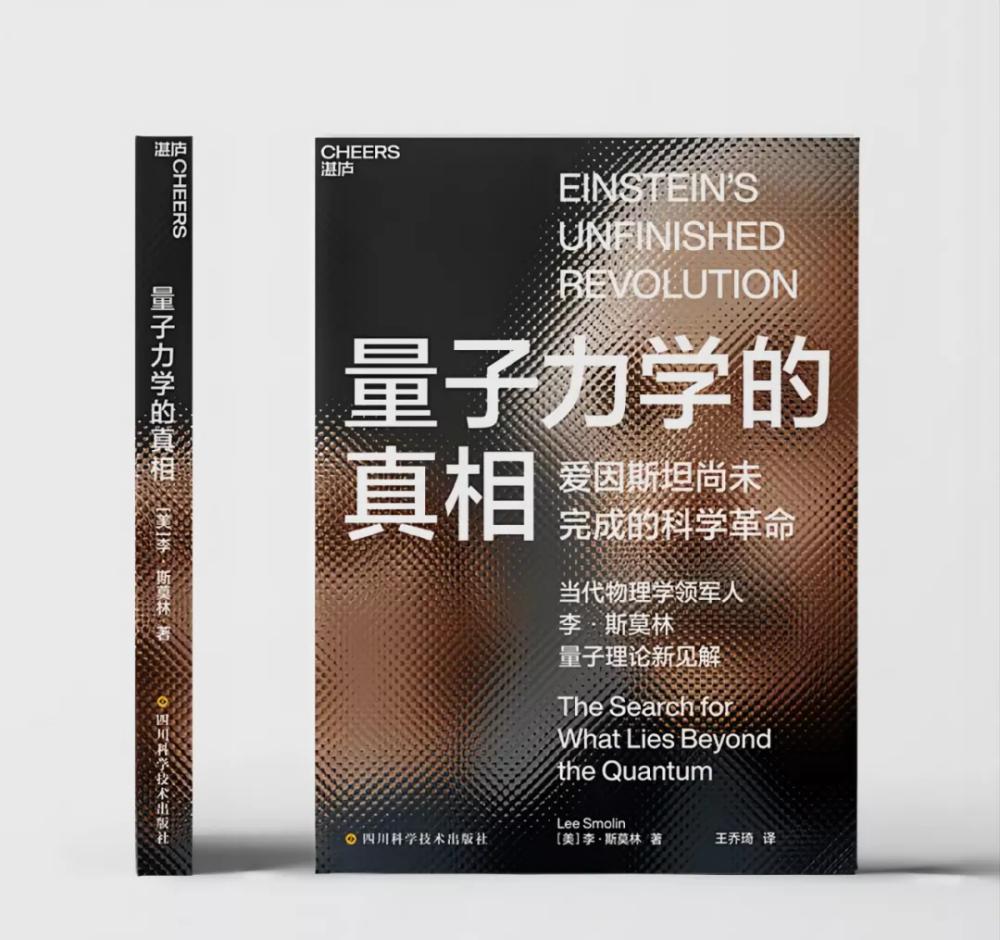
本文經授權選自《量子力學的真相:愛因斯坦尚未完成的革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年9月版)第三幕《革命的替代品》,内容有删減,标題和小标為編者所加。前往“返樸”公衆号,點選文末“閱讀原文”可購買此書。點選“在看”并發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區,截至2022年1月23日中午12點,我們會選1條留言,贈書1本。
撰文丨李·斯莫林(Lee Smolin)
翻譯丨王喬琦
最終,我們還是不得不去尋找那些有望成為正确的世界本體論的理論。畢竟,所有真正的實體學家靈魂最深處燃燒的欲望之火都是為了探明現實的本質。
——盧西恩·哈代(Lucien Hardy)
在過去的幾年裡,量子基礎方面的研究很活躍,并且熱度在不斷上升。這個領域沉寂了80 年之久,任何想要成為這方面專家的實體學家都難免會打退堂鼓,但現在,成為量子基礎領域的專家總算可以算作一份不錯的職業規劃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隻是如今該領域的大多數進展以及大多數年輕人都偏向于反現實主義一邊。目前,這個領域大部分新的研究工作的目标并不是修正量子理論使其不斷完備,而隻是給我們提供一種讨論它的新方式。
李·斯莫林(Lee Smolin)
……
這些進展還加深了我們對量子理論建構方式的了解。例如,哈代開創了一種新方法,用以尋找能從中推導出量子力學數學形式的最簡潔的公理集。在這些公理中,有幾條很簡單,并告訴我們所有理論都正确;還有一條公理則囊括了量子世界的所有怪異之處。
與此同時,在這樣一種受操作主義方法支配的環境中,幾乎沒有什麼空間留給那些苦苦尋找完備的量子理論以解釋各種事件的老派的現實主義者了。在這些現實主義者中有一些是多世界理論的支援者,但也有一小部分支援玻姆的人,還有少數現實主義者則發展了波函數坍縮理論,而嘗試脫離這些現存的方法來搜尋量子力學現實版本的人就更少了。研究這個問題的大部分人本身都是其他領域的專家,有些還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取得了極高的成就,比如斯蒂芬·阿德勒(Stephen Adler)注釋1和1999年諾貝爾實體學獎獲得者特·霍夫特(Gerardus't Hooft)。我們無法完美融入目前已經頗為活躍的量子基礎領域,主要是因為我們的關注重點和最終目标以及我們為了實作這個目标而提出的理論無法用操作主義語言表達,而精通這種語言正是量子資訊理論專家的标志。即便如此,我們仍沒有停下搜尋量子世界現實主義完備圖景的腳步。
我認為,就像哈代在本章章首語中所說的那樣,相比于操作主義觀點,很多實體學家還是更喜歡現實主義解釋,并且一定會對能夠克服現有方法缺點的量子力學的現實主義版本感興趣。現階段操作主義方法盛行的部分原因在于,可供我們選擇的且接近真相的現實主義方法還是少了一些。
本書的其餘部分介紹的就是量子實體學現實主義方法的未來。在我們忘卻非現實主義方法之前,先來看看近來它們的盛行是否提供了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回避測量——萬物源于量子比特
我能從中吸取的第一點教訓是:描述量子世界與适用牛頓實體學的經典世界之間差異的方法有很多。如果你願意采納量子力學的反現實主義觀點,那麼你就有很多選擇。你可以選擇站在玻爾這一陣營,他激進地提出:科學隻不過是我們用以互相交流各自實驗結果的共同語言的延伸。你也可以投入“量子貝葉斯主義”(quantum Bayesianism)的懷抱,這種理論認為,波函數無非就是對我們心中想法的表征,而預測不過就是賭博的另一種說法。你還可以站在純操作主義觀點一邊,也就是隻讨論準備工作和測量操作等過程,純操作主義的相關理論也正是基于這些過程的。
這些理論派别有一個共性,那就是都回避了測量問題,或者說得更準确一點,都從定義上拿掉了測量環節,因為根本不存在用量子态描述觀測者及其觀測工具的可能性。
部分新理論的核心概念是認為世界由資訊構成,我們從約翰·惠勒的名言“萬物源于比特”中就能總結出這一點。他這句名言的現代版本為 “萬物源于量子比特(qubit)”,其中量子比特是量子資訊的最小機關,在我們前面有關寵物偏好的故事中就可視為一種量子二進制選擇。在實際應用中,這種模式設想所有實體量都可以簡化為數量有限的量子“是否問題”,并且規則——限制下的時變演化過程可以了解為量子計算機世界中的量子資訊處理過程。這就意味着,系統的時變過程可以表達為在某個時間點上将一系列邏輯運算應用到一兩個量子比特上的操作。
約翰·惠勒對此是這樣表述的:
萬物源于比特意味着實體世界中的所有物件在本質上都擁有非物質來源和非物質解釋。我們所稱的現實歸根結底來自“是否問題” 的提出以及對儀器反應的記錄。簡而言之,一切物質理論上都起源于資訊,并且這個宇宙有我們所有人的參與。[1]
第一次聽到這種觀點時,你或許會覺得說這話的人隻是随便說說,但惠勒的确是認真的。這個觀點還有一種更簡潔的表述:“實體學讓觀測者參與了進來,觀測者的參與産生了資訊,資訊産生了實體學。”[2]
惠勒曾說:“這個宇宙有我們所有人的參與。”他是指宇宙誕生于我們對其展開的觀測或感覺。沒錯,對此你可以這樣回應:“可是,在我們掌握觀測或者感覺能力之前,我們必須先誕生于宇宙之中,并且還要借助宇宙的力量。”惠勒則會回應道:“沒錯,這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能從類似上述這種對話中得到何種啟示?某些演化結果數量有限的系統可以用這種方式表述,并且這麼做的确能指引實體學的前進方向,例如,量子實體學中糾纏概念的重要性就可以借此走上前台。不過,如果一個系統涉及的實體變量擁有無窮多個演化結果,那就沒法輕松套用這種模式了,比如電磁場。盡管如此,這種研究量子力學基礎的量子資訊方法已經對多個實體學領域産生了積極影響,從居于核心地位的固态實體學領域到關于弦理論、量子黑洞等的研究,無不如此。
微觀世界需要什麼樣的資訊定義?
我們應該小心謹慎地區分有關實體學與資訊間關系的幾個不同概念。在我看來,其中有些概念的确有作用,但很瑣碎;還有一些則頗為激進,仍需進一步論證。我們就從資訊的定義開始。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給出過一個相當有用的關于資訊的定義。他的定義建立在通信架構之内,設想從發送者到接收者的資訊傳遞通道。按照設定,這類通道共享一種語言,正是這種語言讓符号有了意義。資訊接收者收到資訊後,要通過一系列“是否問題”來了解該資訊的含義。這些“是否問題”的數量就決定着所傳遞的資訊量。
按照這個标準,隻有很少的實體系統可以看作共享某種語言的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資訊傳遞通道。從整體來看,宇宙并非這樣一種資訊通道。香農關于資訊的定義的威力在于它可以從語義環境中,即從資訊的意義中衡量究竟傳輸了多少資訊。按照香農的定義,資訊的發送者和接收者共享一套賦予了資訊含義的語義學規則,但你無須掌握這套規則就能衡量一則資訊所攜帶的資訊量。如果缺少了這樣一套語義學規則,一則資訊也就不會具有任何意義。例如,若要衡量某則資訊的資訊量,你首先得對該資訊所使用的語言有所了解,比如在使用這種語言的社群中各種字母、單詞或者詞組出現的相對頻率。這種有關語言環境的資訊并不一定需要編碼進每則資訊中,如果你沒有指定這種語言,該資訊就失去了香農定義下的資訊。尤為重要的是,這意味着被傳遞的資訊必須使用發送者和接收者共有的語言,脫離了雙方共享語言的無規則符号無法攜帶任何資訊。香農定義對資訊的衡量依賴于消息所用的語言以及其他各個方面,這些規則由資訊的發送者和接受者共有,但不必然被編碼進資訊本身之中,并不是純粹的實體量。
了解說話的人表達的意圖、傳遞含義的方式是語言哲學中的一個老大難問題。這個問題棘手不代表說話意圖和含義并非這個世界的組成部分,它們的确是這個世界的組成部分,隻是它們的存在依賴于思維。香農定義下的資訊就是對這個含義和意圖世界中所發生之事的衡量。即便我們沒有深入了解資訊的含義和意圖是如何嵌入自然世界之中的,這種資訊定義也相當不錯。
為了介紹得更清楚一些,我再舉一個例子。一場大雨過後,我聽到水滴從漏水的污水管中斷斷續續地滴落下來。水滴滴落的節奏似乎很不規律,但無論是對我還是對其他任何人來說,這種水滴聲都沒有攜帶任何資訊,因為并沒有發送者,而我也根本不是接收者,是以,按照香農定義,水滴中當然沒有任何資訊。另外,我們也可以利用水滴滴落時的長短間隔編制摩爾斯密碼來傳遞消息。這兩種情況之是以會産生大相徑庭的結果,就是因為前者缺少傳遞資訊的意圖,而後者正好具備,這種意圖很重要:香農定義下的資訊必然伴有傳遞資訊的意圖。對一個想要了解的知識超越了人類已知世界的現實主義者來說,資訊的香農定義在應用于原子所處的微觀世界時用處不大注釋2。
英國人類學家格裡高利·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給資訊下了一個不那麼精确的定義,他稱資訊為“帶來差異的差異”,有時也表達為“帶來差異的差別”。這個定義應用在實體學中可表述為:如果某個可觀測實體量的改變導緻實體系統的未來出現了可以觀測到的變化,那麼我們就認為這個實體量構成了資訊,按照這個思路,幾乎所有實體量都有傳遞資訊的可能。這個定義意味着,如果兩個實體量的值相關,那麼它們之間就存在“資訊”。這也沒什麼深奧之處,畢竟它并沒有表明實體世界的各個部分之間存在本質上的互相依賴關系。此外,我們對這種相關性已經有了測量的方法,現在改稱其為“資訊”,不過是換了一個弱化這種概念的特殊性的名字,但這似乎并不能給這個世界的原有概念帶來變革,反而更可能讓人混淆。
計算機按照香農定義來處理資訊,它們從資訊發送者那兒獲得輸入信号,然後應用某種算法将輸入信号轉變成供資訊接收者閱讀的輸出信号,這類過程個性化程度非常高。植入的算法是定義計算過程的關鍵組成部分,然而,大多數實體系統都不是計算機,并且,實體系統中初始資料演化成後續資料的過程并不總能用算法或者一系列邏輯操作來進行解釋。
有些學者似乎混淆了資訊的這兩種定義,他們希望把大自然描述為計算機,把這個世界在不同時期的各種狀态之間的關系描述為計算過程。我認為這種激進的假設是存在問題的。
誠然,某些實體系統的确能夠通過計算模拟達到某種程度的近似,這顯然是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給實體學中的重要方程(如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中的一系列方程)取近似并将其編碼成算法,然後放在數字計算機上運作。這常常是一種得到方程近似解的非常有效的辦法,但也隻能是近似,而不可能得到準确的答案。例如,我們可以通過數字化手段在某種程度上将交響樂團演奏的聲音近似地捕捉下來,但這永遠隻是近似,數字化手段隻能截取一定頻率範圍内的聲音,現場聆聽交響樂的全部體驗永遠無法通過數字模拟手段完整地呈現出來。這就是現在仍有許多觀衆更樂意親臨交響樂團演奏現場的原因,也是黑膠唱片仍有市場的原因,因為它是純粹的模拟錄音。實體學也是如此,對愛因斯坦的方程進行“數字模拟”可以非常有用,但它永遠也無法囊括這個方程組的所有精華。
雖然我們不能把實體學整體了解為資訊處理過程,但或許可以這麼說,量子态代表的不是整個實體系統,隻是我們掌握的系統資訊。這顯然符合規則二注釋3,因為隻要我們得到有關系統的新資訊,波函數就會突然發生變化。如果波函數代表我們掌握的系統資訊,那麼就必須把量子力學預言的機率視為主觀的、具有賭博性質的機率。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把規則二視為一種更新規則,即當做出測量動作後,我們對未來實驗結果的主觀性機率預測會按照規則二發生變化,這就是所謂的“量子貝葉斯主義”[3]。
關系性量子理論
還有一種相當精妙的方法也認為量子态傳遞了系統間的資訊,即所謂的“關系性量子理論”(relational quantum theory)。這個理論介于操作主義和某種形式的現實主義之間。它認為,量子态與宇宙的分裂、觀測者以及被觀測者有關,并且代表了觀測者可以知曉的關于被觀測者的資訊。關系性量子理論以量子引力理論為基礎,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我與路易斯·克萊恩(Louis Crane)、卡洛·羅韋利(Carlo Rovelli)的讨論中。
克萊恩等數學家之前就已經提出了一種極簡宇宙學理論——“拓撲場論”(topological field theories),關系性量子理論就是一種對拓撲場論的簡練的數學描述。這兩個理論不涉及任何對整個宇宙的量子描述,當然也不涉及描述宇宙整體的量子态。這兩個理論中的量子态描述的是宇宙分裂成兩個子系統的各種方法。我們可以這樣了解這類量子态:它們攜帶了某一側子系統中的觀測者可以掌握的關于另一側量子系統的資訊。
這讓我們想起了玻爾的觀點。玻爾認為,量子力學必然要求世界一分為二,一部分遵循經典力學,另一部分遵循量子力學,并且任何分裂過程都會産生這樣的結果。克萊恩等數學家研究的模型則更進一步,他們提出,系統的每一次分裂都會産生兩個量子态,即分裂産生的兩個子系統都各有一個量子态,這是因為我們有兩種方式解讀每一次分裂。假設愛麗絲生活在分裂後的一側,而鮑勃生活在另一側,那麼愛麗絲會把自己視為經典觀測者,測量另一側的“量子鮑勃”;而鮑勃的視角則正好相反。
這類模型非常簡單,但有一個問題:這兩種視角之間的相似度如何?愛麗絲對鮑勃的量子描述有多大機率與鮑勃對愛麗絲的量子描述相同?數學家們認為,無論宇宙如何分裂,這個答案都不會改變。以此為前提,兩側觀測者描述相同的機率就測度了某些普适的性質,這些性質表征了宇宙内部的聯系方式,數學家們稱其為宇宙拓撲學,這也是拓撲場論這個名稱的由來。
克萊恩意識到,拓撲場論中涉及的數學結構經過拓展可以囊括圈量子引力,是以就把這個宇宙模型拿出來與羅韋利和我一同研讨。事實證明,克萊恩的觀點完全正确,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他還提出,這種全新的數學方法提供了一種将量子力學拓展到宇宙整體的方法,關于這一點他也是正确的,這種方法就是關系性量子理論。
我們兩人都很受啟發,并把這個方法應用到了一般量子理論上,然後各自發表了相關結果[4]。羅韋利的版本更具普遍意義,也更為大家所熟知,是以我在此介紹一下他的理論。玻爾認為,量子實體學家必須始終從兩個世界的角度思考問題。我們這些觀測者生活在被經典實體學支配的世界中,但我們研究的原子處于量子世界中,這兩個世界遵循的實體規則是不同的。尤為重要的是:量子世界中的客體能以疊加态的形式存在,而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中,事物的可觀測屬性總是隻能取确定的數值,而不可能疊加起來。玻爾認為,這兩個世界對科學來說都是必需的。
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用來操控和測量原子的儀器處于我們這個世界和原子世界的邊界,玻爾強調,這個邊界的位置并不固定。目标不同,劃定的邊界也不同,隻要它能把整個世界劃分為兩個區域就行。
還是以薛定谔的貓實驗為例。劃定邊界的一種方法是把原子和光子看作量子系統,而把蓋革計數器和貓視為經典系統。在這幅圖景下,原子可能以疊加态的形式存在,但蓋革計數器總是會呈現确定的狀态:要麼顯示“是”——表征它探測到了光子;要麼顯示“否”——表征它沒有探測到光子。不過,我們也可以重新劃定這條邊界,把蓋革計數器也劃入量子世界。這樣一來,貓要麼活着,要麼死了,即總是處于這兩種狀态中的一種,但蓋革計數器可能處于一種與原子的糾纏疊加态。或者,按照薛定谔的說法,我們可以把邊界劃在盒子四個垂直面上。這樣一來,貓也成了量子系統的一部分,并且可能與原子和蓋革計數器産生糾纏疊加。此時,經典世界中的一個叫薩拉的人打開了盒子探查其中的情況,由于薩拉是宏觀世界的一個主體,是以,我們認為她總是處于某種确定的狀态中。從她的視角來看,薩拉會覺得自己身處經典世界這一側,是以在她看來,貓要麼死了,要麼活着,總是兩者居其一。
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建議我們更進一步,我們可以把薩拉和盒子、貓以及盒子中的其他物件一起劃到量子系統中,而我本人作為旁觀者則劃分到邊界之外,這樣我就能看到薩拉成為糾纏疊加态的一分子。在這種疊加态的一部分中,貓活着且薩拉看到它活着;而在另一部分中,貓死了且薩拉看到它死了。
于是,我們就有了5種區分量子世界和經典世界的方法。我們在此用 “量子”一詞表明事物可以處于疊加态,而“經典”一詞則表明實體量隻能擁有确定值。這些看似不同的描述似乎互相沖突,比如我們看到薩拉處于疊加态時她卻始終覺得自己處于确定狀态。
根據羅韋利的理論,所有這些理論都是正确的,都描述了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也都是事實真相的一部分。它們都各自有效地描述了這個世界的一部分,至于具體是哪個部分,則由劃定的邊界定義。薩拉是否真的處于疊加态,又或者她是否确定無疑地看到了一隻活貓或聽到了一隻貓的聲音?羅韋利不想在這兩者之間做選擇。他認為,對實體事件和實體過程的描述總是與劃定量子世界和經典世界邊界的某些特殊方式有關。羅韋利假定,所有劃定邊界的方式都同樣有效并且都是對世界的完整描述的一部分。簡單來說,羅韋利認為:在薩拉看來,貓活着,這一點沒錯;而在我看來,薩拉處于“看到死貓”和“看到活貓”的疊加态中,這一點同樣沒錯。
那麼,是否存在不會受到觀察者觀察視角的影響的事實?依我看,羅韋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上述例子中,雖然薩拉和我對檢視結果有不同看法,但我們一緻認為,她打開了盒子并且檢查了貓的狀态,不過,薩拉打開盒子的決定是否可能取決于某些量子事件的結果,比如某種不穩定原子是否衰變。這種情況下,我就能稱薩拉處于已經打開盒子和尚未打開盒子的疊加态,但薩拉本人不是已經開了盒子就是還沒開,兩者隻能居其一。
請注意,其中存在一種微弱的一緻性,因為我對薩拉的描述并沒有完全與她自身的描述相抵觸。我們還得注意到的關鍵一點是:所有劃分邊界的方法都會讓這個世界分裂成兩個不完備的部分。不存在宇宙整體的視角,即我們無法跳脫到宇宙之外來觀察整個宇宙,也不存在能夠描述宇宙整體的量子态。
如果關系性量子理論有口号的話,那一定會是“衆多局部視角定義了一個宇宙”。我們可以從多種角度來看待這個理論。務實的操作主義者會把每個通過劃定邊界将世界一分為二的方法視為定義一個可以用量子力學處理的系統。每一次邊界的選擇都會帶來一種全新的描述,它包含處于經典世界一側的觀測者所能掌握的關于邊界另一側量子系統的所有資訊。對這些務實的操作主義者來說,所有這些量子态包含了每個層級上的觀測者所能掌握的資訊,而這些層級則由分隔觀測者的邊界确定,而且每一位觀測者都用量子态編碼他們掌握的有關邊界另一側系統的資訊。這些量子态之是以會各不相同,是因為它們描述的就是不同的子系統。
從操作主義的視角來看,關系性量子力學與埃弗裡特最初提出的關聯态诠釋有一些共同之處。兩者都以編碼不同子系統間相關性的條件語句來描述世界,而這種相關性在子系統發生互相作用時就已經建立,然而,這并不是羅韋利看待關系性量子力學的方式。在他看來,他的這個理論應該符合現實主義,但卻不是我在前文中闡述的那種樸素現實主義。羅韋利認為:現實由一連串事件構成,邊界一側的系統通過這些事件擷取另一側世界的資訊,是以,我們可以稱羅韋利是一名基于因果關系的現實主義者。在他的理論中,現實取決于邊界的選擇,因為在某個觀測者看來确定發生的某些事—确定事件可以是另一個事件疊加态的一部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羅韋利的現實主義與樸素現實主義之間顯然存在一些差異,因為在樸素現實主義中,構成現實的事件是所有觀測者都會一緻認為确實發生了的。
羅韋利認為,這種樸素現實主義不可能存在于我們的量子世界中,是以,他建議我們接納他的這個完全不同的現實主義:世界的分裂定義了觀測者,而對現實的定義又總是相對于這種分裂而言的。羅韋利的描述與玻爾大相徑庭,并且得到了一種更為精準的闡釋,但他們運用的邏輯是相似的,他們都認為量子系統中不可能有樸素現實主義的容身之地。
注釋
1. 本書譯文有誤,将實體學家Stephen L. Adler和美國路透社前社長兼總編輯Stephen J. Adler混淆了。——編者注。
2. 這裡我需要進行一些補充說明,非專業讀者可以跳過這部分内容。可能有些專家會反對我對香農關于資訊定義的描述,指出那個量等于該資訊熵的負數。他們會辯稱,熵是一種客觀存在的自然實體屬性,(在系統處于熱力學平衡态時)由熱力學定律限制。既然香農定義下的資訊與熵存在聯系,那麼它就一定得是客觀且符合實體學規律的。我對此有三點要說明:首先,熱力學定律限制的不是熵本身,而是熱力學熵的變化。其次,就像卡爾·波普爾幾年前指出的那樣,與香農資訊定義相關的熵的統計學定義并不是一個完全客觀的量,它取決于粗粒度的選擇,而粗粒度能近似地為我們描述系統。就特定狀态來說,如果能準确描述系統,那麼它的熵一定是零,這種近似描述特定化的需要就給熵的定義帶來了主觀元素。量子系統的熵取決于形成兩個子系統的分裂過程,我們在這類過程中就能看到主觀元素的存在。最後,資訊的熵屬性是一種定義,用香農給資訊下的定義來定義。
3. 本書給出了三條規則,規則二:這個定律描述了量子态如何回應測量操作,即立刻坍縮成可被測量的具有精确值(這個值由測量操作決定)的狀态。規則二表明,隻能用機率性描述預言測量操作所得到的結果。不過,在測量結束之後,被測系統的量子态就改變了——測量操作把系統放到了與測量結果對應的狀态之中,這個過程叫作波函數坍縮。——編者注
參考文獻
[1] John Archibald Wheeler, “Information, Physics, Quantum: The Search for Links,” in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in the Light of New Technology, Tokyo, 1989, eds. Shunichi Kobayashi et al. (Tokyo: Physical Society of Japan, 1990), 354–58.
[2] John Archibald Wheeler, quoted in Paul Davies, The Goldilocks Enigma, also titled Cosmic Jackpot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6), 281.
[3] Christopher A. Fuchs and Blake C. Stacey, “QBism: Quantum Theory as a Hero’s Handbook” (2016), arXiv:1612.07308.
[4] Louis Crane, “Clock and Category: Is Quantum Gravity Algebraic?,”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36, no. 11 (May 1995): 6180–93, arXiv:gr-qc/9504038; Carlo Rovelli, “Relational Quantum Mechan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35, no. 8 (August 1996): 1637–78, arXiv:quant-ph/9609002; Lee Smolin, “The Bekenstein Bound, Topological Quantum Field Theory and Pluralistic Quantum Cosmology” (1995), arXiv:gr-qc/9508064.
特 别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衆号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閱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衆号,回複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擷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版權說明:歡迎個人轉發,任何形式的媒體或機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和摘編。轉載授權請在「返樸」微信公衆号内聯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