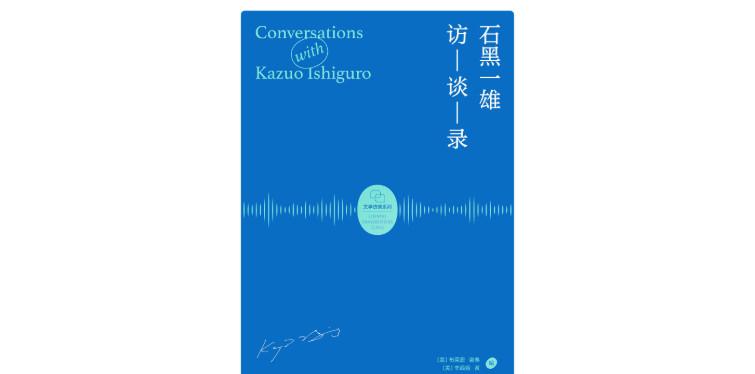
《石黑一雄訪談錄》,作者:[美]布萊恩·謝弗、[美]辛西娅·黃 編,譯者:胡玥,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原作者|辛西娅·黃
摘編|張進
石黑一雄的前兩部小說均取景日本,第三部以英國為背景,第四部選取了歐洲一個不知名的國家,最新的一部則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倫敦和上海。評論家們深入探究了這些背景和相對應的曆史語境,進而挖掘出它們的象征或隐喻含義,并找出作者的哲學視角。石黑一雄本人更願意将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對人類經驗世界性或共通性的表達,這是在闡釋身為作家的願景或目的時他提到的奮鬥目标。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日裔英國小說家。1989年獲得“布克獎”,與奈保爾、拉什迪并稱“英國文壇移民三雄”。201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讀者看小說不應該主要為了弄懂史實”
辛西娅·黃:1989年,你告訴大江健三郎:“我其實并不在意我的虛構世界與曆史現實是否吻合。我強烈地感覺到,這才是我——一個創作虛構藝術的作家——所應該做的:我應當創造我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對着現實的樣子照搬照抄。
你現在如何看待曆史現實與小說創作間的關系,比如尤其就小說中的上海和日本而言?
石黑一雄:我的言下之意不是說,曆史學家也許早已将某段曆史中的事實或者當時的情形蓋棺論定,而小說家對此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我想要強調的是那些并非小說家的首要關注。我想說,讀者看小說不應該主要為了弄懂史實。我是在借用曆史;我的意思是,我不希望我濫用了曆史,但是沒準我也會偶爾為之。
黃:小說家的作品和曆史學家的作品相比,主要差別是什麼?
石黑:曆史學家不得不以嚴謹的方式處理史料。他們必須擺出事實,必須帶着學術的嚴謹為他們了解的曆史而辯護。我沒有這樣的義務。我可以把曆史當成故事的發生地。我覺得通常我都是這麼做的。我選取曆史上的某一段時間,因為我覺得它有助于引出某些主題。
最後,我希望人們在閱讀我的作品時,不是因為可以借此了解這些事件發生的曆史時期,而是因為我也許可以與他們分享一些關于人生和世界更抽象的構想。
黃:小說家對這樣的人生構想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石黑:我的确認為小說家必須承擔一定的責任。每隔幾年總有某種大屠殺回憶錄招來人們的反感,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謊言贻害無窮。呃,最近就有件非常耐人尋味的事——“威爾科米爾斯基事件”,這就是個反例。他的作品1995年出版,摘得多項獎項。人們以為這是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長大的小孩寫下的一部紀實文學——這本書叫《碎片:回憶戰時童年》——幾乎是一夜之間,它成了——或者說似乎成了——大屠殺寫作的裡程碑。隻不過事實上随後就被揭穿原來是作者捏造了一切。
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并非猶太人,而是個瑞士人。倘若他承認這是部小說,那麼一切都安然無恙。實際情況似乎是這樣:他想表達的是有關個人生活的某種内心痛苦。他曾經是個孤兒,來自當時瑞士社會的底層;他被一些據他所說對他并不好的人收養。他認為大屠殺——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長大——的經曆就是對他的人生觀的某種恰如其分的表達或者隐喻。
這起事件挑起了有關虛構文學與非虛構文學之間差異的激烈争論。倘若他從一開始就說清楚自己是瑞士人,也從未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待過,說明白他是以小說的形式來創作,因為個人環境與大屠殺毫無關聯,他隻是覺得自己和大屠殺的幸存者有某種共鳴而已,那麼一切就肯定情有可原了。
但是當他言之鑿鑿地肯定自己當時的确身處奧斯威辛,并且這是一部曆史記錄的時候,他當然就觸碰了底線。這部作品仍然和1995年出版時一模一樣,但是如今,它已被棄如敝屣。這本書變得臭名昭著。現在成了全世界的笑話。這是模糊二者(曆史和虛構文學)界限的極端例子。
我認為二者不是一回事,你從小說中擷取的所謂真相和曆史學家意欲呈現的真相相去甚遠。
黃:你在小說創作中找到的“真相”是什麼?
石黑:我認為它并非像曆史學家追求的史實那般明确,事實上也不是在法庭上擺出證據,人們想要弄清來龍去脈時所探尋的真相。這裡的真相有點模糊的意味。它就像一個人在說:“這是看待人類情感經曆的某種方式。難道不是與你的觀點不謀而合嗎?”
它訴諸的是其他人對于事實的了解:“難道你不也這麼看問題嗎?難道你不也這麼想嗎?”
而且我認為,如果你想表達的内容略有不同或者略為新穎的話,那麼你想說的是:“也許你從未這樣看待問題,但是既然我這麼了解,難道你沒有同感嗎?”從那層意義上而言,它是對真相的追尋;它并非擺出證據說:“這兒有全部的證據,是以結論必然要變更。”它既不是那種科學真相,甚至連社會科學真相也算不上。在我看來,它更多的就像是在體驗人生中找尋知音。
《克拉拉與太陽》,作者:[英]石黑一雄,譯者:宋佥,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1年3月
“當今的寫作是一種交流過程”
黃:寫小說時,你是否有理想讀者在心中?
石黑:沒有,對于為什麼樣的人而寫作我其實稀裡糊塗。我認為這必然越來越受到實際情況的影響。作品出版後,事實上我要飛遍世界各地,做圖書宣傳或是接受訪談。是以,毫不誇張地說,顯然我在談話時對這些人的某種印象不知為何就留在了我寫作時的腦海深處。
我的言下之意并不是我會刻意地想到西雅圖的某個聽衆或者在挪威采訪過我的某個人。所有這些經曆有點堆積起來進而形成了某種讀者混合體。這個形象難以辨識清楚,有時候還讓人望而生畏,尤其因為我們所謂的全球化趨勢。
剛涉足小說創作時,這個想象出來的讀者和我年紀相仿,背景相似,但是随着我去的地方越多,越來越明白不同國家的人們有着相差甚遠的設想,林林總總的當地文化也會随之進入到我的作品中,我覺得自己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存在于頭腦中的這個讀者。
假如說這個想象出來的讀者是個挪威人,這樣一來,很多也許可以書寫的東西立刻就化為烏有。我不能用倫敦當地人熟悉而挪威人摸不着頭腦的東西;我不能用太多雙關,或者僅僅因為措辭睿智,用起來恰到好處,而寫上一句讓我洋洋自得的話——我不能因為這些緣故而引以為豪,因為等到作品翻譯成挪威語的時候,它就會黯然失色。
是以我必須實實在在地扪心自問:“這一句言之有物嗎?不是僅僅在賣弄小聰明吧?它的價值在譯文中仍然存在嗎?”
黃:你如何看待這個想象出來的讀者在你創作其他方面的作用?
石黑:從主題上看,我也許會把某個令當下英國人惶恐不安的大事當成一本小說的絕佳主題,但是再一次,這個想象出來的讀者會在我的頭腦中思忖——假如說(這個讀者)是挪威人,當然也許是丹佛人或者别的——好吧,對這個人來說,這個問題可能無足重輕。
在我看來,一個人去的地方越多,他就越需要按輕重緩急來回應不同文化下的讀者。這位想象出來的讀者就會變得越來越難辨而複雜。有時候,它會讓你束手束腳,寸步難行,對你求全責備。
黃:你讨論了評論界對你作品的反響,認為“克制”“含蓄”“幽靜”這些形容你小說内容的字眼讓你大為吃驚。知道這些評論是否會阻礙你的某些嘗試,或者是否會鼓勵并促使你試水其他東西?評論家的言論與你作為作家的舉動是否有直接的關聯?
石黑:我不知道是否必然有直接聯系,但是我無法脫身于評論家的言論。我的意思是,我通常會看許許許多的評論。我從不在意任何個人的評論。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能在國際上出版的好處就在于,浸淫于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學文化下的各色評論都盡在你的掌握之中。那麼,當人們似乎達成了一種共識,我就不能假裝這毫不重要。不管我怎麼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這真實表明了人們對我作品的反應。
不是隻有倫敦文學界獨有的怪異曲解之風這麼了解,而是身在德國或美國中西部或日本的讀者通通衆口一詞。這就能相當有效地斷定,在任何時間段内,在廣泛的人群範圍中,我的創作反響如何。
但是我無法将那樣的評論與我或許從書展上遇見的普通讀者那獲得的回報割裂開來。這種公衆回報都會左右我,因為我确實認為當今的寫作是一種交流過程。部分是因為這個行當要四處奔波,直面讀者,我對于這樣一個交流過程非常敏感。事情并非僅僅是我碰巧寫了這個東西,然後其他人碰巧讀到了。事實上,我努力去衡量的是人們如何接受我所做的事,他們了解什麼,不了解什麼,哪些地方他們覺得過猶不及,哪些讓他們忍俊不禁,又有哪些讓他們無動于衷。
我認為這些東西十分重要,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我了解其他人的方式,了解在作品的回報上他們與我有多少相似或不同之處。
黃:這樣的思維碰撞與你而言有多重要?
石黑:之前我說過——當時你問我小說家追求的真相是什麼——我想到的是疑問:“難道你對此沒有同感嗎?這是我的看法。”我抛給别人的正是那樣的問題,是以他們的回答至關重要。
但是我并不會真的這樣回應一衆評論,說自己也許更應該這樣寫,或者那樣寫;我不會這樣去做。
你知道,作品的概述對我來說和評價一樣意味深長。他們在概述時,吸引我的是他們會如何總結小說,他們會覺得作品中哪些地方是核心内容,會如何解讀某些東西,以及那一切是不是我期望強調的内容。
關于《長日将盡》,之前我會說我很抵觸許多人從“日本性”來讨論我的作品,就好像是它們隻有對癡迷于日本社會的人來說才有意義一樣。我說的是早期作品。我創作的小說以和日本毫無關聯的英國為背景——顯然,那個決定也許受到了主流觀點的影響,因為它們将我的作品看作是對日本社會的曆史或者社會觀念的闡釋。
黃:這些累積下來的回報促使你審視了作為作家的發展曆程?
石黑:《長日将盡》證明,我回應的不是一兩位對我應該如何寫作指指點點的批評家。恰恰相反,總體而言我是有所不滿的,因為人們在我早期的日本小說中過度搜尋資訊,就好像我能和人類學家,或者記錄日本文化的紀實作家那樣,揭示出耐人尋味的資訊。
我覺得,可能我想表達的關于人類和人生更共性的東西變得越來越晦澀模糊。他們沒有附和說“哦,是的,我就是這麼想的”,而是說“這些日本人的想法真有意思啊”。
以日本為背景(在早期小說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們的評價,有點會讓讀者誤解我的寫作初衷。是以,那個例子說明作品的整體解讀方式會左右我的決定。
《長日将盡》,作者:[英]石黑一雄,譯者:馮濤,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5月
“所有人都不得不走出童年保護的肥皂泡”
黃:在你的第五部小說《我輩孤雛》中,讀者們不應該心存期待,認為他們會找到不曾在曆史書中讀到的三十年代舊上海的某種史實,是吧?
石黑:我認為是這樣,他們找不到的。我所做的就是研讀能找到的資料。有一兩本書是我從珍本書店中淘來的,寫于那個年代(三十年代),但是據我所知,書中沒有說到不為人知的内容。裡面提到了鴉片戰争——這點人盡皆知——任何一本關于舊上海的書都會說到那些東西。
人們對上海津津樂道。也許我可以推薦這方面的許多好書,它們由訓練有素的作者撰寫,這些人追求的是研究藝術的精益求精,通過史料得出結論。
我把上海用作某種隐喻的場景。我是個靠不住的人;要是想了解曆史細節,我是不會信任我這樣的作家的。(笑)
黃:你能談一談《我輩孤雛》中的主旨或者母題的重要意義嗎?諸如像“孤兒”,還有《長日将盡》聯想到的“偉大”等主旨或主題。
石黑:關于孤兒的問題,這并不僅僅是字面上的孤兒。當然,這部作品裡,這些角色的确都是孤兒——他們的父母要麼去世,要麼失蹤。這兒的孤兒狀态有隐喻的意味。我希望在此處探讨的是所有人都不得不走出童年保護的肥皂泡,置身其中時我們對外界的兇險一無所知。
随着年紀漸長,我們走入更廣闊的天地,懂得了命運多舛。有時候,這一過程溫和而舒緩;有時候,對有些人來說,則如晴天霹靂、急風驟雨。主人公克裡斯托弗·班克斯生活在相對而言受到庇護的金鐘罩裡,活在受保護的童年裡,他以孩子的眼光看待世界,他認為自己有了天大的麻煩,但其實不過是些小孩子們不要闖禍之類的小問題而已。
突然,他被扔進了成人的世界。問題變成了:當我們走入更險惡的世界,我們是否帶着懷舊之情,帶着曾幾何時我們相信世界是個美好所在的回憶?也許,我們被大人們誤導了,也許準确地說,我們被保護着免受這些厄運的侵襲。
之後我們走入了大千世界,發現這裡有着污穢之事和棘手難題。有時,也許我們仍然殘留着孩提時代的天真想法,并且有着想要重塑世界、拯救世界,想要讓世界複原成孩提時代模樣的沖動。
是以,最新的這部作品主要講的就是一個猝不及防失去了童年天堂樂園的人。随着他的長大,也許是無意之間,他一直持有的人生宏偉目标就是要修複曾經的錯誤,這樣他才可以從哪裡跌倒從哪裡爬起。
我所說的“孤兒”,指的是最廣義上離開了我所說的保護我們的童年世界。
《我輩孤雛》,作者:[英]石黑一雄,譯者:林為正,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黃:“懷舊之情”如何植根于克裡斯托弗對過去的曆史意識?
石黑:最深層意義上的懷舊主題——我說的并不是全球旅遊産業有時會兜售的那種懷舊,也不是無害的前工業時代才會有的某種美好而悠閑的過去。我說的是更為純粹的個人對童年生活的懷舊之情。
有時,我認為那種懷舊可以是支非常正面的力量,也可以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因為就像是理想主義之于才智,那種懷舊之情對情感也有同樣的作用。你飽含深情地記起一個時代,那時認為世界是個美好的所在。
當然,有時候這種情緒會将你引向毀滅的舉動,但是它也可以讓你想将一切變得更好。
黃:帝國主義主題似乎在你的小說中至關重要。人類對曆史事件的否認,犯下的罪責或者承擔的責任總會以某種形式出現在你的小說中。這部小說呢?
石黑:帝國主義能說的都說完了,我沒有什麼高見。這本書中對于那些主題都有涉及,但是關于帝國主義沒什麼驚人發現。
這本書涉及的帝國主義稍有不同,因為它并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我們讨論的并不是比如說印度的情形(處在大緻相同的時期),英國在那執掌大權,而印度是它的殖民地。我們讨論的是非官方的帝國主義,從根本上說上海仍是中國的城市,外國人隻是赢得了所謂的“治外法權”,意思是他們不受中國法律的限制。
所有這些外國工業家蜂擁而至,并且定下規矩他們不受中國法律的制約,這對于中國人而言是奇恥大辱。但是那就是當時的軍事形勢。
是以事實上,這裡的背景不一樣:敵對勢力——英國人、日本人、美國人,全都虎視眈眈,想要從經濟上和工業上占據主導,剝削中國,但是并沒有帝國主義概念上殖民别的國家時所謂的那種責任。
即使英國統治者也許有自欺欺人的成分(就印度而言),他們當時的确有要給當地人灌輸英式生活方式和英國制度的宏偉想法。這個過程很複雜,并不是簡單的剝削。我認為在上海的那些人不覺得自己肩負這樣的責任。在很多方面,你可以說他們享受到了殖民的許多益處,卻無需承擔任何責任。但是當時并沒有任何勢力在上海掌權。稱其為帝國狀态是不嚴謹的,因為情況并非如此。
黃:你怎麼看克裡斯托弗透露出的對父母失蹤的了解?我們是否應該解讀為有關鬥争的寓言?
石黑: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小說是仿拟的形式;設定了這些謎團,一定程度上而言,我覺得要想符合這種叙事風格,你得給出答案,是以在那層意義上謎團得以解開。有時候,謎團是在更深層次上得到化解的。我不知道這樣的揭露是否意在表達宏大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它們就是用來推動情節發展的。
也許克裡斯托弗的發現——這個原以為是在和邪惡鬥争的人,到頭來卻發現自己從邪惡中獲益——有其深意。
這并非惡棍或江洋大盜身上會表露出的某種邪惡——我是說,你無法對邪惡追本溯源。它無處不在,那些初衷良好的人有時到頭來就會助纣為虐。那時,他就是個天真無邪的孩童,結果毫不知情地從邪惡中獲益。
在小說的開始,他的想法非常簡單,就是作為一名偵探如何與邪惡鬥争:你揭露真兇,把邪惡的精靈放回瓶子裡。最後,他發現邪惡天生就有着盤根錯節的複雜關系,你很難出淤泥而不染或者獨善其身。
《遠山淡影》,作者:[英]石黑一雄,譯者:張曉意,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年5月
“我對于什麼角色是男性、什麼角色是女性并不十分在意”
黃:有一次我參加會議,會上對你作品的一項批評就是你對女性的呈現很有限。然而,有人指出你的小說處女作就是以第一人稱的女性口吻來寫的。那麼這部新作中的女性人物呢?詹妮弗、莎拉還有母親都在克裡斯托弗的探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石黑:呃,我不知道。寫小說的時候,我對于什麼角色是男性、什麼角色是女性并不十分在意。當然,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我是意識到的,但是你不一定會在寫作時把特點分派給不同的群體、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性别。你創設的人物互相作用,那就是最終呈現出的模樣。
對我來說,把《遠山淡影》中的佐知子和這本新書中的詹妮弗相提并論有點困難。當然,她們都是女性,但是她們扮演的角色相去甚遠,她們截然不同。除了都是女性外,我不知道……
原載于Clio雜志第30卷,第3期(2001年)。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有删節,全文見《石黑一雄訪談錄》一書。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