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讓那個模特新人在畫室裡面來回走動,不時擺出各種站立的姿勢。
“好的,就這樣。别動。”
他站在畫架前,托着下巴想了想,蓄起的胡子讓此時的這位年輕畫家更像是個哲人。
他望着女孩補充了一句,“右手請再擡高一些。用食指與拇指捏住帽子的縧帶。”
“很好!”他表示滿意。
接着,他轉過身,對着畫室另一側圍觀的衆人深深鞠了一躬,“我要開始了!”
人群中有沙龍的評委、自己的畫家朋友以及前來湊熱鬧的街坊鄰居。
如果自己的父親也在其中,那該多好——他心中這麼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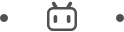
當他在畫布上抹下第一筆的時候,這個世界就僅剩下畫家與眼前的缪斯女神。
女孩身着一套黑綠兩色的拖地長裙,這是他向自己那位超有錢的朋友弗雷德裡克借的。
有品位的弗雷德裡克告訴他,這是第二帝國時代的華美象征,沒有一個女人不會愛上這種面料的質感,沒有一個女人能拒絕這種褶皺貼地的造型;沒有一個男人不會被這種賞心悅目的畫面撩動心思。更為重要的是,黑綠兩色的布面折射出那明暗不定的光澤,能賦予天才藝術家捕捉色彩變化的契機。
弗雷德裡克讓女模特再穿着一件短皮襖的建議,他也聽了——如此昂貴的大衣,當然還是這位财氣側漏的朋友借給自己的。
在如實記錄光與影的時候,這位年輕的新人畫家時不時想起啟蒙老師對自己的忠告,但他不能了解如實記錄畫室内的場景與畫室外的風景究竟有哪些不同。
此時此刻的他,隻想着如何在畫布上複原這個新晉女神的一切。
她有一頭褐色的長發,細嫩的皮膚顯得有些蒼白,因為化妝的緣故,那帶着陰影的眼睑讓人覺得她會永遠拒人千裡,然而,她長長的睫毛似乎又在招呼人不要膽怯。她的雙眼看向身後,那微微嘟起的雙唇,暗示着她欲言又止。
在畫家的筆觸下,女孩的頭部、上身與長裙形成了強烈的“明、暗、明”對比。無論是衣物的光澤、皮毛的觸感、嘴唇的紋理,還有她全身散發出的那種傲慢、惹憐、倦怠、欲拒還迎的氣質,等等的一切都被畫家進行惟妙惟肖地還原。
他不知道為何自己在之前從未達到這樣的精度,他無法解釋為何在她面前,他塗抹的每一筆都是那麼無可挑剔,好像每一筆原本就在那裡。
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終于停了下來。
他看了看畫,又看了看女孩,點了點頭。
他對這幅油畫相當滿意,在畫作右下角起了名字——《綠衣女子》。
他放下畫筆與顔料盤,轉身,再次鞠躬。
這意味着作品已經完成。
霎時,他面前的衆人爆發出歡呼與掌聲,聲浪好像要把畫室的房頂掀翻。
他的畫家好友用力拍着他的肩膀,表示祝賀。一位激動的沙龍代表,則将一枚銀光閃閃的獎章挂在他的身上。
多麼榮耀和具有意義的一刻啊!
對于一位初涉畫壇的年輕藝術家,獲得沙龍的銀質獎章,這意味着他獲得了主流和權威的認可。
他欣喜若狂,轉身大步走到那個女孩面前。
“感謝你,我的缪斯,這是我的榮譽,也是屬于你的榮譽!”
他小心翼翼地握住她的手,那隻小手是那麼白皙酥軟,好像輕輕一捏就能揉進自己的身體中。因為和姑娘的臉蛋貼得太近,他的臉色極不自然地漲得通紅。
兩人四目相對,含情脈脈,他終于試探着用自己的唇去期待少女的回應,少女嫣然一笑,閉上雙眼,她那長長的睫毛拉出動人的曲線,鼓勵着他勇敢一點,主動一些。
他與她擁吻,雖然兩人顯得有些笨拙,但他向她散發的那種溫柔似乎是要表達,“我想給她這輩子唯一的愛與所有的心”。
他重複着女孩的名字,看着心愛的姑娘喃喃自語,“幸福得有些不真實,這是夢嗎?”
這一切,當然隻是個美麗的夢。
他睜開雙眼,那個深愛了6年的臉龐就在身邊。
熟睡中的她,臉頰微紅,鼻翼和嘴唇随着呼吸微微翕動,
他盡可能輕手輕腳地穿衣下床,但木鞋踩在一段有些老舊的橡木地闆上還是發出了不小的“吱呀”聲。
這雙木鞋還是兩人之前從荷蘭傳回法國前,她為他買的禮物。
“克勞德,你要去畫畫了嗎?”一個近似呢喃的聲音問道。
“是啊,親愛的。”他盡可能緩緩地走到窗邊,柔聲細語地回答。
“噢,好像昨晚你和我說過,想一大早去港口找點靈感。”
“是啊,親愛的。”
”早餐想吃點什麼?我馬上給你做。“他的妻子還沒睜開迷蒙的雙眼,已經想要起身。
克勞德趕緊把妻子纖小的身體按住,“我自己随便弄點就可以,現在才5點,你再多睡一會吧!”
“那。。。。。。等你回來,我們一起吃中飯吧!”這個慵懶的聲音說。
“好啊。”
他為妻子重新整理被子,他望着她的臉,她低垂的睫毛、她的眼睛、她的笑容、她那豐腴美麗的肉體,她那動人心魄的靈魂,他早已刻骨銘心。
他輕吻了她的臉頰。
“我愛你,卡米爾。”
“我也愛你,克勞德。”
他小心關起卧室的門,蹑手蹑腳地來到廚房,像一隻機警又可憐的老鼠。
他本想燒點熱牛奶咖啡就點冰冷的長棍面包就這麼将就下,但打開窗戶想透透新鮮空氣的瞬間,秋末冬初的清晨冷風迅速讓他打消了這個念頭。
背着一堆畫具,還要花上至少半小時才能從家到達勒阿弗爾港,肚子裡可不能沒有幹活。
他點起火爐,把昨晚吃剩下的香腸、牛肉、洋芋什麼的都一股腦倒進鍋裡。
這一鍋亂炖,像極了之前那段混亂的歲月。
他終于不顧父親的反對娶了那個在咖啡館認識的模特女孩,那個女孩也無視家人的責罵義無反顧地嫁給了這個貧窮又孤獨的年輕藝術家。
他們的婚禮實在是過于簡單,簡單到甚至沒有彌撒。
然而,她并不在乎。
一點兒也不在乎。
克勞德對卡米爾一直心懷愧疚。
在确定戀人關系18月後,卡米爾就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然而,她分娩時克勞德并不在身邊,她的家人也不在。
于是,當時這個隻有19歲的女孩隻能孤零零地照顧自己和兒子好一段時間。
克勞德的藝術起步并不順利。即使兩年前他以卡米爾為模特的《綠衣女子》獲得了巴黎沙龍的認可,他的作品并沒有得到市場進一步的積極回應。
當時不少學院派大師、畫廊老闆、熱衷藝術的買畫富人和藝術投機商,都對克勞德的畫予以各種批評。畫賣不出去,就意味着克勞德陷入必然的貧窮;而父親對自己的追求報以極大的否定,更讓他連向家裡尋求幫助的可能都沒有。
一天晚上,對他賒賬過多過久已經難以忍受的房東,突然闖進屋子,沒收了克勞德的所有作品和作畫工具,将他掃地出門。
悲憤交集的克勞德直接跳進了冰冷刺骨的塞納河,想淹死羞愧難當的自己。
感謝上帝,他這次的魯莽自殺毫無疑問地失敗了——他忘了自己其實會遊泳。
這一切将年輕藝術家一步步逼進讓人絕望的境地,他的情緒變化開始越發無常,時而長久的沉默,時而長久的憤怒,他的語言與動作都變得猙獰可怕,像極了一隻正在咆哮的雄獅。他在屋子裡一幅幅地毀掉自己的畫作,咆哮着對這個世界的不滿。
而他心愛的卡米爾則在屋子角落中被吓得瑟瑟發抖,不敢動彈,隻能在一旁悄聲提醒:我們的孩子還在隔壁屋子裡睡覺呢!
終于,他停止各種咒罵,開始來回踱步,心緒終于穩定下來。
她與他在一起,從未提出過任何要求,她一直平靜地接收着克勞德所有的喜怒哀樂。而克勞德打心眼兒佩服并感激卡米爾能用那副看似弱不禁風的身軀抗住所有的壓力,不管是拮據、孤獨,還是失望、羞辱。
這個溫柔、腼腆、善良、美麗的女子身上有多大的能量?克勞德不知道。或許這種奇妙的謎團就是他總是為她着迷的原因之一吧!
她總有各種方法幫助克勞德把一堆亂麻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
他慢慢地被她的樂觀與堅韌感染,重整旗鼓,他對妻子和兒子的愛轉化成了一種力量與眼光,這種力量與眼光促使他注意到如何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
他的畫開始被人格外關注了,訂單開始變多了,生活開始明媚了,一切開始真正變得好起來了。
她曾經照亮了他的畫布,她也将照亮他一生所有的畫布。
他就着一杯勃艮第紅酒吃光了一鍋熱氣騰騰的亂炖。
一種富足的溫暖感包裹全身,他信心滿滿,好像一個知道即将去打一場必勝戰役的将軍。當然,似乎隻是因為他知道今天是個不錯的日子——因為昨天傍晚,他仔細觀察過了雲彩。
克勞德穿起那件野外寫生時常穿的破舊外套,拎起那個陪伴多年的木條箱,背起畫布和其他需要的工具,心滿意足地走出家門。
外面有點黑,整個城市還在熟睡,幾點星火,像是在指引克勞德完成夢想的方向。
他知道,回來的時候,整個世界會一片光明。
他還知道,他必須一次又一次地留下光與影,隻有畫畫、不停地畫畫,不停畫出世界上最偉大、更偉大的畫作,才能給自己心愛的人所有她想要的。
他沿着塞納河邊供纖夫行走的小道,向着勒阿弗爾港口的方向走去。
時間伴随着克勞德的腳步一分一秒的過去,整座城市緩緩蘇醒,地平線已經能依稀看到。
童年的地平線,那是他童年的地平線哪!
十幾年前,就是在這裡,克勞德與啟蒙導師布丹一起在野外采集靈感。
就在幾年前,他曾帶着卡米爾向着地平線的遠方逃去——因為戰争來了,他們這些可憐人為了躲避災難,隻能遠赴倫敦。
克勞德厭惡戰争,厭惡與普魯士宣戰的拿破侖三世。
如果沒有那些兵荒馬亂,他的好友弗雷德裡克也不會永遠留在前線;他與卡米爾,還有其他藝術家們也不必遠赴他鄉。
皮埃爾的來信告訴他,巴黎一度到處都是戰鬥、破壞、劫掠和火災,靜靜流淌的塞納河像是整個法蘭西的眼淚,哀悼那些往昔的平和與美好化為一片狼藉。
雖然勒阿弗爾港口重建的鐵路與大橋,展示着一種毀滅、新生後的欣欣向榮,但路邊還未拆除的防禦工事,依舊提醒着來往的人——這裡也曾一度風聲鶴唳、死氣沉沉。
遠方傳來火車的鳴笛聲,克勞德停下腳步,看着鐵道的方向,一列鋼鐵長龍正噴吐着灰白色的龍息向巴黎的方向駛去。
天空好像被這聲長鳴驚動,不自覺地有些泛白。
他想到了聖拉紮爾火車站。
住在巴黎的時候,他挺喜歡去聖拉紮爾火車站附近的那家英國酒吧,喝上一杯甜甜的杜松子酒,真是太美妙了。
他有時會孤零零地站在火車站大廳,像是在夢呓般念起那些城市的名字:魯昂、芒特拉若利、勒阿弗爾、吉維尼。。。。。。
噢,等回到巴黎,我可得去畫幾幅聖拉紮爾火車站——克勞德心想。
抽空再去看看魯昂大教堂吧!——克勞德心又想。
他從大衣的口袋裡拿着那件老舊的煙鬥,在木鞋的後跟上用力敲了敲,散落在草地的煙灰像是一段陳舊的灰色回憶,就這麼被輕松擱置了。他從大衣的另一個口袋裡掏出一包煙草,往煙鬥裡塞了一些,把剩餘的煙草小心翼翼地裝進口袋,又拿出一盒火柴,背着風擦響了一根。
火苗跳躍,這是燃動的希望,他将希望藏于煙鬥,後者漸漸地溫暖了指尖。
克勞德輕輕吐出淡淡的煙,與港口附近彌漫着的薄薄的霧氣,混為一體。
這是我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
克勞德邊想邊走邊看,終于找到了一個他認為視角最完美的地方。
東面,他能看到巨大的船和船桅、碼頭上的起重機、鐘樓還有人;西面,是一道海岸,此時,遼闊的海與天把它擠壓成了一條細線——他覺得這是童年來過的地方,甚至現在站立的地方,就是當年曾獨自作畫的地方。
他放下木條箱和畫具,開始為捕捉那個瞬間做最後的準備。
克勞德先在地上挖了一條溝,支上畫架,放上那塊昨晚就精心挑選過的畫布——這塊畫布并不大,隻有64×48厘米。
他把顔料擠在調色盤上的時候,不由得想起皮埃爾。
3年前,兩人一起畫《青蛙塘》的時候,皮埃爾憨憨地笑,說當年美國人鬧獨立的時候,我們曾給美國佬送各種武器,如今,輪到美國佬給我們送來推翻沙龍權威的強大“武器”了!
克勞德問,什麼武器?
皮埃爾揚了揚手中的錫管顔料,說:“這不就是美國佬發明的麼!我們這些畫畫的窮鬼都得感謝他!否則我們要帶着豬尿泡裝着的顔料到處跑!”
克勞德哈哈大笑,“如果我們真還用着豬尿泡裝着的顔料,又怎麼能外出畫畫呢?”
兩人相視,想到彼此背着畫架和畫布,帶着幾大包豬尿泡在大街上奔走的場景,又是一陣大笑!
其實,克勞德本來想約皮埃爾同來勒阿弗爾港寫生,但皮埃爾昨天來信說他那場談了7年的戀愛戛然而止,倘若克勞德這時還讓痛不欲生的朋友跑到港口吹海風,怕是太不厚道了。
克勞德倒了些許的煙灰,又加了些煙草,他叼起煙鬥,左手端着調色盤,右手拿着畫筆,像是一位胸有成竹、即将指揮千軍萬馬無往不勝的将軍;這一刻,他的雙眼環顧四周,眼神犀利如饑餓的鷹隼,靜心狩獵着令他動心的風景。
這是一個朝氣蓬勃、帶着霧氣的清晨。
蔚藍的海水波光粼粼,晨曦的水霧蒸騰而起。朦胧之美,很快就要被東升的旭日一秒秒地點破。各種影影幢幢已經開始消融,遠處的煙囪、吊車、建築等原本的外形慢慢顯露。
太陽終于躍出了海平面,開始撕裂雲朵,雲層的邊緣開始泛出明亮的金線,海面則被拉出一道越發耀眼的光,夜色與晨光、倦意與清醒、夢幻與真實,随着氤氲的灰色地平線越發清晰,也開始分離。
清晨的勒阿弗爾港,海水、天空、景緻,交錯滲透,光影在清晰與模糊中搖擺不定。
克勞德看得如癡如醉,這樣的畫面好像在童年無數次目睹,現在,嶄新的風景和千變萬化的色彩紛紛射進他的雙眼,湧入他的體内,搖蕩着、共振着。
布丹的那句——“當場直接畫下來的任何東西,往往有一種你不可能再在畫室裡找到的力量和用筆的生動性”——突然萦繞在克勞德耳邊。
此時此刻,他完完全全徹徹底底了解了這句話。
那種豁然開朗的狂喜感似乎要從他的胸膛迸出!
他知道自己期待已久的時刻終于到來了!
呈現在畫布上的隻是短暫的刹那,但這一刹那注定将成為永恒。
他立即拿起畫筆,盡情把這瞬間的景象塗抹在畫布上,盡情把各種色彩潑灑到畫布上。他必須迅速且精準——形式力求簡單、線條卻要格外精準——才能留住眼前所見在這個世界的瞬間。
他瘋狂地記錄着瞬間,也徹底無視這流逝的時間。
6年前,他畫《綠衣女子》時,也處在類似的狀态。
克勞德先是用橙黃或灰色的色塊渲染天空,畫筆在布料上窸窸窣窣地跳着歡樂的舞蹈;之後,他化身為一名建築師,讓遠處的工廠煙囪、港口上的吊車以深藍色的厚薄不一的長條屹立在畫面上;接着,克勞德又化身指揮家,色彩的樂符在畫布上輕快地跳躍,旭日在海面上的倒影、在霧氣中有些模糊不清的三隻小船和人影,都被他用道道短促的線條逐一譜寫,一派水光相映、煙波渺渺的印象看起來是那麼有韻律感。
旭日初升、霧氣迷蒙,這是真實的世界,還是想象的世界?
那天,陽光躍出海平面,讓厚厚的雲層瞬間變得輕盈柔媚的時候,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海水,還有灰色的日子,都已經消失不見了。
終于完成了!
這位将軍終于拿下了一場看不見敵人的戰争的勝利。
他看着這幅畫作,有些得意地點了點頭。
他想吸一口煙,卻發現煙鬥已經滅了。
他拿着煙鬥用力在鞋後跟上敲了敲,木質的煙鬥與堅硬的木鞋底攜手發出贊美的歡呼聲。他把煙灰磕出,又吹了吹,再往餘溫尚存的煙鬥中填滿了新鮮的煙草,重新點起——這一連串動作是那麼熟練、潇灑、精準,與他在畫布上記錄光影瞬間的狀态并無二緻。
噢,似乎還少了點什麼。
他想了想,在畫布的左下角簽上了名字與年份——【克勞德·莫奈,1872】。
是時候回去了。
克勞德對自己說。
他遠遠就看見帽子的絲帶飄蕩着。
卡米爾站在屋外,那濃秀的褐發打成辮子圍在頭上,她戴了一頂很大的帶耳搭的皮帽,皮帽上鑲着略長的黑色絲帶。這位姑娘一邊慢吞吞地、似乎是漫不經心地戴上一雙黑色小山羊皮手套,一邊在眺望、期盼着什麼。
似乎夫妻間的默契已經讓她知道他此時必将歸來。
她一眼就注意到他,興奮地揮了揮手。
“在幹嘛呢?”
“等你回來!”
“幹嘛不在屋子裡等,外面可冷了!然後準備去哪兒?”
“集市!”稍帶冷冽的空氣讓卡米爾的臉頰紅粉绯绯,神采飛揚,“想要烹饪一桌豐富的午餐,可是要去采購不少新鮮食材的!”
“等我把東西放進屋子裡,我們一起去吧!”克勞德說。
“你今天畫了什麼?”
他把新作展示給妻子看,“我畫了勒阿弗爾港早上的日出!”
“真不錯!”卡米爾由衷地贊歎着,“為什麼。。。。。。這個畫面看起來有點模糊?”
“早上有好大的霧!哦,親愛的,當時的場景真的太奇妙了!”
“太遺憾了,早知道我也一起去看看了!”卡米爾說。
“沒關系,每天都有像你一樣美麗的日出的!”克勞德撫摸着卡米爾的臉龐。
“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同的日出,而我隻有一個克勞德。”她略帶嬌嗔地說,微微擡起頭看着他。
那個瞬間,讓他想到了6年前。
在那家不起眼的咖啡館,當時就是這個微微擡頭、眉毛輕挑的可愛微笑,擊中了他的心。
那是就是他生活中的太陽,她的出現就像是創世的第一場日出,靈感和色彩的線條自然而然地從筆尖迸發,照亮了自己的世界和以後所有的路。
一眼萬年。
備注:
【1】根據有關研究,《日出·印象》創作日期為1872年11月13日早上7點左右。
【2】卡米爾是莫奈的發妻,1879年,在生下與莫奈的第二個孩子後不久,死于子宮癌,年僅31歲。莫奈以她的遺像滿懷悲痛創作了《臨終前的卡米爾》,并在簽名處留下了一生中唯一的【一顆❤】。
【3】1872年,莫奈的主要住所其實是在阿讓特伊,它位于巴黎郊外,此處距離勒阿弗爾的直線距離約有150公裡。
【4】本故事基于史實輕微改編。對莫奈有興趣的讀者建議查閱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