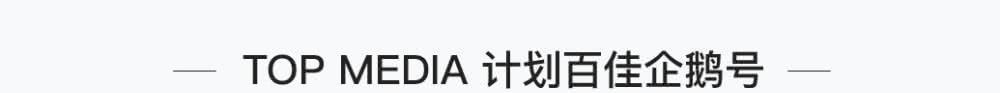
《易經》給詞人辛棄疾的命運提供了神秘的暗示。
那是在年輕的時候,辛棄疾和同學
黨懷英
一同去找算命先生用《易經》測算前程。黨懷英得了《坎》卦,就決定留在金朝。坎,就是坑。《坎》卦裡描述了重重風險,也提供了破解之道。
辛棄疾得了《離》卦,就決定南下到南宋的國土去。離,通假“麗”,就是太陽出來的壯麗景象。《離》卦中的《彖》有“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之語,象征人生奮鬥的蒸蒸日上的場景。用更通俗的話說,就是辛棄疾得到了某種命運的暗示,要他去折騰。
▲辛棄疾畫像。
1
辛棄疾不是瞎折騰。1140年生于濟南的他,長于幹部家庭。他爺爺辛贊後來做了縣令。辛棄疾跟随他到了亳州。在亳州,辛棄疾投師于當地頗有名氣的知識分子
劉瞻
名下學習。
這時,他結識了同學黨懷英。辛棄疾和黨懷英是同學中最有才華的兩個,很快就脫穎而出。兩人被當地知識界稱為
“辛黨”
。在古代,能這樣稱呼是很高的評價。比如辛棄疾還和北宋的蘇轼被後人稱為
“蘇辛”
。
轉眼間,兩人都長大了,開始各奔前程的時候了。一天,兩人帶着酒上了一個山頂。辛棄疾對黨懷英說:“吾友安此,餘将從此逝矣。”兩人痛飲一番,就此拜别,再未謀面。那時候的話别基本上就是永别,和“西出陽關無故人”是一種類型。因為他們出生、成長的地方是金朝的地盤,站在南宋的立場,就等于是“淪陷區”。
雖然是在“淪陷區”長大,但辛棄疾是懷有一顆南宋心的。爺爺
辛贊
做的是淪陷區的官。但他内心深處是熱愛南宋的,也想着宋朝光複中原的一天。當初南宋建立時,迫于族人衆多,無法遷徙,辛贊才留在北方。他有空就時常帶着兒孫登高望遠,分析地理形勢。 1157年,辛棄疾到金朝的都城燕京去趕考,但沒有成功。
三年後,他又去了一次燕京。但這次,他的人生方向改變了。兩次去燕京,辛棄疾除了趕考,還考察了沿途的地理形勢。這些考察為他日後的軍事生涯奠定了基礎。
1161年,金朝發動了對南宋的戰争。辛棄疾面臨重大的人生抉擇。他的選擇是南宋。這樣,發生了本文開頭他和同學各奔東西的場面。 在濟南附近的一個山區,辛棄疾組織了一支農民起義軍。他随後投奔了當地起義軍首領
耿京
在農民起義軍中,目不識丁的人居多,
辛棄疾毫不意外地成了文職工作的領袖,并擔任了他平生第一個官職:掌書記。
耿京的隊伍随後合并了和尚
義端
的部隊。義端雖然也反金,并且在軍事話題上和辛棄疾挺談得來,但是立場不堅定。
有天,他從起義軍中逃跑了,還偷走了辛棄疾掌管的大印。如果義端攜帶了大印去金朝投降,起義軍的損失是很大的。因為這事,耿京要處死辛棄疾。 這時,辛棄疾面臨人生第一次重大考驗。他對耿京說,“丐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立下這個諾言後,辛棄疾立馬去追趕義端,将他抓獲。辛棄疾不顧義端哀求,将其斬首,拿頭去報告耿京。耿京見到此景也大吃一驚。
▲辛棄疾劇照。
二十三歲那年,辛棄疾第一次踏上南宋國土。
耿京派人去朝拜南宋朝廷。這時,教育程度高的辛棄疾有了用武之地。在建康,他們一行見到了南宋皇帝趙構。辛棄疾還被封為右承務郎。 但等到他們傳回時,大事發生了。
在起義軍隊伍中,張安國等叛變,殺了耿京,去投奔金朝了。這時,辛棄疾再次顯示了他有勇有謀的能力。他和統制王世隆等人直奔金營,見張安國正和金朝将領喝酒。他們趁其不備,抓獲了張安國離去。金軍準備追趕。他們一行就大呼,說南宋軍隊十萬人要過來了。金軍就止住了。張安國随後被斬首。
經過了這幾次軍事洗禮,辛棄疾已經成長為一個成熟穩重的将領。
2
二十三歲這年,辛棄疾被任命為江陰簽判,正式開始了在南宋為官的經曆。 然而,安居一隅絕非辛棄疾的抱負。二十六歲時,他給南宋朝廷呈上了廣為人知的
《美芹十論》
。這是關于時政軍事的綜合論述。《美芹十論》展現了辛棄疾畢生的戰鬥理想。他的核心觀點就是金朝并沒有想象中的那樣強大,而是有很多緻命弱點。南宋應該秣馬厲兵,準備興複大業。光複大業的理想也經常存在于他的詞作中。在一首《念奴嬌》中,他哀歎,
“虎踞龍蟠何處是?隻有興亡滿目。”
他頗為欣賞宰相虞允文,給後者上書。虞允文的身上展現了主戰派對時間流逝的惋惜。比如他說,
“機會之來,間不容發,奈何拘此曠日彌久之計?
”
▲虞允文《适造帖》。
辛棄疾的一系列上書,展現了他成熟系統的政治軍事理念。但他不是一個隻懂高談闊論的人。比如他擔任滁州知州期間,就展示了施政的幹練。滁州是宋金拉鋸戰的戰場。他到任時,經過連年戰亂,大量人口跑路。辛棄疾通過各種方式招徕農民,還通過減稅招徕各色商人。商業讓城市恢複了活力。
經過半年時光,他就讓滁州脫離了半荒蕪的狀态。 文治的成功讓他在官場獲得了廣泛的聲譽。1175年,辛棄疾被任命為讨伐茶商軍的指揮官,展現了他的武功。茶商軍就是茶商組織的武裝,用來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保護茶商販運的安全,最早成立于湖北荊南一帶。作為對照,近代另一支有名的隊伍就是民國時期廣州的商團軍。茶商軍慢慢壯大後,對南宋朝廷構成了威脅。辛棄疾調集身強力壯的鄉兵和弓手,深入山區,将茶商軍擊潰。
然而,辛棄疾雖然有出色的軍事才幹,卻沒有機會用于更大的舞台:對金朝的作戰。在一首有名的《菩薩蠻》中,他發出了自己的喟歎——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餘,山深聞鹧鸪。
在擔任荊湖南路的轉運副使期間,辛棄疾給皇帝寫了一封奏折,反映了他對民間疾苦的深度同情,“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盜賊以剽殺攘奪害之,臣以謂不去為盜将安之乎?”
在這封奏折裡,他分析了百姓之是以被迫為盜的原因。但同情歸同情,辛棄疾在治理盜賊的問題上極其嚴厲。他的方式是抓住盜賊就殺,不要窮究來龍去脈了。是以,他的轄區盜賊幾乎絕迹。很難将這種嚴厲與他作為詞人的柔情對應起來。但回到曆史語境中,它們卻是有效的社會治理方式。 辛棄疾将對百姓的關懷體恤和對奸商的嚴厲打擊結合起來。
1180年,辛棄疾被任命為隆興府的知府。他剛上任就遇到一場大旱。饑荒眼看就要來了,怎麼辦呢?辛棄疾繼續他的鐵腕手法。他在十字路口貼出八個大字,
“閉粜者配,強籴者斬”
。就是說在旱災面前,囤積糧食的都要拿出來賣,否則要發配。強行向有糧食的居民搶糧的要斬首。這是維持秩序的第一步。
第二步,則是通過商業手法盤活市場,進而拯救危局。辛棄疾讓各行各業的人推薦一些精明強幹的人出來。然後政府借給這些人本金,限期一個月,讓他們四處買糧食過來到隆興府賣。糧食賣出後,這些臨時商人隻償還政府本金,不用支付利息。通過這種方式,大批糧食被運到了隆興府,當地糧價大跌。當地居民是以挺過了一場饑荒。
3
在江西上饒的帶湖旁邊,辛棄疾修建了一處住宅。四面被他開辟為稻田。這處臨湖住宅被他命名為
“稼軒”
。這個稱号後來變成了他的筆名。辛棄疾生平多次罷官,都回來居于此地。南宋有台官拼湊各種謠言,彈劾辛棄疾,稱他“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于是辛棄疾被第一次罷官。這次罷官導緻他長達十年的時間裡閑居在上饒的“稼軒”。
與陶淵明的歸隐情結不同,辛棄疾在“稼軒”是一種
“隐而欲發”
狀态。昔日陶淵明在戎馬倥偬中有“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的詩句。但辛棄疾的歸隐更多是一種不得志狀态,而且經常想着國家大計。比如在閑居期間作的一首《水龍吟》中,他寫道,
“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裡,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辛棄疾和浙東知識分子
陳亮
交遊頗深。 陳亮也有懷才不遇的境遇。在辛棄疾漫長的賦閑中,兩人曾長聚過十餘日。從這次交往中可以看出辛棄疾的孤獨。當他送陳亮離開時,長送不舍。兩人告辭後,辛棄疾又追上去。直到鹭鹚林的積雪擋住去路,他才作罷。晚上客宿一戶人家後,他在一首《賀新郎》中抒發了自己惆怅的心境:
佳人重約還輕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斷車輪生四角,此地行人銷骨。問誰使,君來愁絕。鑄就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長夜笛,莫吹裂!
像兩宋的衆多官員一樣,辛棄疾經曆了反複無常的官場罷黜和起用。當他再次被起用時,已經五十三歲了。他的抱負是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
,就是揮師北上,收複中原。但現實是,盡管提出過《美芹十論》這樣系統深刻的軍政主張,他至多被委任一些不大不小、無關大局的官職。著名詩人陸遊和辛棄疾也有交往。他在一首長詩中概括了辛棄疾的際遇,
“十年高卧不出門,參透南宗牧牛話”
。 另一位與辛棄疾有交遊的著名人士是
朱熹
這位南宋大儒也跻身不得志者行列。原因是他的學問被南宋朝廷打壓,并被扣上政治帽子“僞學”。朱熹本人也被稱為“僞學之魁”。當年官員被保薦,要聲明不是“僞學逆黨”。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也要提前聲明,和“僞學”劃清界限。這次“僞學”事件牽連的重要人物就達五十九人。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和朱熹來往都變成了一件有很大風險的事,遑論繼承他的學說。但辛棄疾不畏強權,仍多次與朱熹相會,因為他敬佩朱熹的學問和為人。 1200年,朱熹病逝于武夷山。南宋朝廷下诏,禁止衆門徒前去祭奠。朱熹的一些學生基于畏懼,就不敢前去。但辛棄疾不畏這些禁令,親自前往武夷山祭奠朱熹。他的祭文包括這些句子,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朱熹畫像。
生命後期,在對金用兵的背景下,南宋朝廷重新啟用辛棄疾,但也并未将他放置在統軍作戰的重要位置。這樣的安排也不無益處。
南宋少了一個頂級将領,卻多了一個詞宗。
1207年,在新的官職送達不久,六十八歲的辛棄疾與世長辭了。“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在去世前幾年的這首《永遇樂》中,辛棄疾像是自嘲,又像是不解。
但他和老友陸遊一樣,無法看到“王師北定中原日”的場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