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死後谥号“仁皇帝”,他的這個“仁”可謂當之無愧,在位的六十一年間,免錢糧,慎刑法、确實是曆史上一個難得的仁君。隻不過,康熙的“仁”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對待官吏太過仁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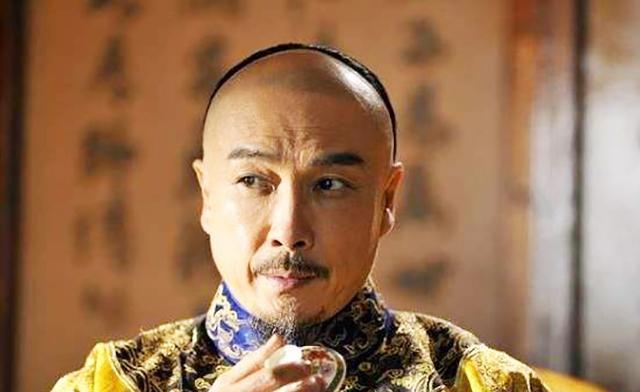
康熙一朝對官員的限制可以說是清代最為寬松的,是以也衍生了許多貪贓枉法之事,而康熙帝往往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要不觸碰政治底線,訓斥幾句也就完了。而在康熙朝,就發生了一起令人十分震驚的經濟案——王綱明買銅案。
王綱明不是朝廷的官員,嚴格地說是屬于皇商,他承辦每年戶部鑄錢所需的358萬餘斤黃銅。從康熙四十年到五十四年的15年裡,王綱明按照規定應該交給内務府節省銀256萬餘兩,但他卻隻交了186萬餘兩,欠70萬餘兩。
要知道,内務府的銀子就是皇帝的小金庫,王綱明吃了豹子膽,居然敢拿皇上的銀子。而且不僅如此,王綱明還欠交戶部黃銅1390萬餘斤,按時價每斤一錢五分計,折合有銀209萬餘兩。
王綱明承辦賣銅之案,應該算是康熙年間最大的經濟犯罪案。說其實最大之案,根據有三。一是王綱明欠交黃銅1390萬餘斤,這是朝廷鑄錢局一年額需銅360萬斤的三倍多,即三年多沒有銅來鑄錢,鑄錢局如不另設法緊急購買這些銅,就要停爐三年多,就要少鑄銅錢将近20億文,在當時錢少鬧錢荒的形勢下,那就是天塌下來的特大災禍。
二是虧欠戶部帑銀,這樣大的虧欠銀兩,在康熙年間,也是第一名。三是更嚴重、更惡劣、更不應該、更是膽大包天的罪過,是王綱明竟敢虧欠皇上的節省銀70餘萬兩,并且讓皇上拿出200多萬兩内庫帑銀替他還了戶部的債。
要知道,欠皇上的錢,那可是天大的罪過。按清制,皇莊的糧莊,欠皇糧一石,鞭打莊頭二鞭;采參的壯丁,欠一兩人參,鞭一十,欠二兩人參,鞭一百,枷四十日。王綱明膽敢欠交皇上70萬餘兩,怎麼說都該處以極刑,甚至是滿門抄斬。
可此案的處理結果令人難以想象,這種可以算是與十惡不赦相等的大不赦之罪,康熙帝竟然從輕發落,而且輕得沒邊。不僅不将王綱明押進天牢,擇日斬首,不籍沒家産,而且還大大減少其應還之銀,一再允許王綱明借口還債而讓其開礦買馬,拖欠不還。
從王綱明一案中,可以反映出康熙帝是為“昏君”,這裡所說的“昏君”二字,并非是罵康熙帝,而是以“昏”字為動詞,是說康熙帝昏了頭,是作為利令智昏的意思來用。
既然王綱明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就應該判令斬立決,籍沒家産,妻、子為奴,怎麼 還能作出免罪無罪并代還其戶部欠款等等極端的錯誤決定。這唯一能解釋的就是,王綱明曾為康熙帝,為内務府上交給數量巨大的效敬銀子,為皇上積攢堆積如山的内帑出過大力。正因為如此,康熙帝才利令智昏,竟當了既吃回扣索要節省銀又貪利枉法的大貪官角色。
此外,從此案中也可以看出大學士、戶部尚書等人也是庸臣。這裡特别要講講戶部尚書趙申喬,這次王綱明欠交1390萬餘斤銅,折合帑銀200餘萬兩的特大案子,就是趙申喬揭露出來的。
趙申喬,兩榜進士,曆任知縣、布政使、巡撫、戶部尚書,數谙律法,多次查辦大案,其“清廉、剛毅”滿朝盡知。他當然知道此案之重大、性質之惡劣,也應當知道應按不赦之大罪來審理,依律重判。可是,這次他隻是建議停止商人辦銅,恢複稅關買銅舊制,隻字不提嚴懲王綱明。
其他的大學士、九卿也和趙申喬一樣,沒有一位大臣站出來奏述處理意見。可見,康熙帝積攢内帑的威力實在是無比強大,把閣臣、九卿們一個個震懾住了,使他們淪為庸臣。
再來說一下王綱明,康熙帝為他還了大部分欠款,隻要求他拿出23萬兩。可是這筆錢一直到了雍正元年也沒有拿出來。這絕不是他沒錢,而是拖着不還,而且更讓人不能了解的是,王綱明居然在康熙五十四年還拿出了三千兩銀子,捐了一個三品頂戴,而康熙帝居然也準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