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博雅好書(boyabook)
多數的讀者都是普通人,對詩歌的了解平實、正常,對詩歌中的喜怒哀樂的感受不會有太大的出入。
金聖歎說:“作詩須說其心中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說心中之所誠然,故能應筆滴淚;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我詩者應聲滴淚也。”在優秀的詩人與廣大的讀者之間,确實存在着“心中之所同然者”,人們的心是相通的。
深受讀者喜愛的《莫砺鋒詩話》新一版于近期上市,這是一部镕鑄生命的感悟與詩性的光輝,展現古典詩詞撫慰人心的力量的大家小書。
本期微信将推送《莫砺鋒詩話》的序言部分。詩歌在你的人生中承擔着什麼樣的角色?
回複評論區參與讨論,将抽取兩位幸運讀者獲得贈書钤印本《莫砺鋒詩話》1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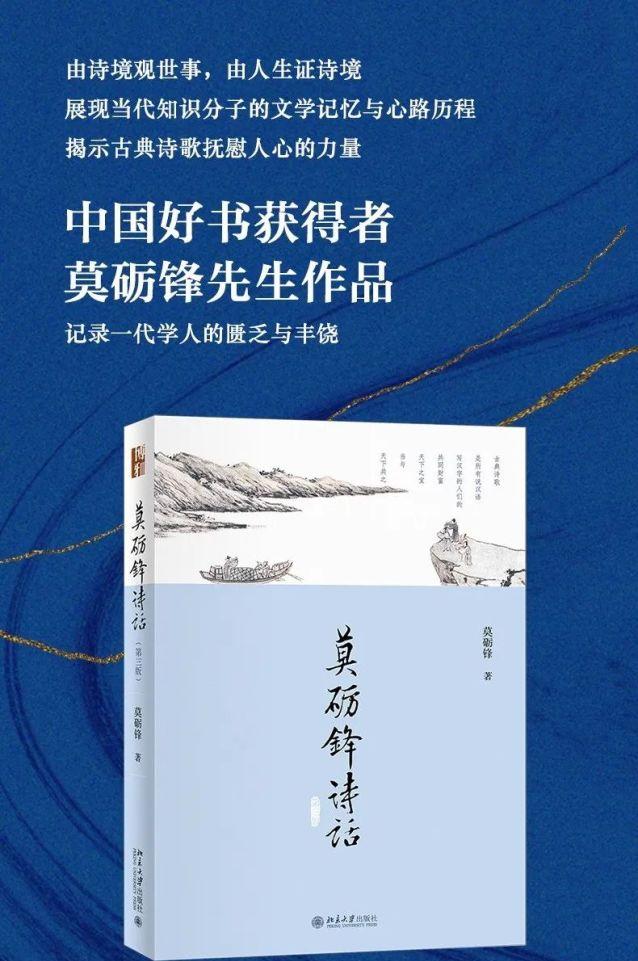
莫砺鋒詩話·序
我最早讀到的古詩是寫在一把芭蕉扇上的。那時中國的家用空調好像還沒有出現,電扇也尚未走進尋常百姓家,每逢揮汗如雨的季節,芭蕉扇便是人們唯一的消暑用品。我家雖窮,也配備了好幾把芭蕉扇,夏夜乘涼時人手一把,既用它扇風,也用它打蚊子。為了讓扇子更耐用一些,母親用碎布把扇子沿上一道邊,以防它開裂。于是我家的芭蕉扇鑲着各種顔色的布邊,物各有主,很容易辨認。父親的那把扇子更是與衆不同,它的邊上鑲着藍布,中間還熏着幾行字。那些字是父親的手迹,他先用毛筆蘸了濃墨在扇面上寫字,然後把扇面湊近煤油燈的火苗把它熏黑,最後用抹布蘸了水一擦,一塊黑底白字的鑲嵌物便出現在扇面上,樣子很像我們臨摹用的小楷碑帖。扇面上的那幾行字是: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當時我不大明白那些句子是什麼意思,更不知它們就是一首“唐詩”。我和弟妹們漸漸長大了,便羨慕起父親手裡的扇子來,紛紛央求父親在我們的扇面上也熏上字。再往後,我便與父親合作,他題字,我配畫。後來我家的芭蕉扇上總題着幾句詩,背景則是一座亭子或一株垂柳,再加上一鈎月亮。于是我又讀到了“但得暑光如寇退,不辭老景似潮來”“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等詩句,但我不知道它們的作者是誰,也不知道父親為什麼欣賞它們。
我與古詩相識雖早,卻多年未能發展為深交。一來我家根本沒有多少藏書,而且隻有《紅樓夢》裡有幾首詩詞,其餘的書都與古詩無關。二來我在中學裡一直迷戀數學和實體,對詩歌則敬而遠之。然而,在我高中畢業的那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迹,我心中珍藏了多年的關于清華園的夢想破滅了。兩年以後,我來到長江岸邊的趙浜村插隊務農。又過了一年,我把所有與數理化有關的書本一股腦兒賣給了廢品收購站,從此一心隻讀文科書了。插隊十年,生活相當艱苦,最苦惱的是沒有書讀。那年頭圖書館根本不對我們開放,書店裡也買不到我想讀的書,我千方百計從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處借點書來讀,但是杯水車薪,根本不能解我的饑渴。就在此時,我漸漸地迷上了古典詩歌。
我愛上讀詩的表面原因是詩很耐讀,好詩更是百讀不厭。一冊薄薄的《唐詩三百首》,就伴随我度過了無數個霜晨月夕。還有,詩易于背誦,我雖然并不想做詩人,也不相信“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說法,但翻來覆去地把手頭所有的幾本詩選、詞選讀了又讀,也就把它們全都背誦出來了。蘇東坡說:“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辄參禅。”他那是在玉堂值夜,明燈高照,持卷而讀。我沒有足夠的煤油來點燈,有時甚至摸黑吃晚飯,這時背詩的好處便凸顯出來了。記不清有多少個風雨凄凄的夜晚,我躺在床上默默地背詩,再細細地回味,幾十首背下來,寂寞的長夜便熬過大半了。
我愛上讀詩的深層原因是詩歌使我感動,給我安慰。我通過讀詩先後結識了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轼、陸遊、辛棄疾等人,他們可都是才華橫溢、品德高尚的傑出人物。他們屈尊走進我的茅屋,與我朝夕相伴,還敞開心扉向我細訴衷腸。相處久了,我驚訝地發現原來那些偉人都是與我同樣的普通人,他們的生活中有同樣的坎坷挫折,他們的心中也有同樣的喜怒哀樂。甚至那位亡國之君李後主也不是屬于另一個世界的異類,我曾在雨聲淅瀝的春夜默誦他的詞句:“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盡管我知道他那天潢貴胄的身份與我這個插隊知青有着天壤之别,我還是被深深地感動了。“文革”前的學者們曾為李後主詞有無“人民性”争得不可開交,在我看來,隻要能感動普通的讀者,那就是人民性。正如金聖歎所說:“詩非異物,隻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凡是好詩,一定是人人心頭都有的某種情思的自然流露,詩人的本領在于把它說得細緻入微、回腸蕩氣。當我讀詩時,往往覺得詩人就是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就是為我而寫的,那樣的詩當然會感人肺腑。
也許是我在茅檐底下與詩人們結下的因緣在冥冥之中引導着我,十多年後,當我以安徽大學外語系二年級學生的身份報考研究所學生時,南京大學中文系程千帆教授的“唐宋詩歌”方向竟成了我的首選志願。考進南大後,讀詩成了我的專業,後來又成了我的本職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決心把畢生精力貢獻給古典詩歌研究,來報答詩人們對我的恩情。
專業的讀詩者其實是很辛苦的,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隻讀自己喜愛的作品,也不能任意停留在欣賞、玩味的閱讀階段,他必須服從現行體制的規定,從古詩中讀出一篇又一篇的論文來。于是我耐着性子逐字逐句地讀完了《全唐詩》,其中有不少“惡詩”我再也不想讀第二遍,怪不得孟郊曾抱怨唐人“惡詩皆得官”。于是我從《唐詩三百首》中讀出了一首混進去的宋詩,我考證出嫁名張旭的《桃花溪》其實是北宋蔡襄寫的《度南澗》,這項“研究成果”實在有點煞風景。當我從事這些工作的時候,心裡一直有點遺憾,又有幾分歉疚。遺憾的是我在論文中無法充分表達我讀詩時所受到的感動,因為那是不符合“學術規範”的。歉疚的是我寫的文字盡管淺薄,卻都是象牙塔裡的東西,它們與大學圍牆外面的人們毫無關系。我很想與所有喜愛古典詩歌的朋友(不限于學術圈子)談談我最愛讀哪些詩,說說我讀詩的感想。當上海古籍出版社來約我編選一本中型的《宋詩選》時,我不假思索便把它看作實作上述想法的一個機會,當即與出版社簽了合同。沒想到雜事猬集,一年過去,我才讀到第五冊《全宋詩》,而尚未讀過的《全宋詩》還有六十多冊! 這樣下去,再過十年也完成不了《宋詩選》,我怕耽誤出版社的規劃,便提議撤銷了那份合同。
詩選一時難以完成,我便産生了寫一本詩話的念頭。詩話的性質是什麼?人們并沒有統一的看法。宋人許顗說:“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清人沈懋德說:“詩話有兩種。一是論作詩之法,引經據典,求是去非,開後學之法門,如《一瓢詩話》是也。一是述作詩之人,彼短此長,花紅玉白,為近來之談薮,如《蓮坡詩話》是也。”他們對詩話的定義過于嚴格,而且陳義過高,我要是那樣寫詩話,結果恐怕與論文差不了多少。其實最早的詩話原是歐陽修“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的随筆,不過内容與詩有關而已。清人章學誠對詩話大加撻伐:“以不能名家之學,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這倒從反面說出了我所認可的詩話的某些性質,即淺易、随意、輕松。我想寫的詩話便是這種關于詩的随筆,是我讀詩的零星感想。這些文字裡沒有考據、論證,也沒有注釋、參考書目,一句話,它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符合“學術規範”,它們發表以後絕對不能算作我的“學術成果”。我寫這些文字不是因為我對某首詩、某位詩人或某個詩學問題有了新穎的觀點,恰恰相反,我想說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談,即使有些讀後感是我獨有的,我也相信在相同的閱讀背景下多半會人同此心。雖說“詩無達诂”,但一首好詩所蘊含的情感傾向卻是清晰可感的,我想談的正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作詩是高度個性化的行為,黃巢落第後詠菊說“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那種激越的豪情是專屬于革命領袖的。但是優秀的詩人都是普通人,他們的喜怒哀樂是與千千萬萬的讀者相通的,這正是他們的作品家喻戶曉的原因。讀詩也是高度個性化的行為,郭沫若從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讀出了“赤裸裸地表示着詩人的階級立場和階級情感”,那種如炬的目光是專屬于紅色學者的。但是多數的讀者都是普通人,他們對詩歌的了解平實、正常,他們對詩歌中的喜怒哀樂的感受不會有太大的出入。金聖歎說:“作詩須說其心中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說心中之所誠然,故能應筆滴淚;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我詩者應聲滴淚也。”在優秀的詩人與廣大的讀者之間,确實存在着“心中之所同然者”,他們的心是相通的。鑒于以上看法,我相信我讀詩的感受是與其他讀者大同小異的,我完全可以敞開心扉與大家交流讀詩感想,不必擔心别人嘲笑我的淺薄。“嘤其鳴矣,求其友聲。”這本是古代詩人的心聲,作為古詩的讀者的我也有同樣的希望。
《列子·楊朱》中講過兩個笨人的故事,一個是“獻曝”,另一個是“獻芹”,後者的結果是:“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慚。”我從閱讀古詩中獲益匪淺,很想向大家“獻曝”“獻芹”,為了避免“衆哂而怨之”的結果,讓我先把讀詩的好處稍作介紹。
首先,詩歌能感動讀者、安慰讀者。漢人何休認為,詩歌緣起于“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南朝的锺嵘更具體地指出:“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既然詩歌的核心内蘊是“感蕩心靈”的感情,它就必然具有感蕩讀者心靈的強大功能。宋人嚴羽讀《離騷》,“歌之抑揚,涕淚滿襟”。清人盧世 讀杜詩,“肝腸如火,涕淚橫流”。古人如此,今人何必不然?更令人欣慰的是,正如韓愈所說:“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真正的好詩都是抒發胸中牢騷的不平之鳴,自古以來,由“歡愉之辭”組成的好詩寥若晨星。既然讀詩的最高境界是讀者與詩人之間達成心靈上的共鳴,那麼好詩最能感動的讀者理應是心多“愁思”的普通人。韓愈嘲笑富兒說:“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如今的富豪日夜沉溺在燈紅酒綠的豪華場所,也沒有什麼心情來讀詩。隻有我輩平頭百姓才是最合格的讀詩之人,我們才會在月白風清的良夜,對着一盞青燈攤開詩卷。讀詩是我們的專利,不能輕易放棄。
其次,讀詩是最易于操作的行為。古詩的篇幅都很短,詩選大多是薄薄的小冊子,很少有豪華包裝的大部頭。這有兩個好處:一是價格低廉,無須太大的财力即能購置。二是攜帶友善,無論出差還是旅遊,在行囊中放進一冊詩集不會增加多少重量。詩選中的作品都是互相獨立的,它們颠倒次序也沒有關系,每次讀多少首,從哪裡開始,都可以随心所欲。我有時用詩選下酒,随意翻到一頁,便從那兒開始讀。一不小心把書合上了,也不必費心尋找剛才讀到的地方,隻管任意翻開一頁就行了。讀完一首,不妨眯起眼睛回味一番,就像嘴裡抿了一口好酒一樣,那真是别有滋味。一旦你熟讀成誦,能背個幾百首,那就等于在腹中貯存了一冊詩選,即使在燈光昏暗、人聲嘈雜的火車上,你都可以繼續讀詩。這種唾手可得的精神享受,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既然讀詩有這麼多好處,我便要放心地向大家“獻曝”“獻芹”了。收入本書的四十篇詩話,是我多年來讀詩的感想,它們沒有什麼高深的意思,也沒有什麼新穎的觀點,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希望它們能在同樣愛好讀詩的朋友那兒得到共鳴,也希望它們能在暫時還沒有這種愛好的讀者那兒起到推薦古詩的作用。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古典詩歌是所有說漢語、寫漢字的人們的共同财富,大家千萬不要放棄對這份珍貴遺産的繼承權。
2005 年8 月11 日于南京大學南秀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