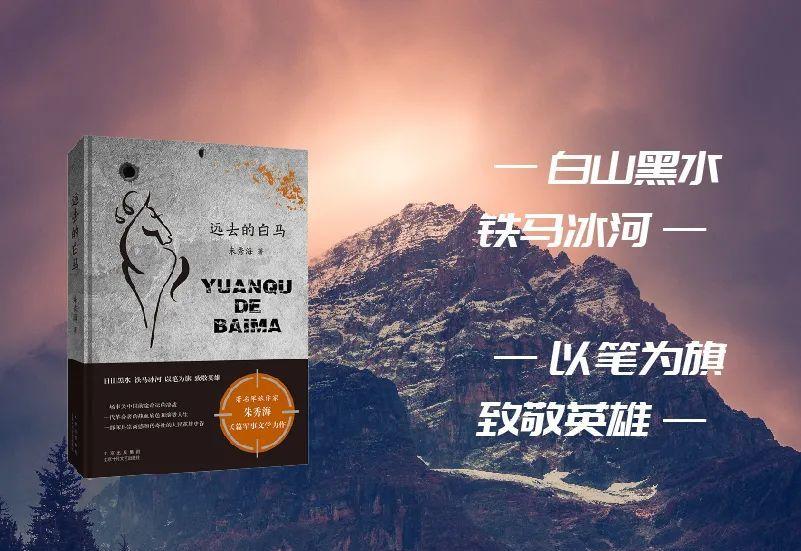
我在上川藏線的第三天收到朱秀海的短信。當時車剛到折多山垭口,海拔高度4380米,下車走幾步就要大喘氣,嘴唇也有些發紫。那種情況下,我實在是無法回信,直到下山到了新都橋才把他的資訊重看一遍,原來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召開朱秀海長篇小說《遠去的白馬》座談會的通知,因當時無法确定返京時間,我隻給朱秀海回了一個有關行程的信。
自此以後,《遠去的白馬》就好像一直和我如影随形。車在高原崎岖蜿蜒的山路上馳騁,不時有一群群黑色的牦牛從窗前掠過,我的眼前卻總是幻覺出有一匹白色的駿馬與我的車并駕齊驅,現實與曆史就這樣不停地在時空中交錯前行。當朱秀海筆下的人物再次與我相遇時,最打動我的還是秀英大姐這個傳奇女英雄,有血有肉、敢愛敢恨、剛柔并濟,不落概念化的俗套,個性鮮明、思維缜密、内心強大,一生都是扣人心弦的故事。當初閱讀就看得我潸然淚下,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動不已,這确實是一個非常獨特又非常豐滿的人物,即使放在“紅色題材”作品大量湧現的今天來看也是鳳毛麟角實屬不易。
多少年了,表現革命戰争的文學無數,但又能看到幾位“大姐”的形象堪稱藝術典型而難以忘懷?或有哪一部鴻篇巨制能把一個“大姐”的滄桑歲月貫穿始終,把人物的悲歡離合寫得蕩氣回腸。很遺憾,我所讀過的像“大姐”這樣的人物,即使有也是綠葉襯紅花,筆墨不多、内涵不深、分量也輕,不能給人打下烙印。默默無聞的确是“大姐”們可貴的品質和鮮明的特征,但讓這些中國革命的“無名英雄”在我們作品中也一直“默默無聞”,就不能不說是革命戰争文學創作的不足或缺失了。可能我的閱讀角度與别人不太一樣,他們大多看到寫活了一位傳統的戰鬥英雄,而我更欣賞這部作品寫活了“大姐”這個人物。在我看來,“大姐”是一個看似普通卻與衆不同的人。這就是被革命戰争造就出來的一個極特殊的英雄群體的典型形象。她們吃過苦、遭過罪,多數教育程度低,但有智慧,有倔勁和韌性,辦事幹巴利落,能夠快刀斬亂麻。她們的年齡、軍齡或黨齡相對長,比連排幹部甚至營團上司還要長,也沒有顯赫的職務,但覺悟高、接地氣,說個啥大家都愛聽。她們來自不同家庭,都有傳統美德,還有一些叛逆,屬于那種不受舊禮教束縛的女性。她們待人厚道,尤其對自己的同志和戰友傾其所愛,表現出女性的細膩和慈母般的感情。她們不自私,能為别人着想,有苦果自己吞,有眼淚往肚子裡流,遇到事兒敢站出來頂上去。差不多具備了這些“硬體”,人們就會情不自禁地叫她大姐了,那些看似很了不起的官職、頭銜一類的東西就會被人悄悄收起來。一聲聲親切的稱謂,被叫作大姐的人無形中就有了感召力和凝聚力,成為這支隊伍中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文學史一再證明,未必不是英雄的文學形象就不傳世,中外文學名著中的經典形象什麼種類都有,重要的是源于生活又被作家賦予了鮮活的生命,有高尚的心靈還能夠牽動讀者的神經。最神奇的是作者賦予“大姐”相當貼切的語言體系——膠東婦女就是這樣說話,爽快、風趣、犀利,好話歪說正話反說,各種形容比喻,語言的生活化、鄉土風透着豐厚的文化底蘊。或者說鄉而不土也不隻展現在秀英大姐身上,同樣展現在其他人物身上,包括故事的整個叙述過程,即語言與内容的渾然一體。朱秀海說“真實是創作者最強大的武器”,這話沒有錯,但我以為,有了對真實曆史的了解,不一定會有真正的感動和創作的熱情,即使有了這種感動和熱情,也不一定就能寫出有真情、動人心的作品來。這好比老話裡說的,擁有好食材也不是哪個大廚都能做出好飯菜。“大姐”本是虛構的人物,雖說也有原型,但作者沒有拘泥于某一個曆史人物,而是依據他對很多革命大姐的深入了解和認識,再經過十幾年的沉澱提煉,終使她們成了秀英大姐這個典型人物,并且把她寫得如此真實傳神。這對于沒有那個年代戰争體驗的作家來說,真的是難能可貴。我之是以會有這種感慨,是因為看到不少的作品,明明是一個尚好的題材,卻沒有講出好的故事來,讓讀者味同嚼蠟。明明是依據真實的事件,卻有不少生編硬造的痕迹,讓讀者心理逆反。明明是一個崇高的人物,卻幹巴巴地概念化,讓讀者無動于衷。《遠去的白馬》則完全不同,把枯燥的、衆人皆知的有名的無名的多次真實戰役,從點到面、從物到人,無論是一門炮、一袋糧、一駕馬車、一台交換機,還是一處陣地、一截壕溝、一次任務、一場戰役,大到情節小至細節,化繁為簡詳略得當,有精雕細鑿、有粗犷豪放,似層巒疊嶂起伏有序,真假虛實無痕銜接,很多場面有身臨其境之感,很多人物能叫讀者看了怦然心動,讓我這個很挑剔的讀者不得不承認《遠去的白馬》是近年來少見的一部好書。
寫到這裡,我又想起在川藏線過雀兒山的情景。那天從上午開始就下起了鵝毛大雪,被稱為“川藏第一險、川藏第一高”的雀兒山早已是白雪皚皚,地處隧道口的川藏公路十八軍紀念廣場也是銀裝素裹,我們一行來到“築路英雄”張福林烈士塑像前敬獻哈達。這位來自河南扶溝縣的農家子弟先後榮立一等功兩次、二等功兩次、三等功三次,犧牲時年僅26歲。他的母親也早在他犧牲前4年為掩護我黨地下組織轉移壯烈犧牲。蓦然間一種悲壯和崇高感襲上心頭,類似這樣的英雄母子,在那個年代的革命隊伍中并不鮮見。他們本是生于窮鄉僻壤的農民,懷着對革命樸素和真誠的了解,投身于推翻舊社會、建設新中國的偉大戰鬥,成了中華民族曆來歌頌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英雄豪傑。伫立在風雪中,突然有一句話從心裡湧出來:“他們的事迹和精神值得我們一再回眸、鄭重記取。”這句話是朱秀海剛從步兵師調到飛彈部隊以後對我說的,多少年過去了,我一直都沒有忘記。當時見面,本想聽朱秀海說初來乍到的感受,他卻說起自己的老部隊、老師長興奮不已。聽着聽着我就被朱秀海熾熱的情感打動了,讓我覺出這支光榮之旅的紅色基因已經在他的血管裡流淌。我和朱秀海還就他的老師長傳奇的人生進行了深入交流,他最後說了一句,我要把他們的故事寫下來,其原因不但在于他們當年的浴血奮戰、英勇犧牲換來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在于他們的理想、他們的信仰、他們毅然堅守并為之奮鬥終生的價值,和我們今天的時代血肉相連。
現在想來,朱秀海與老部隊、老師長那種割舍不下的情結,已進入到對革命曆史、戰鬥精神、氣節操守和光榮傳統的一種敬畏,這種從感性認識到理性思考的轉變,表明他在那個時候已經開始醞釀如何用文學來描繪這段革命曆史和這個英雄群體了,盡管還是初步的、表淺的,更談不上系統性和典型性,但至少向着他說的“一再回眸鄭重記取”的承諾又邁進了一步。再後來,朱秀海被點名叫去為老部隊的老師長寫傳記。當我倆聊起這個事兒,他說難度大,我說總比寫小說容易吧!他說要比寫小說耗時間和精力,我再說肯定要比你寫小說收獲大。理由很簡單,老師長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座含金量很高的富礦,不是誰都能有機會接近他,更不是誰都能有資格有條件去開釆這座富礦,隻要帶着感情去,甘願坐得冷闆凳,你的爐子裡肯定就能煉出金子來。轉眼十幾年過去了,當《遠去的白馬》問世後,朱秀海深有感觸地說,這些人物及其故事在他心裡埋藏了多久,壓抑了多久,等到寫作時,他們像隊伍一樣沖鋒、像江河一樣奔湧的氣勢和力量就有多強,終于讓他在花甲之年寫出了《遠去的白馬》,幾乎用了自己近半個世紀軍旅人生的積累蓄備。其價值當然就不僅僅是這一部作品,而是要讓英雄之歌、道德之歌和革命者的理想之歌,在當代軍事文學乃至革命戰争文學中久久回響。
我對朱秀海說,你要感恩“老師長”,因為《遠去的白馬》是源于他也就是“千秋”這個人物而最終成書。朱秀海回答:“我就是在為漸漸凋零的老英雄寫一部史,寫一首詩。”但在一些人看來,“千秋”僅是一個“配角”,朱秀海說,“千秋”在整個故事中是“一雙眼睛”。也有朋友認為,“千秋”這個人物比較平面,甚至是個影子。知道的是因為朱秀海寫過“千秋”的傳記,他的視角是躲不開的,而且畢竟真有其人不宜過多發揮想象力。但更多不認識朱秀海的讀者就會感覺故事一講到“千秋”就欠些火候。還有的朋友覺得作品安排“千秋”與秀英大姐始終不離不棄,但并沒有真正命運上的糾葛,就算他也有一匹大姐心中的白馬,那也僅是柏拉圖式的。但我不這麼看,相反認為朱秀海用主要的筆墨描繪“大姐”的形象,是作者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遠去的白馬》最大的成功。一方面因為作者對“大姐”和“千秋”的關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顯示出曆史的眼光和思想的穿透力;另一方面因為作者釆用類似現代中國畫縱筆豪放的潑彩,讓畫幅神形兼備氣韻不凡,正是思想與藝術的相輔相成由此及彼,才把“大姐”寬廣敞亮磊落的性格表現得如此酣暢淋漓。從“大姐”和“千秋”兩個人物形象中所顯示出來的不凡品格和藝術張力,對于整個革命戰争文學創作都有着重要的啟迪意義。具體說來,就是改變了以往革命戰争文學中那種傳統的“大姐”依附于“千秋”的模式,或者說改變了“大姐”隻能給“千秋”當配角的公式,讓我們看到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大姐”一直是“千秋”的力量之源;還讓我們看到在衣錦還鄉的生活中,“大姐”更是激勵鞭策“千秋”不忘初心的道德導師,正是從這兩個人物攜手走來密不可分的心路曆程中,揭示出了力量在人民之中,英雄也在人民之中的深刻内涵。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文藝的人民性不是概念說教,也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的集合,每個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都有内心的沖突和憂傷。我的家人在讀了《遠去的白馬》後有一個很實在的評價,前半部分打江山出生入死,愛恨交織,悲歡離合,好看;後半部分和平年代功過難分,英雄氣短,更見人心,深刻。這幾句大白話,或許能夠代表很多人閱讀《遠去的白馬》的真實感受,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這部作品對人的個體性價值的凸顯,對“人民”這個概念認知的深化,還有對書寫“革命者”的情感、價值和訴求的内在要求的藝術呈現。聽說朱秀海正在考慮要把小說改編成電視劇,我有一個設想,假如,前半部分的戰鬥過程适當壓縮,後半部分人心善惡的沖突适度展開,會不會讓“大姐”和“千秋”的故事更厚重更有戲劇性呢?或者在電視劇裡加強一下後半部分的故事?這對于朱秀海這個拿了無數編劇獎的金牌編劇來說,應該不是什麼問題吧,我對此抱有充分的信心和期待。
相關圖書
《遠去的白馬》
朱秀海/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21年2月出版
《遠去的白馬》是一部有分量、有思考的軍事文學作品。著名軍旅作家朱秀海在采訪多位親曆過解放戰争的幸存者後,收集了豐富的創作素材,以一匹馳騁沙場的白馬為引子,拉開了長篇小說《遠去的白馬》的帷幕。
小說主人公趙秀英,在抗日戰争期間就曾多次組織村民支前,帶領全村民工隊配合八路軍作戰。由于混亂中的一個誤會,趙秀英和她帶領的支前隊來到東北解放戰争的戰場上。背井離鄉、思念幼兒之苦沒有動搖這位共産黨員的心,她充分發揮了自己的組織才能和做群衆工作的經驗,組織打糧隊幫助三十七團度過缺衣少食的艱苦歲月,數次救全團于饑困。在戰場上,她冒着槍林彈雨從前線搶運傷兵,在敵軍的轟炸中用血肉之軀架起戰場通訊的生死線。解放戰争勝利後,她繼續堅守着共産黨人的使命,為一方水土、一方百姓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本書根植于真實的曆史故事,借助豐厚的曆史史實,以事關中國前途命運的決戰——解放戰争為背景,以清醒客觀的文學立場審視和書寫曆史的複雜與真實、人性的善良與崇高,對戰争場面、戰場情節與細節的書寫,對衆多人物的情感與命運的描繪,均掌控有度,拿捏準确。在曆史與現實的兩個時空中縱橫捭阖,以詩性的筆調和詠歎的激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無私無畏、信念堅定、生動飽滿的共産黨人形象,震撼人心,感人肺腑。
★
★ ★ ★
圖檔來源于網絡
編輯:徐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