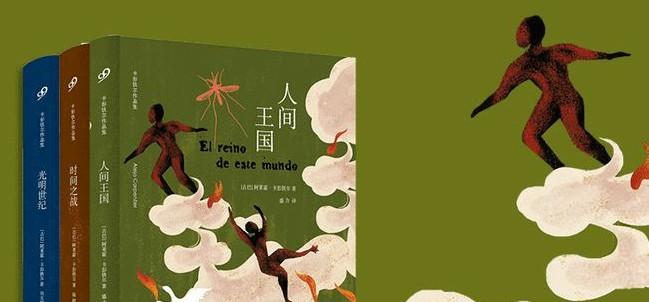
(卡彭鐵爾作品集 網絡圖檔)
侯健/文
1816年,一部名喚《癞皮鹦鹉》的小說在墨西哥出版,這部作品被許多人認為是真正意義上在拉丁美洲土地上出現的第一部小說,自此之後,拉丁美洲的小說家們就不斷在探索和定義拉美小說的概念。這種嘗試并非隻存在于文學界,拉丁美洲人定義自身身份的努力也在同時進行着,其中墨西哥哲學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1925年提出的“宇宙種族”理念頗有代表性:“将要出現的是具有決定性的種族、合成的種族,換句話說,完整的種族,它由所有民族的才智和血統造就,是以更有可能具備真正的兄弟情誼和世界性目光”,這種籠罩着樂觀主義色彩的理念“實質上是一個掩蓋了深層次沖突的神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在拉丁美洲,無論是文學界還是思想界,這種搖擺于夢想與現實之間的探索在《癞皮鹦鹉》問世後的一百多年間不斷上演,卻始終未有答案。
仿效西班牙流浪漢小說而作的《癞皮鹦鹉》可能是19世紀拉美小說家們最早也是最後一次對宗主國文學的模仿和緻敬,在此之後,對西班牙的仇視和抵觸情緒也在小說界不斷蔓延。進入20世紀後,拉美小說的發展似鐘擺一般擺到了另一個極端,小說家們醉心于描寫大地、山川、河流、雨林、土著,仿佛不寫這些就算不得真正的來自拉美的小說家。《旋渦》《堂娜芭芭拉》《青銅的種族》《廣漠的世界》等一批大地主義小說、土著主義小說就在此時問世,可這些小說逐漸陷入了套路化的死胡同,甚至成為了宣教、鼓動政治鬥争的工具。模仿他者,還是強調自身?這成了一個問題。
出生于1914年的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的首部小說《埃古-揚巴-奧》(1933)盡管聚焦黑人文化,卻似也可歸入土著主義小說之列,但卡彭鐵爾并未在鐘擺的這一端停留太久,多年之後,他甚至拒絕承認自己的這部小說處女作,因為他認定它并不成熟,巴爾加斯·略薩用四個字評價了卡彭鐵爾的這一态度:“極度明智”。卡彭鐵爾是有可能走向鐘擺的另一極端的:1923年,卡彭鐵爾與同處巴黎的米·安·阿斯圖裡亞斯一道加入了布勒東的超現實主義陣營,還攜手創辦了第一份西班牙語超現實主義刊物《磁石》,似乎“否定父輩,回歸祖輩”的魔咒就要再現,這兩位此後成為拉美小說史上響當當人物的作家就要再次走上模仿學習他者的老路上了,然而此時二人不約而同地停下了腳步,朝着美洲的方向回望過去。
卡彭鐵爾後來表示,他當時發現自己不會給超現實主義運動增添光彩,他産生了反叛情緒,生出了表現美洲大陸的強烈願望。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種族”理念雖說更趨近于夢想,但其産生的根基卻是真實存在的:白人、黑人、黃種人、印第安人、混血種人……拉美是一片混血的大陸,拉美文化是多元的文化,這是拉美小說家們的作品中未曾窮盡的東西。超現實主義成為了一種反作用力,它幫助卡彭鐵爾發現了屬于美洲大陸的“神奇現實”:那些在歐洲人眼中處處透着魔幻神奇色彩的東西,卻是美洲人習以為常的,換句話說,美洲現實本身就是“神奇的”“魔幻的”。
這種反思的成果就是1949年出版的《人間王國》。在這部小說裡,神話與曆史交織,現實與虛構交織,人間世界與神鬼世界交織,“神奇”元素随處可見:大主教的幽靈現身審判暴君克裡斯托夫,麥克康達爾能變化成鬣蜥、蝴蝶、鲣鳥、山羊、蜈蚣,蒂·諾埃爾則能變化成胡蜂、螞蟻、驢、鵝等動物,長廊兩旁的人形雕塑似乎有了生命、開始活動……
神奇有了,現實何在?不妨來看看反抗殖民的黑人領袖麥克康達爾被處火刑的場景:“麥克康達爾被捆在柱子上。劊子手用鉗子夾起炭火。總督用前一夜對着鏡子反複練習過的姿态抽出利劍,下令執行判決。火苗升騰,朝獨臂人身上舔去,燒灼着他的腿。這時,麥克康達爾……用嗥叫般的聲音念起奇怪的咒語,身軀猛地向前一傾。捆在身上的繩子落到了地上,黑人的身體騰空而起,在一些人的頭上飛過……那天下午,奴隸們一路笑着回到各自的莊園。麥克康達爾履行了諾言,永久地留在了人間王國。白人們又一次被另一個世界的至高無上的神靈所嘲弄。晚上,頭戴睡帽的勒諾芒·德梅齊老爺向他那位虔誠的妻子大發議論,說什麼黑人目睹同伴受刑而無動于衷。他還從這件事中引出一些關于人種差别的帶哲理性的結論。”
黑人果真愚昧冷漠嗎?這段文字實際上恰恰反映出了西方人對美洲“神奇現實”的漠視和無知。因為印第安文化傳統本就相信萬物有靈,人鬼世界是相同的,其間并無鴻溝,而且印第安人的傳統巫術也有“變化”之法。在對此深信不疑的黑奴眼中,麥克康達爾變化飛升是真實的,而哪怕他真的死去了,他也絕不會離開這人間王國。對他們來說,這就是現實。
從首批殖民者來到美洲大陸開始,這種漠視和無知就在逐漸蔓延,甚至引發了拉美文化和文學史上持續不斷的對“文明與野蠻”話題的讨論。殖民者看到印第安人用活人祭祀,無比血腥恐怖,就認定這是殘忍野蠻的表現,他們此後“以暴制暴”的行徑仿佛也是以獲得了倫理支撐。上文提及的阿斯圖裡亞斯在法國遇到了被認為是美洲文化基石的瑪雅聖書《波波爾·烏》,該書記載的創世神話為我們了解印第安人的行為提供了可能。我們通過該書得知,在印第安人的信仰中,人之是以成為世間主宰隻不過因為他們有贊美創世神并為之獻祭的能力,一旦他們停止了這種活動,便會像先于人類被創造出的其他動物一樣受到神的嚴厲懲罰。是以,印第安人的活人獻祭是他們的信仰的展現,這也是美洲的神奇現實。
那麼兼具神奇和現實的《人間王國》,或者說卡彭鐵爾的全部小說作品,如果隻是立足于展現美洲特有事物的話,它與上文提到的大地主義小說、土著主義小說又有什麼差別呢?二者的差異主要展現在寫作技巧層面。在前人的作品中,故事中的人物和環境大多是單純為主題服務的,為了表現沖突關系,土著主義小說中的印第安人大多善良、老實、本分,白人則暴虐不仁,大地主義小說中的環境要麼是塑造人物性格的背景(如《堂塞孔多·松布拉》中的潘帕斯草原與高喬人),要麼是某種刻闆特點的代名詞(如《旋渦》中最終吞噬掉主人公們的可怕叢林)。比起這些作家和作品來,卡彭鐵爾更進一步的地方就在于通過精心設計,使小說的主題與技巧達到了完美的契合。試看麥克康達爾下毒的段落:“毒物在北部平原擴散,侵襲牧場和牲畜圈。誰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在絆根草和苜蓿中擴散,又如何混進成捆的草料并落進牲口槽的……很快傳來了可怖的消息:毒物已進入宅院……總在伺機進攻的毒物潛伏在小桌上擱着的杯子裡,隐藏在湯鍋、藥瓶、面包、酒、水果和鹽裡。不祥的釘棺材聲随時可聞,送葬的隊伍随處可見……銀十字架在路上來來往往,綠色、黃色、無色的毒物在它的庇護下,繼續像蛇那樣爬行,或經由廚房的煙囪落下,或從緊閉着的門的縫隙裡鑽進屋内。”
卡彭鐵爾在這裡隐去了下毒人的活動,将毒物蔓延的動作發出者寫成了毒物本身,毒物仿佛有了生命一樣自由活動、自主攻擊,這正與上文提及的印第安人萬物有靈信仰相契合(同理,書中拉費裡埃城堡中的三門大炮被取名西庇阿、漢尼拔和哈米爾卡也就不隻是個幽默橋段了)。這種被巴爾加斯·略薩稱為“選擇性隐藏材料法”(即選擇性地隐藏某些重要資訊,在這裡被隐去的是操縱物體的人類)的寫法貫穿小說始終,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很難察覺到這一點,但是在讀完全書之後則會留下這種印象:小說中的動物植物、裝飾擺設無比“鮮活”,仿佛全都有了生命。值得注意的還有《波波爾·烏》中的某些句子:“當高山被創造之時,河流在山谷之間找到了它們的源頭”;“‘你們讓我們受了許多苦,還把我們的肉當食物吃,現在輪到我們吃你們了!’狗和其他動物說。石磨指責他們說……狗随聲附和道……甚至玉米煎鍋和飯鍋也開始斥責木頭人。”讀者在潛移默化中就接受了印第安文化最本質性的某些特點。
墨西哥文豪卡洛斯·富恩特斯曾指出寬泛意義上的“烏托邦”概念關注的是“某個不可能存在的空間”,但拉丁美洲的“烏托邦”卻隻能是一個時間概念,人們似乎始終在追憶着某段不可再現的黃金時代。在進行創作時,卡彭鐵爾也在“時間”因素上費盡了心思,如《溯源之旅》(又譯《回歸種子》)等時間因素占顯著地位的名篇自不必說,《人間王國》的時間設計也同樣别出心裁。在《人間王國》裡,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抑或是混血種人,一旦成為統治者,最終都會走向暴政,乍看上去,故事時間對應的是1751至1830年間海地曆史的真實時間,故事似乎是按照線性時間發展的。可再細想一番,會發現這種“壓迫-反抗-上台-暴政-壓迫”的首尾銜接模式反複出現,似乎沒有盡頭,故事又像是按照《百年孤獨》那樣的環形時間結構來設計的,似乎拉美曆史真的是在不斷畫着圓圈、回到原點。可是再細細一看,《人間王國》每個部分(從第一部到第四部)之間并沒有明顯的文字連接配接,而是跳躍發展的,甚至每部分前都似獨立小說一樣擁有不同的文前引言,卡彭鐵爾極緻細膩的巴洛克式描寫又使得每部分的故事發展時間極度緩慢,幾近停滞,仿佛是慢鏡頭掃過一幅又一幅畫面,這難道不正是拉美曆史的另一面嗎:原地踏步,仿佛從未前進。
在卡彭鐵爾之後,拉美“文學爆炸”的作家們之是以能夠轟動世界文壇,并非單純依靠凸顯拉美元素的異域主題或新穎技巧,而是二者的完美結合,這實際上正是卡彭鐵爾給拉美小說帶來的最重要啟示,卡彭鐵爾能被譽為“‘文學爆炸’的先驅”“大師中的大師”,原因正在于此。當下,随着經濟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年輕一代(或者年輕作家)體驗着看似超現實的生活(如加入超現實主義陣營的卡彭鐵爾一般),他們迫切需要的是不是回歸種子、溯歸本源呢?他們必須要做的又是不是去思考和發掘實作這種回歸的路徑呢?這正是卡彭鐵爾帶來的思考,也是卡彭鐵爾的文學作品永恒價值之所在。
(作者系西安外國語大學歐洲學院西班牙語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