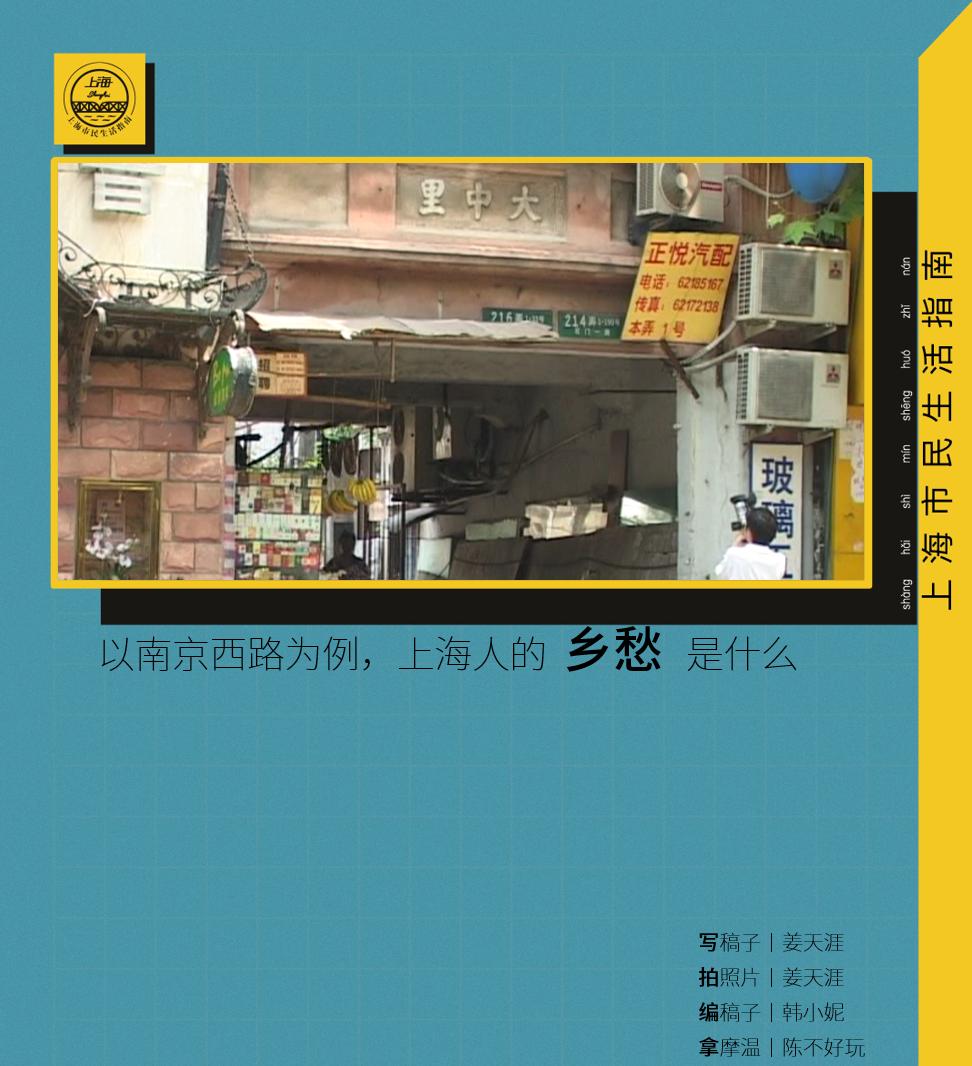
本文作者/姜天涯
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南京西路是一條時髦、高端的商業街。 是久光、芮歐、嘉裡中心、上海商城、梅泰恒、興業太古彙,和密布的小咖啡館。 不過30多年前,南京西路還不是這樣。彼時的南京西路兩側是大量住宅區,臨街有很多小店鋪。 在城市變化中,有些老店、老建築成功在原址待了近百年。但更多的店搬遷、消失,居民遷出。 面對過去幾十年迅速變化的上海,我們不免生出疑惑:仍在故土的上海人有鄉愁嗎? 我們試圖以南京西路為例,探讨上海人的鄉愁是什麼?
01
在NHK的紀錄片《上海夢》裡,我們看到了1994年前後的港彙恒隆、恒隆廣場和不夜城。
那是一個飛速發展、劇烈變化的時期。
上海在畫面裡看起來灰蒙蒙的。工地上舊裡弄拆了,新的高樓等待建起。一個新世紀商業城市的雛形,呼之欲出。
當我們分享這些畫面的時候,有讀者認出了自己曾經的住處:
“畫面裡最大的那個三層樓的建築,是我生活了10年的地方,居然我還能看到它。曾經是第七印染廠的職工宿舍。”
1994年左右的恒隆所在地,圖左的三層建築曾是第七印染廠的職工宿舍。 /NHK紀錄片《上海夢》截圖
我們找到了上述讀者匡文(化名)。若不是靠着紀錄片和1989年老地圖,她甚至還不知道自己居住過10年的地方現在是恒隆。
“那裡(高樓)太多了,以前房子拆遷造的是恒隆,還是梅龍鎮、中信泰富,我沒搞清楚過。都是奢侈品,我也不是他們的目标消費群。”
2001年,在西康路、南陽路、南京西路、陝西北路圍合起來的街區中,建起了恒隆。
如今的恒隆
而曾經,這裡有匡文的住所,就讀的西康路國小,父母機關的食堂和澡堂,還有沿着南京西路的十來家沿街商鋪。
1981年出生的匡文,曾在第七印染廠的宿舍裡,度過了人生前十年。
1985年4月,匡文(化名)在靜安公園。 /受訪者提供
在1989年出版的《上海市商用地圖冊》裡,彼時恒隆一邊的南陽路上還寫着“農副食品市場”。
這被匡文一眼指出:“啥農副産品市場,就是一個露天的菜場。”
沿着南京西路的十來家商鋪,她記得最清楚的是華僑彩影中心。
“老進階的,門口是一個櫥窗,擺了一台老大的機器,一頭膠卷塞進去,前頭照片一張張出來。”
“我經常去看的。都是人家吃酒水、公園合影的照片,印象蠻深的。”
“還有(潮聲)皮鞋廠我記得的,因為阿拉娘(我媽媽)經常去買皮鞋的。”
1989年出版的《上海市商用地圖冊》中匡文(化名)小時候的生活街區 (點選放大圖檔)
在這一段南京西路上,1988年開業的椰露酒吧,曾是那個年代上海的新事物。
1988年的《文彙報》對這家店的開業用了這樣的描述:
“酒吧,一度從辭典上消失的字……這年頭,它又重新在上海大都市湧現了。上酒吧,已是上海市民生活中的一種時尚。”
還隻是國小生的匡文當然沒有去過。她印象深刻,是因為在家裡能看到椰露的服務員,在樓下的弄堂裡教育訓練端盤子。
一街之隔的上海商城,匡文是看着它一點點建起來的。
現在的上海商城
“我讀國小辰光,已經開始造了。伊格地都圍起來的,裡向不曉得啥事體,外頭都在賣早飯啥的。一到落雨,都是爛泥地。”
當時的南京西路,遍布低矮的住宅樓房和沿街小商鋪,高樓是個不常見的事物,上海市民還有些新鮮。
“除了國際飯店,侬看不到像波特曼一樣像樣的高樓了。”
“埃辰光阿拉經常讨論的,假使格房子倒下來,阿拉肯定死了。但是沒想到,(後來)其它地方還會有噶許多高樓。”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城市新生事物,高樓開始取代20世紀初的建築。
現今的上海商城,曾是1906年建造的英商彙豐銀行大班住宅。這是一棟L形的歐洲古典主義建築,解放後是新華社上海分社。
上海商城的位置曾經是英商彙豐銀行大班住宅 /翻拍自《南京西路一百四十年》一書
而它對面的錦滄文華,1986年之前曾是有着70多年曆史的滄州飯店。
等匡文1991年搬離西康路的時候,錦滄文華也已建成。
1900年建造的滄州飯店,1986年拆除建成錦滄文華大酒店。 /翻拍自《南京西路一百四十年》
“有一年周潤發到上海來,交關(很多)人跑過去看,就是住在錦滄文華裡向。因為當時有《上海灘》,伊老紅的。”
1993年2月21日《新民晚報》對周潤發來滬進行了報道
匡文家連同往東的兩個街區,1997年建起了梅龍鎮廣場,2001年建起了中信泰富和恒隆廣場,被人稱為“梅泰恒”。
這三個商業體覆寫了原先的住宅區和沿街的小商鋪。
曾經,陝西北路口有着友聯點心店;中信泰富的位置上有着65年曆史的陝北菜場;梅龍鎮靠近江甯路的轉角處是“上海書店”。
随着城市發展,他們都有了新的定位。
1989年出版的《上海市商用地圖冊》,“梅泰恒”的位置上曾是陝北菜場、上海書店等。 (點選放大圖檔)
如今,匡文也時常經過南京西路附近,不過不是去商場,而是在銅仁路、南陽路這樣的後街穿梭。
在這些小路上,還留有兒時的空間感,時常會引起她的回憶。
“西康路、南陽路口那個煙雜店,一直在格地。雖然名字一直變,現在變成小超市,反正還是煙雜店的形态嘛。”
02
匡文家隔着兩個街區的南彙路10弄15号,曾是易敏(化名)家所在的弄堂。
1973年出生的易敏,出生不久就搬到了弄堂裡的一個亭子間。
房子是她父親機關裡分的。一直到國小五年級之前,她都住在這裡。
這棟建築今天仍然還在,隻不過曾經一街之隔的低矮樓房,變成了梅龍鎮伊勢丹。
易敏有着異常快樂的童年,因為她居住過的這段南京西路,曾被稱為“兒童街”。
今天南京西路、茂名北路口的絲芙蘭,曾是“向陽兒童用品商店”。
向陽兒童世界商廈前身為向陽兒童用品商店,1966年開設于南京西路993号。 /翻拍自《南京西路一百四十年》
“我第一支自動鉛筆、第一個自動鉛筆盒,都在那邊買的。”
“向陽門口有一大塊空地,老早放跷跷闆、滑滑梯、秋千。一到放學,附近幼稚園、國小的小朋友都在那邊玩。玩好到對面兒童食品商店買吃的。”
兒童食品商店今天還在老位置,幾步之遙的少年兒童圖書館也是。
上海少年兒童圖書館依然在原處
對過的凱司令也沒有變,隻是當時曾叫過“凱歌食品店”。
“阿拉爸每天夜到(晚上)給我買一塊奶油蛋糕回來,然後一杯樂口福。”
再過兩個路口的王家沙,也在原地。
“阿拉爸專門叫我拿隻鋼宗镬子到王家沙去買雙檔。開葷呀,難闆(偶爾)吃趟好的。”
在易敏童年的認知裡,附近最高的建築是泰興大樓,很進階。她有個同學就住在裡面。
泰興大樓建于1933年
“有電梯的房子,當時很厲害的。同學爺爺是海軍上校,阿拉都不敢到他家裡去的,因為曉得伊拉屋裡有個司令。小朋友不是有個兒歌麼,叫‘湯司令到,馬桶蓋掀(上海話讀xiāo)~’。”
當我們一同走過這段南京西路時,除了1997年開業的梅龍鎮伊勢丹,她都感到親切。
“我噶大了,還是個路盲。但格塊沒啥變化,我小辰光的店還都在,我就覺得老熟悉的。”
事實上,從南彙路到石門一路的南京西路段,幾乎保留了原先的建築。
兒童食品商店、少兒圖書館、凱司令、泰興大樓、王家沙隔壁的同孚大樓、南京美發店所在的德義大樓,都還在。
王家沙隔壁造型奇特的同孚大樓也是老建築
梅龍鎮伊勢丹對面的南京西路也沒變:靜安别墅、梅龍鎮酒家、新鎮江酒家、花園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藍棠皮鞋都在原址幾十年,甚至上百年。
隻不過現在一溜進階手表店,原先是更為生活化的業态。新鎮江兩邊的Omega和寶珀,30年前分别為東風絨線店、飛躍鞋帽店。
還有位于南京西路863号、擁有90多年曆史的鴻翔百貨,2008年變成過英國零售商Marks & Spencer,而後又變成了GAP。
面對這段南京西路的變與不變,匡文和易敏有着完全不一樣的回憶路徑。
對易敏來說,每次路過這段她熟悉的南京西路,都會發個微信給老父親。“跟他講我又來老房子了。”
德義大樓建成于1930年
而匡文卻很難尋覓童年的蹤迹。
她感到非常可惜的是,沒能留下一張西康路國小的照片。她至今清晰地記得,那是一棟擁有落地門窗、木地闆、露天長廊、小尖頂的洋房式樣建築。
她國中的時候,曾想回去拍過,可惜膠卷曝光,沒有拍到。
1987年6月匡文在北京路第五幼稚園的畢業照,可惜沒能留下國小的照片 /受訪者提供
我們翻閱了很多資料,也沒有找到這棟建築留下的印記(歡迎讀者提供)。
隻有在部落格上,看到一張某屆學生的黑白畢業照,依稀能從背景中看到主教學樓的一隅。
30年過去了,南京西路還是那條南京西路,地理位置永遠不會變。隻是街道的風貌、建築的形式、曾經的鄰舍,發生了變化。
正對中信泰富的花園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建于1927年,海派女作家程乃珊曾居住于此。
對匡文來說,鄉愁已經很難從實物中尋找。匡文的鄉愁是她回憶裡“很多很多小事”,是在此地和某些人的往事。
“我媽媽已經去世了。我到那邊,就會回憶起那個時候,我跟媽媽相處是什麼樣,然後周圍的環境是什麼樣子的。”
“有時候也會回想起以前我跟我同學,在波特曼門前,把他們種的一串紅都一隻隻嗦掉。”
03
如果說匡文遺憾的是沒能留下一張西康路國小的照片,舒浩侖則非常有意識地留下了自己和南京西路周邊的回憶。
2002年,剛從美國回來過暑假的舒浩侖,聽奶奶說大中裡要拆遷了。
在美國學習電影的他,感覺到了一場巨變即将發生。他拿起攝影機,拍攝了一部講述大中裡的紀錄片,名為《鄉愁》。
紀錄片《鄉愁》中的大中裡,舉着錄影機的正是該片導演舒浩侖
舒浩侖出生在石門一路214弄的大中裡。這是舒家從解放前就開始居住的石庫門裡弄。
1935年,舒浩侖的奶奶跟随爺爺,從甯波鄉下到上海來謀生。爺爺在鳳陽路上的四明銀行找到了工作,用幾根金條從房東手裡頂下了大中裡3号。
最多的時候,舒家住了6口人。
現在太古彙位置上的大中裡,曾是舒家從1935年就開始住的弄堂。 /截自紀錄片《鄉愁》
在這部極富個人視角的紀錄片裡,舒浩侖自己也出鏡了。
他說,采用這個在紀錄片中不尋常的做法,是希望自己能和大中裡一起留下最後的影像記錄。
舒浩侖和奶奶在大中裡 /截自紀錄片《鄉愁》
片中,他提及了自己兒時在弄堂裡的同學、鄰居和生活。
曾經,他和小夥伴在弄堂裡打井水浸西瓜、抓蝌蚪、吃大餅、拷醬油,一起看居委會的16寸黑白電視。
“當時有這個感受,我可能是最後一次到大中裡來了,這個地方肯定要沒有了。果然是這麼回事。”——大中裡原址上,是現在的興業太古彙。
這個大體量的商業綜合體,北起南京西路,南至威海路,西到石門一路,東靠青海路,呈南北狹長型。
上世紀,該地塊曾由天樂坊、柏德裡、華盛裡、大中裡四個住宅裡弄和民立中學構成。
循着1989年的商業地圖,舒浩侖少年時代的回憶一一展現。
1989年《上海市商用地圖冊》上,紅圈是興業太古彙所占地塊的一部分,黃圈是一些現已消失或搬遷的商鋪場所。
“紅村點心店,老早印象最深就是熱天賣刨冰的地方,而且賣的是熟水冰。”
“一塊冰買回去,方的,放在鋼宗镬子裡,包進被子。”
“阿拉阿娘(奶奶)甯波人,伊專門做糖醋刨冰,拿螺絲刀加把榔頭,‘啪’敲開。再放糖、放醋。”
“綠楊邨,小辰光經常從伊隔壁的弄堂,穿到對過新華電影院。”
紅村和綠楊邨,都曾位于今天興業太古彙的位置上。
2014年,老字号綠楊邨歇業歇停5年後,開在了奉賢路、江甯路。
而前身是夏令配克(Olympic)影戲院的“新華電影院”,1994年拆除,現在是彙銀大廈。
威海路、石門一路口,曾經是靜安第一糧油店、石門路水果店。
上國中的時候,舒浩侖經常被家人派去買米。每逢新米來到糧店時,買米就得排很長的隊。
2002年,糧油店原址變成了四季酒店。“是以我有朋友說,四季酒店很旺嘛,底下有米呀。”
威海路、石門一路口的四季酒店,如今也成了過去式。
1986年,石門一路、南京西路口建起了一座S型天橋,也被稱作王家沙天橋,2001年拆除。
“阿拉小辰光經常走的。我記得小辰光學雷鋒,還專門去擦欄杆的灰。”
1986年建成的這座S型天橋 /翻拍自《南京西路一百四十年》
大中裡附近的幾條小馬路,過去曾有着完全不同的業态。
如今100米一家咖啡館的威海路,30年前是“汽車、機車配件一條街”。
吳江路在成為“小吃一條街”之前,是馬路菜場。
“老早阿拉阿娘經常在那裡買魚,早上三四點鐘拿着魚票,去排隊。否則侬買不到最新鮮、最大的(魚)。”
青海路曾經一度也是服裝市場。“就在馬路上,擺那種鐵皮做的攤頭。格辰光牛仔褲啥的,就在那裡買的。”
小時候,舒浩侖喜歡爬到石庫門的房頂上,乘風涼,聽評書。
大中裡的房頂 /截自紀錄片《鄉愁》
80年代,高樓還沒有那麼多,國慶可以在房頂上看到人民廣場的煙火,“沒有遮擋”。
當時從大中裡往人民廣場看,視野範圍内最高的是上海電視塔。
1974年建成啟用的上海電視塔(左)後改建為廣電大廈 /翻拍自《南京西路一百四十年》
“阿拉屋裡電視信号從來沒啥(不好),因為就在貼隔壁嘛”。電視塔後經拆除,改建了廣電大廈。
往南京西路東邊走,舒浩侖曾在人民廣場學騎腳踏車。過去弄堂裡的小孩管人民廣場叫“大道”,指代“人民大道”。
“那時候(大道)是長馬路,還是煤渣路,練腳踏車掼(摔)下去的辰光,膝蓋還紮傷過。”
1979年的南京西路(人民廣場段) /轉自天地圖www.tianditu.gov.cn (點選放大圖檔)
往西走,舒浩侖印象裡有上海書店、放學後去練國術的靜安區少體校。這兩處現在分别為梅龍鎮伊勢丹和中信泰富的一部分。
2002年拍攝《鄉愁》的時候,舒浩侖曾就讀的威海路第二國小還在。
等他4年後剪輯、補拍素材的時候,“威二”的地皮上,已經蓋出了中凱城市之光。
舒浩侖的奶奶一直居住到大中裡拆遷。而後興業太古彙建了很多年。
舒浩侖的奶奶(左一)和鄰居們搓麻将 /截自紀錄片《鄉愁》
偌大一個地塊,最後隻剩下了他母校民立中學的一棟建築。
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園洋房,在2009年整體朝東南平移了57米。——這也标志着大中裡地塊的正式動工。
2009年3月10日《新民晚報》對于民立中學移位工程的報道
04
紀錄片《鄉愁》的片尾伴随着《啊,朋友再見》的旋律,打出了字幕:
“此片僅獻給我的家人,淳樸而溫暖的大中裡,以及那個純真的80年代。”
舒浩侖并不希望拍攝一部他者視角的紀錄影片。在《鄉愁》拍攝之前,有國際選片人曾建議他這麼做,更迎合國際口味。
“我怎麼可能這麼拍?我曾經是其中的一員,我有感情在裡面,不可能從純人類學的角度去看他們。”
2008年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候說道。
大中裡對于舒浩侖來說,不單單是石庫門本身,而是個體回憶和人生經驗的承載。拍攝《鄉愁》,也是希望予回憶一個載體。
“人的青少年,特别是少年時代的一段生命在裡面,那段時間雖然不能完全懂,但是我覺得是人比較重要的一段生命在這裡。”
舒浩侖認為:“如果‘鄉’是個實體空間,‘愁’就是個時間(概念)。你很難說僅僅是對一個實體空間的懷念,時空是一體的。”
紀錄片完成時大中裡還未拆除,但舒浩侖站在家裡的曬台上,發現弄堂已被高樓團團圍住。 /截自紀錄片《鄉愁》
對于背井離鄉者來說,鄉愁是對原鄉的惆怅。
對于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來說,鄉愁或許有些不同。原鄉仍在,隻是時間模糊了過去的風貌,卻留下了永遠的少年回憶。
它屬于南京西路曾經的居民,也屬于每一個在上海遷往他處,而後看着自己原先的家成了城市發展一部分的人。
我們并非單純指向懷舊,城市自有其發展的步調,人的生活方式也會不斷朝前。
等到舒浩侖拍攝《鄉愁》的時候,他已經不再習慣拎馬桶了,劇組的從業人員都是去四季酒店上廁所的。
拍攝期間,舒浩侖曾登上四季酒店俯瞰大中裡。
酒店大堂經理對他說:“這樣的風景在上海也不多了,但外國客人就特别喜歡,甚至會要求下面有這樣風景的房間”。
從四季酒店俯瞰大中裡 /截自紀錄片《鄉愁》
這句話曾讓舒浩侖五味雜陳。但今天,當他走回石門一路,想要辨識大中裡的方位時,四季酒店成了他判斷方位的地标。
而去年四季酒店停業之後,人們開始懷念起了這家有18年曆史的酒店。
網友回憶四季酒店 /來自大衆點評使用者@st_dolly
你看,時間會重新塑造新一代鄉愁。
就像匡文帶兒子回西康路時會告訴他,這曾是媽媽住過的地方,小孩子并不以為然。
但是她覺得,兒子長大後也會擁有自己的鄉愁。
“就是他長大的各個地方。幼稚園住在闵行,房子比較大。然後到了國小,搬到閘北來了。還有天天‘逼’他彈琴,總歸也是回憶不可缺少的部分。”
也許,對于00後、10後來說,上海本來也就是現在的樣子。
參考資料:
1. 靜安年鑒編輯部,《南京西路一百四十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2003年3月。
2. 江迅,《醉人的“椰露”》,文彙報,1988年12月17日。
3. 馬仁武,《别有風味的友聯生煎饅頭》,文彙報,1981年9月19日。
4. 孫衛星,《生産自救的“小陝北”——市紅旗機關陝北菜場“保旗”記》,新民晚報,1993年10月2日。
5. 馮婧,《天橋上的風景好》,東方早報,2015年12月3日。
6. 俞康華,《上海崛起一批特色街》,解放日報,1990年12月7日。
7. 鄒娟,《78年綠楊邨重制老味道“淮揚三頭”》,東方早報,2014年9月13日。
8. 金姬,《上海百貨業“透支”過冬?》,新民周刊,2009年2月23日。
9. 《GAP旗艦店取代瑪莎百貨進駐南京西路863号 8月25日開業》,赢商網上海站,2017年8月15日。
10. 缪毅容、金定根,《吳江路休閑步行街開街》,解放日報,2000年7月14日。
11. 宋甯華,《靜安大中裡保護建築上午啟動移位工程,90歲民立中學老校舍今“開步走”》,新民晚報,2009年3月10日。
12. 徐琳玲,《舒浩侖:上海不是這樣的》,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6月11日。
- END -
寫稿子:姜天涯/ 拍照片:姜天涯/
編稿子:韓小妮/ 寫毛筆:劉 娴/
做圖檔:二 黑/
拿摩溫:陳不好玩/
部分圖檔來自網絡
版權所有,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請給我們留言,擷取内容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