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语研究所统计,德语翻译家、卡夫卡专家叶廷芳于2021年9月27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九岁时,叶廷芳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左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叶廷芳将卡夫卡、迪伦·马特等一批德国经典作家译入中国,被誉为"中国学中第一个翻译卡夫卡的人"。
《缪斯的追求》是叶廷芳的选集。这本书,顾名思义,包含了叶廷芳对文学、艺术、建筑等艺术之美的体验。正如叶廷芳在序言中所说,"我的生活是由这些缪斯姐妹支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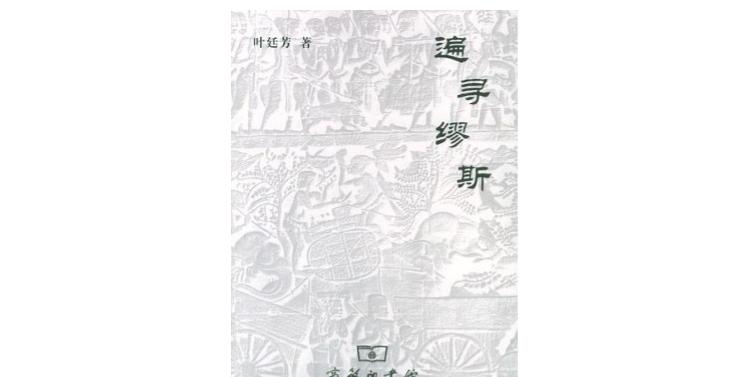
"缪斯的追求",叶廷芳著,商务出版社,2004年5月。
焦虑和缓解
焦虑是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条件,首先是现代知识分子或文化人。
如果欧洲人冲出中世纪的黑暗,发现新大陆,掀起工业革命,让人类看到自己的伟大和美丽,然后发出"宇宙的本质,万物灵长类"的赞美,那么现代人面对科技发展的加速和生产力的快速进步, 回首往事,却发现自己成了"地球的杀手,万物的天敌",进而成了"宇宙的害虫"。因此,在我们来不及悔改之前,大自然就开始了凶猛的报复。俊没有看到,从未听说过怪物"厄尔尼诺",完全奇怪的瘟疫"艾滋病"肆虐;我们曾经相信,世界永远越好越好,人类会越来越和平。谁能想到这种意想不到的警报会不断出现。难道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加了"原罪",使他永远不会在世上得到救赎吗?
虽然我们伪造以赎回对自然犯下的罪孽,但至少有一个目标要实现。现代人越来越多地发现的合理规律——悖论或圆圈——对我们来说尤其令人尴尬和困惑。不,当我们挣脱桎梏时,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不知道在自由的另一边,一个新的枷锁抓住了我们。你看:没有法治,我们将感到恐惧,并呼吁它的诞生;法治一旦建立和完善,就要小心谨慎,甚至要付钱给律师充当心理保镖,否则随时都有违法的风险;我们塑造上帝,希望它能祝福我们,一旦它被创造,我们就陷入了它的奴役;我们为牛顿和爱因斯坦欢呼,他们认为物理学可以改变世界,但物理学的发展导致了数以万计的核弹头的储存。它们足以一次又一次地摧毁地球。......这个自相矛盾的圈子曾经困扰着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他写了一系列杰作,像"被鞭打"一样震撼了文学世界。这个圈子也折磨着美国作家海勒,他花了八年时间完成了"黑色幽默"的杰作"22条规则"。这甚至让马克思主义剧作家布莱希特兴奋不已,他在那部智慧剧《四川好人》中让主人公说,我能行善,能作恶,我到底该如何生活?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Dylan Matt)从这种生活情境中获得了审美洞察力,并创作了一部又一部令人心碎的喜剧。
面对生存的艰辛或焦虑,最严肃的态度和最"傻帽"的是卡夫卡,他真正在进行现实生活经验的异化,并把写作作为这样一种经历的过程。下面这段话不是为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写的,他说:我们一直往前跑,越来越兴奋,越来越有活力,到最后看了一眼,其实并没有跑,还是站在原来的地方!这种荒谬和尴尬感积压在脑海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焦虑、急切地发泄出来,否则就会被"撕裂",而一旦能够宣泄出来,它就是"内在的伟大外在",是巨大的幸福和幸福。
迪伦·马特比卡夫卡聪明和"狡猾"得多,卡夫卡认为"现实以悖论的形式出现",但他把它变成了一个美学游戏,作为一个创造性的谜团:"写出没有谬误的剧本是不可能的。"难怪他的戏让大家都笑了起来,同时挂了两滴眼泪。如果他和卡夫卡通过写作感到高兴,那么后者是焦虑宣泄的乐趣,而他是"审美小说"的乐趣。
现在人们很少像卡夫卡那样做,昆德拉大概是唯一一个,他"人生经不起光"的警告没有经历过的皮肤疼痛是写出来的,无愧于老卡的故乡。不同的是,他毕竟是从布拉格出来的,也是从那个时代出来的,所以他的一生都是被鲜花赞美的,而宫中的喀什仍然承受着那种难以忍受的光芒,因为现在杨施赞美他,他可能不同意,否则他为什么要在死前"烧掉"他的全部作品呢?
如今的文化人在生存经历中,在现代哲学的启发下越来越焦虑,但大多愿意走迪伦·马特的路,即世界的无助简直是"沉默",在熙熙攘攘的封面上披着一个焦急的灵魂。作者不会搞美学游戏,只知道在美国王国自由驰骋,以平衡生活的失重。当感觉到一个声音在内心深处呐喊、呻吟时,只需走出去看一场画展,看一场芭蕾舞剧,听一首音乐......我称之为"生活压抑的审美平衡"。这种态度与周国平先生唱歌不谋而合,周先生说,在物质和金钱的重压下,选择"审美生活"是可取的!
您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以来一直颁发,与世纪完全相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而失败的七年,实际上共颁发了91个奖项。其中四个是双赢家,所以总共有95个幸运的赢家。但并非每个获奖者都是幸运的,比如法国的萨特,他声称"拒绝了资产阶级的所有荣誉",并拒绝接受奖品。有些人对此并不热心,更不用说,比如我们国家的鲁迅,当有人打算推荐它时,他声称:他不想成为"千鼎"作家,这样他就不再有活力了。当然,这样的例子是独一无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奖项被接受为一项巨大的荣誉。然而,文学奖的评选并不像科学奖那么简单,可以根据经验确定一项发明的结果,或者看它是否解决了多少人为之奋斗的难题。文学成就是不可预测的,文学奖项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有些作品不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和持久的审美魅力,反而能引起一定的轰动效果,所以名列榜,但很快成为明天的黄花;这样的作家往往对它视而不见,或者把它看作是"非文学"的异端邪说。难怪有人说"写当代史最难的事情,无论历史学家多么主观地追求正义,最终他必然要看错一些人,忽视一些人,或者指责一些人错了。而且,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是由一个国家创建的,即诺贝尔的故乡瑞典学者,她缺乏国际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局限。尽管年度颁奖典礼上的激烈辩论证明了她对正义的追求。但是,年度业绩的公布几乎总是伴随着不满的异议或怨恨。
这并不难理解。人们常说,文学是人类研究的,是艺术对情感、阅读或评判,不仅受时代、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政治、语言、风俗等因素的客观影响,还受每个人的气质、生活经历、知识背景等主观因素的影响。难怪,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没有悖论:她发现的天才几乎和她埋葬的天才一样多!因此,如果我们要从本世纪的世界作家画廊中选出前60名,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瑞典学院几乎有一半被遗漏了!奥地利人口只有700万,有六个人:小说家卡夫卡(1883-1924),诗人里尔克(1875-1926),小说家穆齐尔(1880-1942),诗人和戏剧家霍夫曼斯塔尔(1 874-1929),小说家布罗赫(1886-1951),诗人泽兰(1920-1970),法国也有六个:小说家佐拉(1840-1902),小说家普鲁斯特(1871-1922),诗人瓦莱丽(1871-1945),诗人和剧作家克洛(1868-1955), 诗人布列塔尼(1896-1966),小说家马洛(1901-19 76);五个英国人:小说家哈代(1840-1928),小说家劳伦斯(1885-1930),小说家康拉德(1857-1924),小说家伍尔夫(1882-1945),诗人奥登(1907-1973);至少有两个俄罗斯人: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和小说家和剧作家高尔基(1868-1936);和美国两位:诗人庞德(1885-1885-1885-)1972)和诗人兼小说家纳博科夫(1899-1977); ;一个挪威人:剧作家易卜生(1826-1906);一个在西班牙:诗人和戏剧家洛尔现在(1898-1936);一个在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1902-1963);一个在日本:小说家三个Yukif(1925-1970);瑞士:瓦尔特(1878-1956)和迪伦·马特(1921-1990),弗里施(1911-1991)黎巴嫩:基贝隆(1883-1931)。中国拥有12亿人口,一直被称为文学强国,她应该至少有三到五个:鲁迅,老舍,沈从文,郭莫罗,毛墩。
从上面的名单中不难看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至少有三个问题:一是她对本世纪世界文学现代精神的理解麻木不仁,钧敏没有看到她"怀念"的上述作家,大多是现代精神的作家,或者说是"现代主义"作家, 不仅崛起在奥地利的相当一部分群体中没有得到她的认可,甚至连世界公认的三位"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都在她的视线之外!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是剧作家和小说家斯特林堡,在她自己的国家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某种偏见的结果。其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偏见也在意识形态上暴露出来,聚焦于布莱希特、高尔基、鲁迅的"疏漏"。特别是布莱希特,是本世纪西方艺术创新的一面旗帜,他的戏剧既是一个平民世界,也是"现代",而东西方世界都认可,其影响力还在不断上升,范围越来越大,没有理由将他排除在诺贝尔文学奖谱系之外。此外,第三世界的赢家显然很少,而且相差甚远。从近年来的选拔结果来看,瑞典学院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一些补救措施。
当然,瑞典科学院对上述指责也有辩护。应该说,有些理由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到卡夫卡和普鲁士三位"现代文学之父"在其中去世,他们的大部分作品或主要作品尚未出版,即使已经出版(如乔伊斯),也就不容易找到,因为现代人文精神和现代审美意识的普遍觉醒有一定时间, 我们不能要求诺贝尔奖评审团有这样的超前感。但她给出的一些作家没有获奖的理由并不令人信服,比如托尔斯泰没有得到奖励,因为他后来的小说已经转向了宣扬无政府状态的教育和宗教小册子,这与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想主义"不一致。这很难确定。众所周知,托尔斯泰之所以成为托尔斯泰,主要是因为他写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伟大作品,这是他作为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奖励应该是对他一生中主要表现的评估,还是应该是一次性的?当然,答案应该是前者。例如,左拉没有获胜,因为他的作品"对自然主义的不加提炼的愤世嫉俗";这些原因显然是牵强附会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感谢诺贝尔评审团的筛选,感谢她发现了许多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至少和失踪的作家一样多。尽管该名单必须在下个世纪或更长时间进行筛选,但据信,其中总会有一部分将永远存在。如果没有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就会忽略其中的一些!因此,我们需要诺贝尔文学奖的窗口,我们不会给她绝对的正义。
《西风路》,叶廷芳著,海天出版社,2016年9月。
书斋,我的精神家园
书籍对读者来说是禁食的,农田对农民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不是每个有学问的人都必须快一本书,但书快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定不能留下的东西。它是我工作的基础,也是我精神家园。它是我几十年辛勤工作的结晶,也是我远见、知识、兴趣奔腾的场所。
书斋,顾名思义,是藏书的地方,是用书的地方,书是其主要内容。我的收藏数量不是太多,没有百万,从来没有数过;但我非常重视它们。因为它们来之不易。特别是在我拿着补助金上学的日子里,每月三五元的零花钱已经够穷的了,但大部分都是用买书来消费的。下班后,拿到知名人士每月几十元的工资,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开心买几本书。遇到出国的机会,买书的欲望就更难遏制了,因为书的内容范围很广,装裱精美,以牺牲食物为代价来满足部分欲望。特别是在1991年,几乎没有任何用品被购买,用于购买德国乐器,总共超过100公斤,其中包括一些大型图画书。但在国外的书店里,没有那么多的开心,也没说不舒服,因为害羞在包里,对更多的书只能发痒在心里,看着"书"叹息。
买书很开心,但也常常让家人忧心忡忡,甚至吵架也很难过冬。直到现在,每次家里来客人面前,女主人真的无法躲在家里的寒冷,然后向书房抱怨:"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没什么不对,直到两年前,我的银行存折从未超过3000元!"即便是现在,人们看到我卧室那歪歪扭扭的大柜子还是不能幸免笑:这个人的书柜和大柜子,一个属于精神,一个属于材料,两者之间的对比是如此之大!
书也给我带来了长期的麻烦,因为它与人争夺空间,尤其是16年的家庭,一直住在一个房子里,大小相当于两张床,两个书架,一张写字台,哪里就有空间!作为最后的手段,必须在写字台上设置两层木板来放置书籍。然后只需将书架靠在写字台上的墙上!对于两间卧室,它只是在第一年或两年稍微宽松一点。但书房必须既是卧室又是客厅。而且书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每次买一本书,都要考虑旧的半天,哪本书应该拉出来放在床底?久而久之,书上堆积着所有的空白,到了一本书,经常翻找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虽然汗流浃背,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两年前,单位终于为我补充了一间一居室,使我有条件腾出一个大房间,专门用于使用书籍。我装修房子,自己画设计,去大红门木厂定制六层2.7米高的硬木书柜(两层叠),"顶楼"充分利用空间;书柜每层高低,每层内外两层书,中间层高六厘米,再加一块文件板,这样书里面就有一部分书脊高于外层,拿书时要找厕所。但《一面墙》四个书柜中间的三层只有一层书,所以外层是空的,可以放一些工艺品等玩物。每次出门,无论在海内外,我都要带一两件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品回来,放在玻璃书柜里,不仅是为了增加艺术气息和异国风情,也是为了纪念价值。六个橱柜肯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于是我把角落阳台密封了大约六平方米,把已经淘汰的四个书架放到阳台上放一些小书,同时把原来的两个书柜搬到卧室,用写字台,放一些日常用的书。桌子上的书架上还放满了工具书。现在可以说,我的每一本书都已经"自得其足",不再摆脱翻找的罪孽、尘埃落定的风险。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愿望。当然,三年后,恐怕我又要开始担心了。
在内容方面,我的馆藏比较丰富:既有中文,也有德语,除了文学书籍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艺术、音乐、建筑甚至当地景区的信息,可谓是外交融合、图形丰富。每当我需要处理什么信息,依靠自己的书快速解决时,我都会感到非常高兴;现在,我尽量买书到高端的努力,尤其是单位图书馆不买书。例如,我看了《英国图书市场观点百科全书》,虽然它更贵,但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它。很快,看到大型国画画册《元四》、《明四》、《四僧》等刊物,不便宜,我也一口气抢回了。从国外购买的大量德国地图集,以及艺术史上的线索,也变得规模庞大。每个假期或晚上都很安静,相信手读书,味道好,真的是难得的舒适,很享受。
我的人生哲学是对审美人生的追求。为了增加书的丰富性和立体感,达到审美的"多样性"效果,我在书房中同时把音响和电视机结合放在书房里,让记忆符号和听觉、视觉印象融为一体,增加审美氛围的集中度。所以说我每天都在这本书里,相当于每一天都沉浸在一个美丽的王国里。尽管生活中有其他缺点或缺点,只要有这本书和我在一起,我就会感到快乐,甚至陶醉。
原作者|叶廷芳
摘录 |刘亚光
编辑|清子
该指南校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