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語研究所統計,德語翻譯家、卡夫卡專家葉廷芳于2021年9月27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5歲。九歲時,葉廷芳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左臂。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葉廷芳将卡夫卡、迪倫·馬特等一批德國經典作家譯入中國,被譽為"中國學中第一個翻譯卡夫卡的人"。
《缪斯的追求》是葉廷芳的選集。這本書,顧名思義,包含了葉廷芳對文學、藝術、建築等藝術之美的體驗。正如葉廷芳在序言中所說,"我的生活是由這些缪斯姐妹支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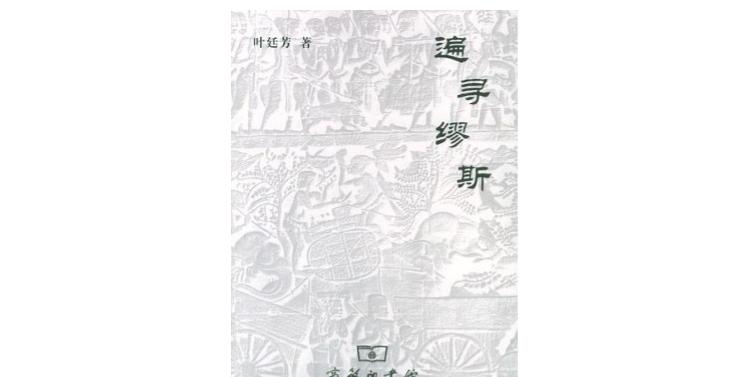
"缪斯的追求",葉廷芳著,商務出版社,2004年5月。
焦慮和緩解
焦慮是現代人的基本生活條件,首先是現代知識分子或文化人。
如果歐洲人沖出中世紀的黑暗,發現新大陸,掀起工業革命,讓人類看到自己的偉大和美麗,然後發出"宇宙的本質,萬物靈長類"的贊美,那麼現代人面對科技發展的加速和生産力的快速進步, 回首往事,卻發現自己成了"地球的殺手,萬物的天敵",進而成了"宇宙的害蟲"。是以,在我們來不及悔改之前,大自然就開始了兇猛的報複。俊沒有看到,從未聽說過怪物"厄爾尼諾",完全奇怪的瘟疫"艾滋病"肆虐;我們曾經相信,世界永遠越好越好,人類會越來越和平。誰能想到這種意想不到的警報會不斷出現。難道神在創造人的時候就加了"原罪",使他永遠不會在世上得到救贖嗎?
雖然我們僞造以贖回對自然犯下的罪孽,但至少有一個目标要實作。現代人越來越多地發現的合理規律——悖論或圓圈——對我們來說尤其令人尴尬和困惑。不,當我們掙脫桎梏時,我們以為我們已經自由了,我不知道在自由的另一邊,一個新的枷鎖抓住了我們。你看:沒有法治,我們将感到恐懼,并呼籲它的誕生;法治一旦建立和完善,就要小心謹慎,甚至要付錢給律師充當心理保镖,否則随時都有違法的風險;我們塑造上帝,希望它能祝福我們,一旦它被創造,我們就陷入了它的奴役;我們為牛頓和愛因斯坦歡呼,他們認為實體學可以改變世界,但實體學的發展導緻了數以萬計的核彈頭的儲存。它們足以一次又一次地摧毀地球。......這個自相沖突的圈子曾經困擾着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他寫了一系列傑作,像"被鞭打"一樣震撼了文學世界。這個圈子也折磨着美國作家海勒,他花了八年時間完成了"黑色幽默"的傑作"22條規則"。這甚至讓馬克思主義劇作家布萊希特興奮不已,他在那部智慧劇《四川好人》中讓主人公說,我能行善,能作惡,我到底該如何生活?瑞士劇作家迪倫·馬特(Dylan Matt)從這種生活情境中獲得了審美洞察力,并創作了一部又一部令人心碎的喜劇。
面對生存的艱辛或焦慮,最嚴肅的态度和最"傻帽"的是卡夫卡,他真正在進行現實生活經驗的異化,并把寫作作為這樣一種經曆的過程。下面這段話不是為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曆而寫的,他說:我們一直往前跑,越來越興奮,越來越有活力,到最後看了一眼,其實并沒有跑,還是站在原來的地方!這種荒謬和尴尬感積壓在腦海中,變成了一個"巨大的世界",焦慮、急切地發洩出來,否則就會被"撕裂",而一旦能夠宣洩出來,它就是"内在的偉大外在",是巨大的幸福和幸福。
迪倫·馬特比卡夫卡聰明和"狡猾"得多,卡夫卡認為"現實以悖論的形式出現",但他把它變成了一個美學遊戲,作為一個創造性的謎團:"寫出沒有謬誤的劇本是不可能的。"難怪他的戲讓大家都笑了起來,同時挂了兩滴眼淚。如果他和卡夫卡通過寫作感到高興,那麼後者是焦慮宣洩的樂趣,而他是"審美小說"的樂趣。
現在人們很少像卡夫卡那樣做,昆德拉大概是唯一一個,他"人生經不起光"的警告沒有經曆過的皮膚疼痛是寫出來的,無愧于老卡的故鄉。不同的是,他畢竟是從布拉格出來的,也是從那個時代出來的,是以他的一生都是被鮮花贊美的,而宮中的喀什仍然承受着那種難以忍受的光芒,因為現在楊施贊美他,他可能不同意,否則他為什麼要在死前"燒掉"他的全部作品呢?
如今的文化人在生存經曆中,在現代哲學的啟發下越來越焦慮,但大多願意走迪倫·馬特的路,即世界的無助簡直是"沉默",在熙熙攘攘的封面上披着一個焦急的靈魂。作者不會搞美學遊戲,隻知道在美國王國自由馳騁,以平衡生活的失重。當感覺到一個聲音在内心深處呐喊、呻吟時,隻需走出去看一場畫展,看一場芭蕾舞劇,聽一首音樂......我稱之為"生活壓抑的審美平衡"。這種态度與周國平先生唱歌不謀而合,周先生說,在物質和金錢的重壓下,選擇"審美生活"是可取的!
您如何看待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以來一直頒發,與世紀完全相同。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兩次世界大戰而失敗的七年,實際上共頒發了91個獎項。其中四個是雙赢家,是以總共有95個幸運的赢家。但并非每個獲獎者都是幸運的,比如法國的薩特,他聲稱"拒絕了資産階級的所有榮譽",并拒絕接受獎品。有些人對此并不熱心,更不用說,比如我們國家的魯迅,當有人打算推薦它時,他聲稱:他不想成為"千鼎"作家,這樣他就不再有活力了。當然,這樣的例子是獨一無二的。在大多數情況下,該獎項被接受為一項巨大的榮譽。然而,文學獎的評選并不像科學獎那麼簡單,可以根據經驗确定一項發明的結果,或者看它是否解決了多少人為之奮鬥的難題。文學成就是不可預測的,文學獎項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有些作品不具有深刻的時代内涵和持久的審美魅力,反而能引起一定的轟動效果,是以名列榜,但很快成為明天的黃花;這樣的作家往往對它視而不見,或者把它看作是"非文學"的異端邪說。難怪有人說"寫當代史最難的事情,無論曆史學家多麼主觀地追求正義,最終他必然要看錯一些人,忽視一些人,或者指責一些人錯了。而且,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是由一個國家建立的,即諾貝爾的故鄉瑞典學者,她缺乏國際性,這本身就是一個局限。盡管年度頒獎典禮上的激烈辯論證明了她對正義的追求。但是,年度業績的公布幾乎總是伴随着不滿的異議或怨恨。
這并不難了解。人們常說,文學是人類研究的,是藝術對情感、閱讀或評判,不僅受時代、民族、地區、曆史、文化、政治、語言、風俗等因素的客觀影響,還受每個人的氣質、生活經曆、知識背景等主觀因素的影響。難怪,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過程中沒有悖論:她發現的天才幾乎和她埋葬的天才一樣多!是以,如果我們要從本世紀的世界作家畫廊中選出前60名,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瑞典學院幾乎有一半被遺漏了!奧地利人口隻有700萬,有六個人:小說家卡夫卡(1883-1924),詩人裡爾克(1875-1926),小說家穆齊爾(1880-1942),詩人和戲劇家霍夫曼斯塔爾(1 874-1929),小說家布羅赫(1886-1951),詩人澤蘭(1920-1970),法國也有六個:小說家佐拉(1840-1902),小說家普魯斯特(1871-1922),詩人瓦萊麗(1871-1945),詩人和劇作家克洛(1868-1955), 詩人布列塔尼(1896-1966),小說家馬洛(1901-19 76);五個英國人:小說家哈代(1840-1928),小說家勞倫斯(1885-1930),小說家康拉德(1857-1924),小說家伍爾夫(1882-1945),詩人奧登(1907-1973);至少有兩個俄羅斯人: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和小說家和劇作家高爾基(1868-1936);和美國兩位:詩人龐德(1885-1885-1885-)1972)和詩人兼小說家納博科夫(1899-1977); ;一個挪威人:劇作家易蔔生(1826-1906);一個在西班牙:詩人和戲劇家洛爾現在(1898-1936);一個在土耳其:詩人希克梅特(1902-1963);一個在日本:小說家三個Yukif(1925-1970);瑞士:瓦爾特(1878-1956)和迪倫·馬特(1921-1990),弗裡施(1911-1991)黎巴嫩:基貝隆(1883-1931)。中國擁有12億人口,一直被稱為文學強國,她應該至少有三到五個:魯迅,老舍,沈從文,郭莫羅,毛墩。
從上面的名單中不難看出,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至少有三個問題:一是她對本世紀世界文學現代精神的了解麻木不仁,鈞敏沒有看到她"懷念"的上述作家,大多是現代精神的作家,或者說是"現代主義"作家, 不僅崛起在奧地利的相當一部分群體中沒有得到她的認可,甚至連世界公認的三位"現代文學之父"——卡夫卡、喬伊斯、普魯斯特都在她的視線之外!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是劇作家和小說家斯特林堡,在她自己的國家對世界文學産生了巨大影響,也視而不見!這不能不說是某種偏見的結果。其次,諾貝爾文學獎的這種偏見也在意識形态上暴露出來,聚焦于布萊希特、高爾基、魯迅的"疏漏"。特别是布萊希特,是本世紀西方藝術創新的一面旗幟,他的戲劇既是一個平民世界,也是"現代",而東西方世界都認可,其影響力還在不斷上升,範圍越來越大,沒有理由将他排除在諾貝爾文學獎譜系之外。此外,第三世界的赢家顯然很少,而且相差甚遠。從近年來的選拔結果來看,瑞典學院似乎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做出了一些補救措施。
當然,瑞典科學院對上述指責也有辯護。應該說,有些理由是有道理的,比如說到卡夫卡和普魯士三位"現代文學之父"在其中去世,他們的大部分作品或主要作品尚未出版,即使已經出版(如喬伊斯),也就不容易找到,因為現代人文精神和現代審美意識的普遍覺醒有一定時間, 我們不能要求諾貝爾獎評審團有這樣的超前感。但她給出的一些作家沒有獲獎的理由并不令人信服,比如托爾斯泰沒有得到獎勵,因為他後來的小說已經轉向了宣揚無政府狀态的教育和宗教小冊子,這與諾貝爾獎中提出的"理想主義"不一緻。這很難确定。衆所周知,托爾斯泰之是以成為托爾斯泰,主要是因為他寫了《戰争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複活》等偉大作品,這是他作為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獎勵應該是對他一生中主要表現的評估,還是應該是一次性的?當然,答案應該是前者。例如,左拉沒有獲勝,因為他的作品"對自然主義的不加提煉的憤世嫉俗";這些原因顯然是牽強附會的。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感謝諾貝爾評審團的篩選,感謝她發現了許多世界級的文學大師,至少和失蹤的作家一樣多。盡管該名單必須在下個世紀或更長時間進行篩選,但據信,其中總會有一部分将永遠存在。如果沒有諾貝爾文學獎,我們就會忽略其中的一些!是以,我們需要諾貝爾文學獎的視窗,我們不會給她絕對的正義。
《西風路》,葉廷芳著,海天出版社,2016年9月。
書齋,我的精神家園
書籍對讀者來說是禁食的,農田對農民來說也是如此。雖然不是每個有學問的人都必須快一本書,但書快對我來說,确實是一定不能留下的東西。它是我工作的基礎,也是我精神家園。它是我幾十年辛勤工作的結晶,也是我遠見、知識、興趣奔騰的場所。
書齋,顧名思義,是藏書的地方,是用書的地方,書是其主要内容。我的收藏數量不是太多,沒有百萬,從來沒有數過;但我非常重視它們。因為它們來之不易。特别是在我拿着補助金上學的日子裡,每月三五元的零花錢已經夠窮的了,但大部分都是用買書來消費的。下班後,拿到知名人士每月幾十元的工資,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書店,開心買幾本書。遇到出國的機會,買書的欲望就更難遏制了,因為書的内容範圍很廣,裝裱精美,以犧牲食物為代價來滿足部分欲望。特别是在1991年,幾乎沒有任何用品被購買,用于購買德國樂器,總共超過100公斤,其中包括一些大型圖畫書。但在國外的書店裡,沒有那麼多的開心,也沒說不舒服,因為害羞在包裡,對更多的書隻能發癢在心裡,看着"書"歎息。
買書很開心,但也常常讓家人憂心忡忡,甚至吵架也很難過冬。直到現在,每次家裡來客人面前,女主人真的無法躲在家裡的寒冷,然後向書房抱怨:"我們家什麼都沒有,隻有幾本書。"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沒什麼不對,直到兩年前,我的銀行存折從未超過3000元!"即便是現在,人們看到我卧室那歪歪扭扭的大櫃子還是不能幸免笑:這個人的書櫃和大櫃子,一個屬于精神,一個屬于材料,兩者之間的對比是如此之大!
書也給我帶來了長期的麻煩,因為它與人争奪空間,尤其是16年的家庭,一直住在一個房子裡,大小相當于兩張床,兩個書架,一張寫字台,哪裡就有空間!作為最後的手段,必須在寫字台上設定兩層木闆來放置書籍。然後隻需将書架靠在寫字台上的牆上!對于兩間卧室,它隻是在第一年或兩年稍微寬松一點。但書房必須既是卧室又是客廳。而且書的數量在不斷增加,每次買一本書,都要考慮舊的半天,哪本書應該拉出來放在床底?久而久之,書上堆積着所有的空白,到了一本書,經常翻找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雖然汗流浃背,卻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兩年前,機關終于為我補充了一間一房間,使我有條件騰出一個大房間,專門用于使用書籍。我裝修房子,自己畫設計,去大紅門木廠定制六層2.7米高的硬木書櫃(兩層疊),"頂樓"充分利用空間;書櫃每層高低,每層内外兩層書,中間層高六厘米,再加一塊檔案闆,這樣書裡面就有一部分書脊高于外層,拿書時要找廁所。但《一面牆》四個書櫃中間的三層隻有一層書,是以外層是空的,可以放一些工藝品等玩物。每次出門,無論在海内外,我都要帶一兩件具有地方特色的藝術品回來,放在玻璃書櫃裡,不僅是為了增加藝術氣息和異國風情,也是為了紀念價值。六個櫥櫃肯定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于是我把角落陽台密封了大約六平方米,把已經淘汰的四個書架放到陽台上放一些小書,同時把原來的兩個書櫃搬到卧室,用寫字台,放一些日常用的書。桌子上的書架上還放滿了工具書。現在可以說,我的每一本書都已經"自得其足",不再擺脫翻找的罪孽、塵埃落定的風險。這是我期待已久的願望。當然,三年後,恐怕我又要開始擔心了。
在内容方面,我的館藏比較豐富:既有中文,也有德語,除了文學書籍外,還有相當數量的藝術、音樂、建築甚至當地景區的資訊,可謂是外交融合、圖形豐富。每當我需要處理什麼資訊,依靠自己的書快速解決時,我都會感到非常高興;現在,我盡量買書到高端的努力,尤其是機關圖書館不買書。例如,我看了《英國圖書市場觀點百科全書》,雖然它更貴,但我毫不猶豫地買了它。很快,看到大型國畫畫冊《元四》、《明四》、《四僧》等刊物,不便宜,我也一口氣搶回了。從國外購買的大量德國地圖集,以及藝術史上的線索,也變得規模龐大。每個假期或晚上都很安靜,相信手讀書,味道好,真的是難得的舒适,很享受。
我的人生哲學是對審美人生的追求。為了增加書的豐富性和立體感,達到審美的"多樣性"效果,我在書房中同時把音響和電視機結合放在書房裡,讓記憶符号和聽覺、視覺印象融為一體,增加審美氛圍的集中度。是以說我每天都在這本書裡,相當于每一天都沉浸在一個美麗的王國裡。盡管生活中有其他缺點或缺點,隻要有這本書和我在一起,我就會感到快樂,甚至陶醉。
原作者|葉廷芳
摘錄 |劉亞光
編輯|清子
該指南校對|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