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請大家在閱讀之前,關注下小暖,一起探讨更多文化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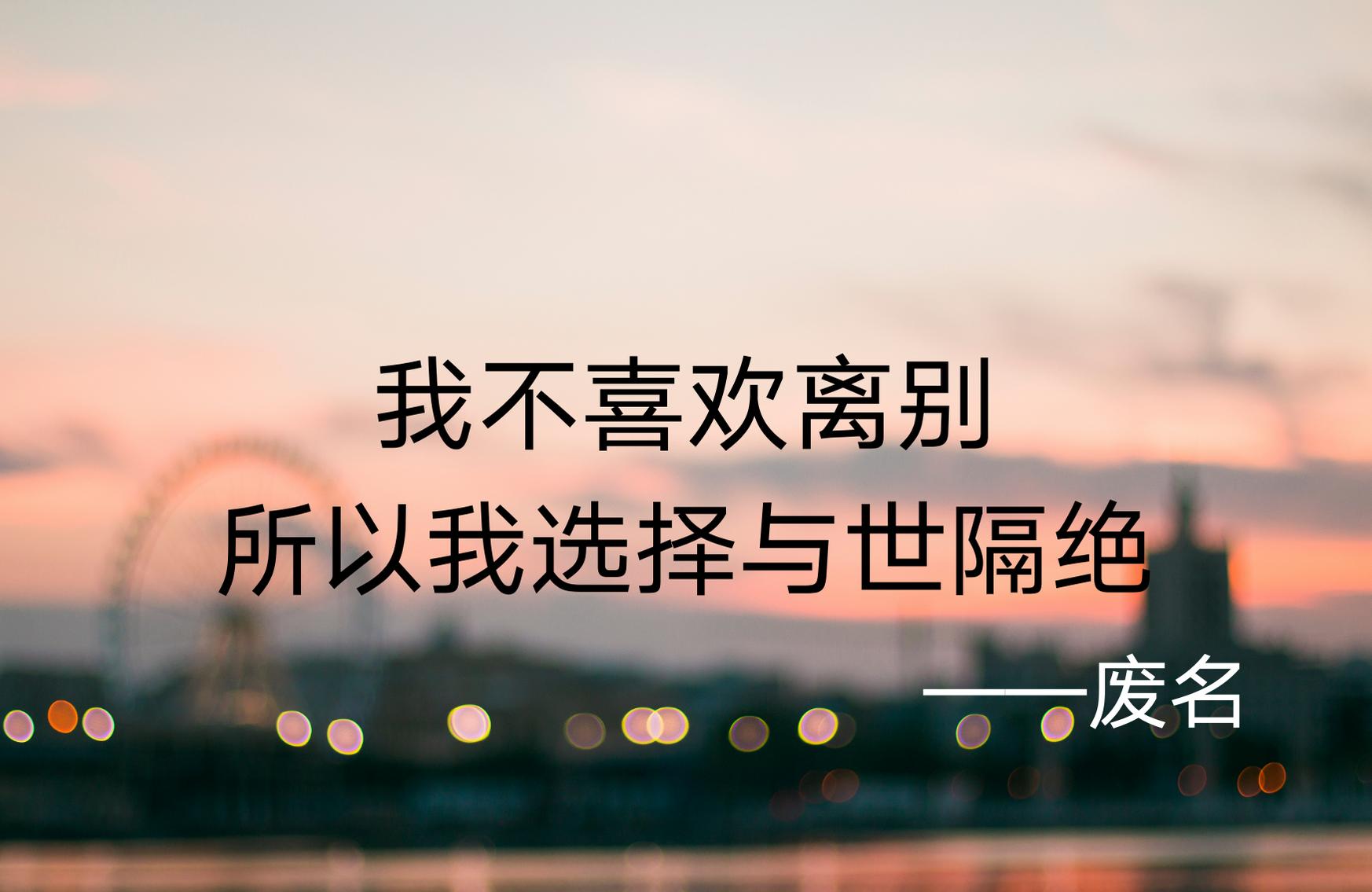
廢名出生于1901年,原名馮文炳,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家之一,師從周作人,“京派文學”的鼻祖。
小時候我們經常會感歎“佚名”這個人的才華,随着我們長大,知道了“佚名”是不知名或者不願透漏自己名字人們的稱謂,剛從這個彎繞過來,廢名便攜着晦澀難懂的詩文進入成人的生活。
《如切如磋》既是廢名在随筆中章節的名字,也是2018年,中國文史出版社整理廢名作品的合集名。合集中,廢名的《随筆》,《棗》,和《竹林的故事》均被收錄,為人們共賞廢名的生辣奇僻之美。
1927年4月23日,《語絲》周刊的第128期上面出現了這樣一組日記:《忘記了的日記》,什麼樣的人才會以這種獨特的方式給自己的日記命名呢?
這個人就是馮文炳,這組日記中記錄了1926年6月1日到14日的事件,其中6月10日中的内容就有“廢名”筆名的由來:
“從昨日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個名字,就叫“廢名”。我在這四年以内,真是蛻了不少的殼,最近一年尤其蛻得古怪,我把昨天當個紀念日子罷。”
話語中可以看出來,馮文炳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表示着自己的蛻變,此後“馮文炳”這個名字将會消失在人們的印象當中,受到作品感染或者一同産生共鳴的,也隻會驚歎于“廢名”這個稱呼。可是這位文學大師的作品,卻超前的令人難以懂識。
京派作家代表人物汪曾祺這樣評價廢名:“廢名的價值的被認識,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真正被肯定,恐怕還得再過二十年。”這句話出現在《廢名短篇小說集》中,汪曾祺寫的序言之中,那是1996年的3月。
汪老的預言到了現在,已經24年之久,人們仍舊對廢名感到陌生。
廢名小時候體弱多病,但卻家境殷實,且學習努力。1917年他考入湖北第一師範學校,就被剛接觸的新文學吸引到了,于是他勵志把畢生精力放在文學事業上。畢業後,他在武昌一所國小任教的時候,結識了周作人。
當時他給周作人的第一印象是:“廢名之貌奇古,其額如螳螂,聲音蒼啞,初見者每不知其雲何。”雖然初次見面并沒有給周作人偏偏俊朗的印象,不過這并沒有影響到二人的師徒關系。
廢名以墊底的成績考入北大之後,胡适主持的《努力周報》成為他學習新文學的寶貴園地。早在廢名于湖北第一師範學校就讀的時候,章黃學派嫡系傳人劉赜(博平)從北大過來執教,當時劉赜以一種鄙夷的語氣說北平有一個叫胡适的人倡導新文學。從那個時候廢名就知道胡适了。
在北大參加了“淺草社”,廢名在其發表了很多文章,取得了一些名氣,很多朋友一看就知道是廢名寫的。而他的這個名氣,引起了陳衡哲、胡适、周作人等的注意。
而後來的魯迅對其當時的評價很中肯:“後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并未顯出他的特長來。”顯然魯迅先生當時對廢名并不怎麼關注,或者說是他忙的到不上關注廢名。
得到胡适和周作人關注的廢名,以《竹林的故事》新鄉野風格拉近了他和二人的關系。1923年9月,他首次拜訪了周作人。同年,他也拜訪了胡适。
《語絲》時期,新文化運動開始分裂和重新整合,廢名也在這個時期走向成熟,而他作為《語絲》重要的撰稿人,經常得到魯迅和周作人的教導,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廢名發表了長篇詩化體小說《橋》。
1927年,胡适、魯迅南下,尚未畢業的廢名和周作人留了下來,以苦雨齋作為二人的精神寄托之地,互相安慰。新文化陣營徹底瓦解之後,廢名和周作人确立師徒關系。
廢名在文學創作上,并沒有附和那些可以給他帶來名利的雜文,從《竹林的故事》開始,他便以一種獨特隐晦的特色,踱進另一片幽勝。他的小說是當散文寫的,散文是當詩寫的。
他在北大做講師的時候,常常在講台上自問自答,旁若無人,并且聽者往往不知所雲。當然和現在的高校課堂氛圍不同,他并不是為了緩解自己課堂氛圍,而是真正的沉浸在了自我文化魅力當中。是以,他也同傅斯年,錢玄同一起,被稱為北大“三大魔”。
廢名的作品《理發店》:
理發店的胰子沫 同宇宙不相幹 又好似魚相忘于江湖 匠人手下的剃刀 想起人類的了解 劃得許多痕迹 牆上下等的無線電開了 是靈魂之吐沫
他原本想寫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卻刻意将“相濡以沫”嵌入當中,彰顯胰子沫、剃刀、無線電等構成的世界的荒誕,舞台上擠滿了物質,靈魂被渴死在邊緣。詩的立意很高,讀起來卻頗為突兀。
而廢名作品難懂的原因便在于此處,他總是從這個意向突然跳到另一個意向當中,給讀者帶來迷茫的感覺。他的小說也是一樣,雖然每一個細節都精雕細琢,言語也平實樸素,可是整體讀起來,依舊讓人難以捉摸其内在含義。
廢名也非常注重語言美,如《柚子》當中:“推開帳子,由天井射進來的月光,已經移上靠窗的桌子。”、“院子裡從前用竹竿圍着的豬窠,滿堆些雜亂的稻草,竿子卻還剩下幾根。”這些語句都表現出了一種質樸的語言美。
朱光潛先生曾說廢名:他不是循規蹈矩的小說家,他寫小說的時候,眼睛朝裡看,關注着自己的内心,他的人物沉沒在他的自我裡面,處處都在過他的生活。
可這種标新立異的寫作風格并不被文壇大家接受,甚至受到了很多鄙夷,連同他的老師周作人都不看好他的寫法。
周作人批評廢名後期從平淡走向“簡潔或奇辟生辣”,讓他大感失望。魯迅也說:“過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隻見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态。”魯迅也是廢名的老師,當時廢名多次給他投稿均未見發表。
沈從文也曾這樣批評過廢名:“此種作品,除卻供個人寫作的怿悅,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這工作意義上,不過是一種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罷了。”
然而面對這些批評,廢名選擇以一種沉默躬耕的方式,化作一盞獨立冬日中的燭火,成為文學創作孤島上隐晦的星光。
由衷的感謝大家付出寶貴的時間閱讀本文章,喜歡的朋友可以點個贊或者關注下小暖,小暖為出好文不懈努力……
圖文來自:青稞日暖
如需圖檔,還請關注作者後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