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大家在阅读之前,关注下小暖,一起探讨更多文化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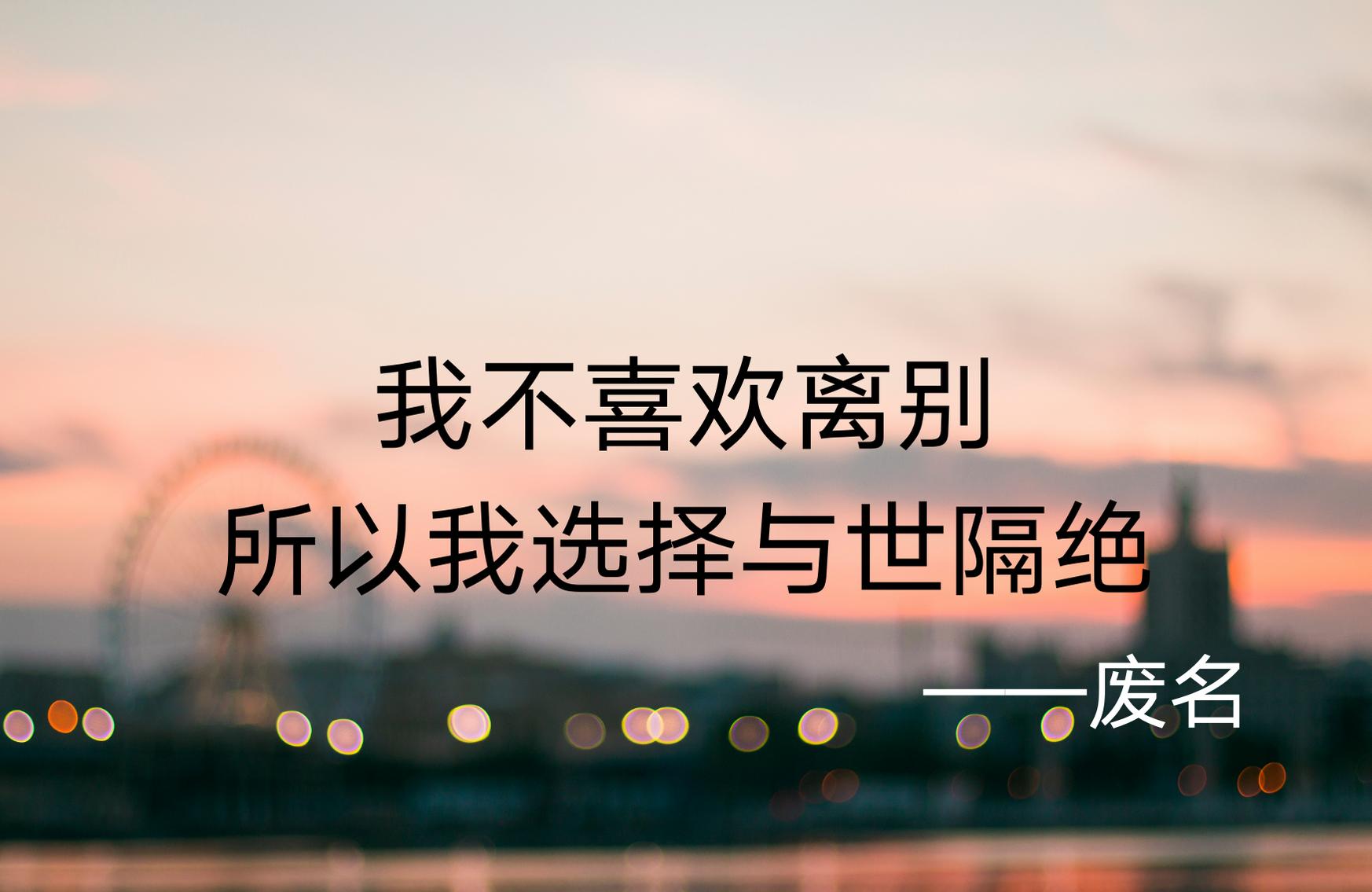
废名出生于1901年,原名冯文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师从周作人,“京派文学”的鼻祖。
小时候我们经常会感叹“佚名”这个人的才华,随着我们长大,知道了“佚名”是不知名或者不愿透漏自己名字人们的称谓,刚从这个弯绕过来,废名便携着晦涩难懂的诗文进入成人的生活。
《如切如磋》既是废名在随笔中章节的名字,也是201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整理废名作品的合集名。合集中,废名的《随笔》,《枣》,和《竹林的故事》均被收录,为人们共赏废名的生辣奇僻之美。
1927年4月23日,《语丝》周刊的第128期上面出现了这样一组日记:《忘记了的日记》,什么样的人才会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给自己的日记命名呢?
这个人就是冯文炳,这组日记中记录了1926年6月1日到14日的事件,其中6月10日中的内容就有“废名”笔名的由来:
“从昨日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我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
话语中可以看出来,冯文炳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示着自己的蜕变,此后“冯文炳”这个名字将会消失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受到作品感染或者一同产生共鸣的,也只会惊叹于“废名”这个称呼。可是这位文学大师的作品,却超前的令人难以懂识。
京派作家代表人物汪曾祺这样评价废名:“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被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这句话出现在《废名短篇小说集》中,汪曾祺写的序言之中,那是1996年的3月。
汪老的预言到了现在,已经24年之久,人们仍旧对废名感到陌生。
废名小时候体弱多病,但却家境殷实,且学习努力。1917年他考入湖北第一师范学校,就被刚接触的新文学吸引到了,于是他励志把毕生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毕业后,他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的时候,结识了周作人。
当时他给周作人的第一印象是:“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虽然初次见面并没有给周作人偏偏俊朗的印象,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二人的师徒关系。
废名以垫底的成绩考入北大之后,胡适主持的《努力周报》成为他学习新文学的宝贵园地。早在废名于湖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时候,章黄学派嫡系传人刘赜(博平)从北大过来执教,当时刘赜以一种鄙夷的语气说北平有一个叫胡适的人倡导新文学。从那个时候废名就知道胡适了。
在北大参加了“浅草社”,废名在其发表了很多文章,取得了一些名气,很多朋友一看就知道是废名写的。而他的这个名气,引起了陈衡哲、胡适、周作人等的注意。
而后来的鲁迅对其当时的评价很中肯:“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显然鲁迅先生当时对废名并不怎么关注,或者说是他忙的到不上关注废名。
得到胡适和周作人关注的废名,以《竹林的故事》新乡野风格拉近了他和二人的关系。1923年9月,他首次拜访了周作人。同年,他也拜访了胡适。
《语丝》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分裂和重新整合,废名也在这个时期走向成熟,而他作为《语丝》重要的撰稿人,经常得到鲁迅和周作人的教导,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废名发表了长篇诗化体小说《桥》。
1927年,胡适、鲁迅南下,尚未毕业的废名和周作人留了下来,以苦雨斋作为二人的精神寄托之地,互相安慰。新文化阵营彻底瓦解之后,废名和周作人确立师徒关系。
废名在文学创作上,并没有附和那些可以给他带来名利的杂文,从《竹林的故事》开始,他便以一种独特隐晦的特色,踱进另一片幽胜。他的小说是当散文写的,散文是当诗写的。
他在北大做讲师的时候,常常在讲台上自问自答,旁若无人,并且听者往往不知所云。当然和现在的高校课堂氛围不同,他并不是为了缓解自己课堂氛围,而是真正的沉浸在了自我文化魅力当中。因此,他也同傅斯年,钱玄同一起,被称为北大“三大魔”。
废名的作品《理发店》:
理发店的胰子沫 同宇宙不相干 又好似鱼相忘于江湖 匠人手下的剃刀 想起人类的理解 划得许多痕迹 墙上下等的无线电开了 是灵魂之吐沫
他原本想写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却刻意将“相濡以沫”嵌入当中,彰显胰子沫、剃刀、无线电等构成的世界的荒诞,舞台上挤满了物质,灵魂被渴死在边缘。诗的立意很高,读起来却颇为突兀。
而废名作品难懂的原因便在于此处,他总是从这个意向突然跳到另一个意向当中,给读者带来迷茫的感觉。他的小说也是一样,虽然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言语也平实朴素,可是整体读起来,依旧让人难以捉摸其内在含义。
废名也非常注重语言美,如《柚子》当中:“推开帐子,由天井射进来的月光,已经移上靠窗的桌子。”、“院子里从前用竹竿围着的猪窠,满堆些杂乱的稻草,竿子却还剩下几根。”这些语句都表现出了一种质朴的语言美。
朱光潜先生曾说废名:他不是循规蹈矩的小说家,他写小说的时候,眼睛朝里看,关注着自己的内心,他的人物沉没在他的自我里面,处处都在过他的生活。
可这种标新立异的写作风格并不被文坛大家接受,甚至受到了很多鄙夷,连同他的老师周作人都不看好他的写法。
周作人批评废名后期从平淡走向“简洁或奇辟生辣”,让他大感失望。鲁迅也说:“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只见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鲁迅也是废名的老师,当时废名多次给他投稿均未见发表。
沈从文也曾这样批评过废名:“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
然而面对这些批评,废名选择以一种沉默躬耕的方式,化作一盏独立冬日中的烛火,成为文学创作孤岛上隐晦的星光。
由衷的感谢大家付出宝贵的时间阅读本文章,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下小暖,小暖为出好文不懈努力……
图文来自:青稞日暖
如需图片,还请关注作者后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