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名著700種之第103種
♚
費希特的曆史哲學在德國古典哲學的曆史觀的發展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
《現時代的根本特點》就像康德的《從世界公民的觀點來看普周遊史的觀念》(1784年)和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演講錄》(1822——1831)一樣,是從先進文明的全球化角度來考察人類曆史發展的邏輯的。
在本書中,作者指明,每個民族的曆史既有其必然的發展趨勢,也有其偶然的變化形态,是以每個民族的成員應該既以世界公民的意識,也以愛國主義的态度看待和參與曆史程序。由此,本書不僅上繼了康德的傳統,而且下開了黑格爾的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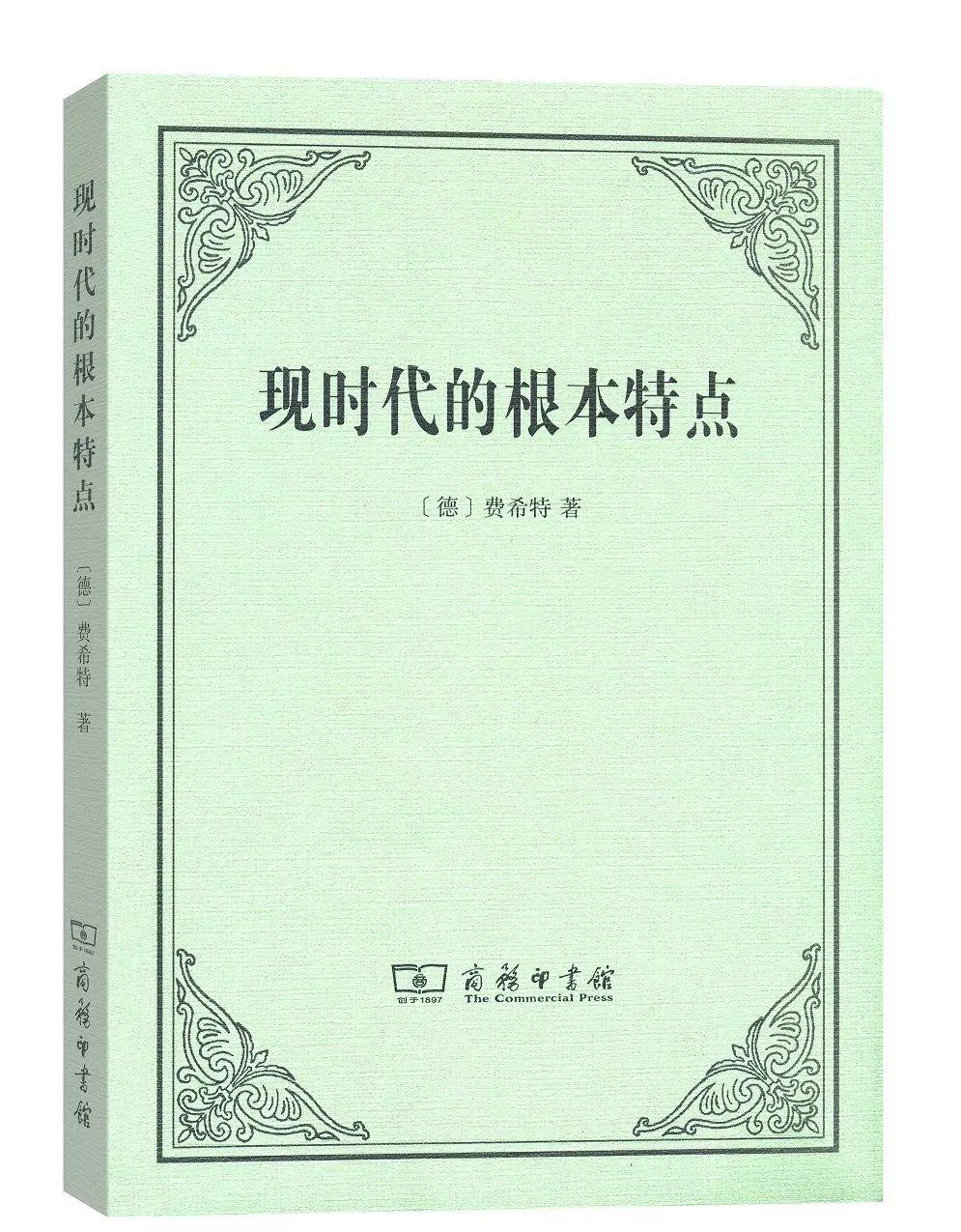
在德國古典哲學中,費希特的《現時代的根本特點》(1806年)就像康德的《從世界公民的觀點來看普周遊史的觀念》(1784年)和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演講錄(1822—1831年)》一樣,是從先進文明的全球化角度來考察人類曆史發展的邏輯的。關于這一考察所做出的獨特貢獻,我們可以從以下九個方面予以評述。
費希特
(一) 費希特的曆史哲學首先是從時間的起源談起的。這是因為,時間是任何現實事物的過程本身,無論什麼曆史哲學都應該說明,作為這個過程本身的曆史是如何可能的,不做出這樣的說明,就是非批判地肯定了曆史哲學的研究對象。
費希特看出了以往的曆史哲學的這個缺陷,是以在他的早期知識學裡就演繹了時間:逾時間的自我通過自己設定的非我的阻礙作用,展示出一個無限的時間序列,在這個序列中各種客體被設定起來,進而克服了康德那種沒有從自我推演出作為感性直覺的純粹形式的時間的缺點。在晚期知識學裡,他又繼續研讨了時間的起源問題。不過在這個時候,時間已經不再被認為是植根于自我的設定活動中,而被認為是顯現絕對的一個不斷展開的環節;他在這時認為,絕對是逾時間的存在,是唯一的、真正存在的和絕對靠自身存在的東西,是在所有的語言中都被稱為上帝的東西;絕對必然要表現出來,也就是說,上帝必然要顯現出來,而這種顯現就是知識活動,就是神聖力量的表現和映現;這種知識活動具有創造萬物的神力,它設定了自己的對象,靠這種對象不斷地發展自身,進而出現了時間。由此可見,費希特已經認識到,時間是絕對顯現自己的過程,或反過來說,時間上的變化是絕對的顯現。
這種關于逾時間的存在創造時間上發展過程的觀點,不管講的多麼晦澀難懂,也不管帶有多少神學色彩,隻要我們把它與現代宇宙學作為最高原理提出的假說加以比較,就很容易了解,它确有其合理性。現代宇宙學認為,宇宙是從初始奇點出發,分裂為物質在時間上的無限發展過程的,在經過品類繁多、光輝燦爛的發展以後,又塌縮到這個奇點。這個假說也許可以被視為費希特的時間起源理論的經驗科學表達,或者反過來說,他的這一理論是對現代宇宙學的思辨預見。不過,費希特也像當時的許多哲學家一樣,認為那種被知識活動設定的對象是在時間上沒有發展和變化的自然界,而隻有在時間上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社會才是逾時間的存在靠這種對象發展其内在力量的曆史過程。
(二) 在費希特看來,這種由逾時間的存在構成的發展過程就是人類的文明史,在這裡,歐洲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都處于一個共同的起源,并且在将來會複歸于這個共同的起源。
雖然他在他的曆史哲學裡考察的完全是歐洲文明的曆史,而沒有研讨人類文明的其他分支,但他卻以他的知識學為依據,分析了人類曆史的内部結構。他認為,人類曆史包含兩個互相密切聯系的部分,即先驗部分和經驗部分。前者是必然的存在,它展現的是作為曆史目标的宇宙藍圖及其實作的過程,是人類曆史發展的邏輯;後者是偶然的現實存在,它展現的是數量無窮的曆史事實及其出現的過程,是人類曆史發展的經驗。這兩個方面分别構成了曆史哲學研究的對象和曆史學研究的對象。費希特由此規定了曆史哲學與曆史學的任務。
(三) 關于人類曆史中的那個先驗部分,康德稱之為大自然的隐蔽計劃,并将其展開劃分為本能的統轄、自由的狀态和完善的公民社會這樣三個階段。費希特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把那個先驗部分稱為人類世俗生活的發展所遵循的宇宙藍圖,把它的實作描述為理性從盲目的統治到自覺的統治的過程,描述為社會從不文明狀态到文明狀态的過程,它的含義在于,“人類的世俗生活目的就是人類在這種生活中自由地、合乎理性地建立自己的一切關系”。
這個目的的實作經過許多迂回曲折的道路,以不可移易的必然性,刻畫出五個不可超越的時代或者基本時期:第一,無須進行強制,不必付出辛勞,人與人的關系隻靠合理本能加以安排的時期;這是理性借助于本能進行直接統治的時期,叫做人類無辜的狀态。第二,合理本能已經變弱,隻表現于少數傑出人物身上,被他們變成一種對大家有強制作用的外在的權威的時期;這是各種學說體系和人生體系采取專斷态度的時期,叫做惡行開始的狀态。第三,直接擺脫專斷的外在權威,間接擺脫合理本能和任何形态的理性統治的時期;這是對任何真理絕對漠不關心,不要任何指導而晚期放縱的時期,叫做惡貫滿盈的狀态。第四,具備科學形态的理性普遍傳播于人類,理性及其規律在清晰的意識中得到把握的時期;這是真理作為至高無上的東西得到承認和最受人喜愛的時期,叫做理性開始的狀态。第五,通過完善的技藝,按照理性的規律,人類的一切關系得到調整和安排的時期;這是人類擁有确實可靠的、以不出錯的手段,把自身塑造為理性的準确摹本的時期,叫做說理完善和聖潔完滿的狀态。費希特預測,在這個時期,國家作為管理合理的技藝的機構,将自覺地、有計劃的緻力于完成理性提出的任務;這樣,人類就以自由的、合理的行動建立起了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以理性為最高準則、大家都平等自由、人人為我和我為人人的社會。費希特的這個社會史藍圖當然屬于近代西歐啟蒙時期的樂觀主義思潮,它雖然已經被現代的現實生活所揚棄,但它所蘊含的真理成分卻至今都對我們有啟迪意義。
(四) 按照費希特制定的這個藍圖來說,雖然許多民族在人類曆史上有過其輝煌的時期,但并不是任何一個在人類曆史上出現的這樣的時期都可以被算作一個時代,而是隻有那種能夠以其原則涵蓋全人類的時期才有資格被列為一個時代。
這個界定時代的标準不僅對我們考察較遠的曆史時,而且對我們考察較近的曆史也有重要意義。一個自文藝複興以來自然而然地得到實作的原則,在經受了經濟危機、世界大戰和暴力革命的震蕩以後,已日臻完善,進入快速全球化的階段,因為這個以它為基礎的時期也就表明了自己是人類世俗生活發展的一個時代。反之,一個從20世紀初葉從單個人的特殊信念出發,用人為手段加以貫徹的原則,則由于不能提供更高的勞動生産率和更高的民主,而自己毀滅了自己,因而這個以它為基礎的時期也不過表明了自己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短暫插曲。雖然前一個原則的實作不免帶有許多惡果,是以不是我們的理想,不是曆史的終極目的,但它作為一個必經的重要時代的原則,至今還沒有完成其囊括和傳遍全人類的使命。
(五) 在費希特制定的那個藍圖的實作中,作為曆史過程本身的時間分化為兩種:一種時間标志着先驗部分的展開,這就是不均勻地流逝着的概念中的時間;另一種标志着經驗部分的進展,這是均勻地流逝着的編年史的時間。
由于這兩個部分的進度有反差,在同一個編年史的時間裡就總是彙聚着一些不同的概念中的時間;費希特就此寫到,“由于要把所有民族聯合為一個大家庭的目的使然,這就可以使概念中的時間通過相當可觀的編年史時間,而停留在同一個地方,仿佛可以迫使時間的長河停頓下來似的”。這意味着,在同一個編年史時間裡總有一些不同的個體,他們處于不同時代的不同的文明發展階段。于是,在同一個編年史時期總是有不同的個體,費希特把他們分為三種:一種是“那些确實是自己時代的産物,把這個時代表現得最清楚的個人”;另一種人“落後于自己的時代,因為他們在他們的發展期間從來沒有與範圍廣闊的、代表一般發展水準的個體有什麼接觸,他們發展自己的那個狹隘圈子還是舊時代的遺老遺少”;第三種人則“已經走得超過自己的時代,他們的心中帶有新時代的萌芽,但在他們周圍占支配地位的仍是這個被他們視為業已陳舊,實際上卻真正現實的現時代”。費希特的這種分析讓我們聯想到,正像在19世紀中葉德國人與法國人相比,僅僅在編年史的時間上,而不是在概念中的時間上是同時代人一樣,當今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是如此。但很令人遺憾,我們周圍還有一些人,他們以為自己超越了現時代的原則,其實他們尚未達到這個原則。
(六) 在費希特制定的那個藍圖的實作中,各個民族和國家都是作為獨立自主的有機整體不斷發展的,并且處于不同的社會進化階段。于是,在這種發展不平衡的局面中,發達的有機體成了不發達的有機體的原型,業已進入世界曆史的進階階段的民族和國家是評判尚未進入這個階段的民族和國家的尺度。從這樣的事實着眼,費希特在講世俗生活的第三個基本時期時簡明扼要地寫到,“要對時代做出評判和認識,隻有躍居其時代的文明之巅的那些民族才可能做到”,并且他進而指出,做出評判的唯一有效的準則就是那些“居于現時代頂峰的人們的基本準則,亦即現時代本身的原則”。不管這個說明多麼簡短,它也能使我們看出,當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裡談到“資産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鑰匙”時,他對這位德國古典哲學家的繼承關系是十分明顯的。我們完全可以按照他們的社會進化論觀點斷言,沒有任何一個落後于時代的民族和個人會有資格對現時代做出正确的評判,在當今的國際社會中,從概念的時間來看,發達國家遠比不發達國家先進,是以它們對現時代做出的評判就比不發達國家對現時代做出的評判要正确的多,依照前一種評判制定的國家規則當然應該逐漸傳遍全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不發達國家無疑應該積極創造遵守這些規則的條件,但發達國家卻不可将這些規則強加于任何尚未具備這類條件的國家。費希特曾經針對當時出現的類似問題寫到,“時代以它的堅定的、向來就已給它确定的步伐前進着,任何東西在時代的長河裡都是不能靠單槍匹馬的力量加速或者強求的”。這就意味着,時代是不可阻擋地前進的,不發達國家的人民絕不可能長期脫離世界文明的光輝道路,而是會經過艱難的、曲折的曆程走上這條道路,而那種想強迫這樣的國家服從自己的意願的單槍匹馬的力量則在充當一種世界警察的角色。
(七) 在費希特闡明歐洲文明的發展過程時,他把跌宕起伏地貫穿其中的種種沖突分為兩類:一類是代表先進文化的标準民族與未開化的愚昧民族之間的、或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沖突;另一類是各個歐洲國家内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前者是歐洲文明的外部沖突,後者是歐洲文明的内部沖突。
關于前一類沖突,費希特認為,有教養的民族應該進行統治,野蠻人應該效勞;隻有在文明與野蠻的這種沖突中,一切思想和一切科學作為把野蠻引向文明的力量和手段,才開始萌芽,獲得了發展;文明反對它周圍的野蠻的天然戰争對于促進世界曆史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關于第二類沖突,費希特指出,基督教民族共同體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進階階段,不僅在公民法方面,而且也在國際法方面貫徹了人人平等的原則,雖然這個原則在當時并沒有通行于周圍的非基督教國家。如果我們綜觀人類當今的狀況,我們也許可以說,第一類沖突現在已經消失,野蠻人進入了文明階段,雖然他們的文明還處于這樣或那樣欠發達的階段;是以,費希特的論點已經不再有任何現實意義。但他關于第二類沖突所說的,則另當别論。全人類現今的文明程序都有了長足進步,以緻那種依據歐洲文明成果确立起來的公民法準則和國家法準則是否能夠分别推行于非基督教國家内部和這類國家與基督教國家之間,都已經稱為現時代所面臨的最大曆史課題,也是全人類要解決的最大現實問題。在這裡,抵制前一種準則的引入是倒行逆施,無視後一類準則的推廣是侵略行徑。正像在國際關系中要求平等而在國内關系中制造不平等是可笑的一樣,在國内關系中堅持平等而在國際關系中不講平等也是荒唐的。
(八) 費希特在《現時代的根本特點》裡已經扼要地指明,每個民族的曆史既有其必然的發展趨勢,也有其偶然的變化形态,是以每個民族的成員應該既以世界公民的意識,也以愛國主義的态度看待和參與曆史程序。
在随後寫出的《愛國主義及其對立面》(1806—1807年),他進一步闡述了這個主題。在他看來,世界主義就是一種認為人類生活的目的定然會得到實作的信念,而愛國主義是一種認為這個目的首先會在我們是其成員的民族中得到實作,然後将所得的成就傳遍全人類的信念。他所說的人類生活的目的,就是人類自由地、合乎理性地建立自己的一切關系,或者說,是建立理性王國;這是人類文明的普遍原則,它将具體地展現出來。是以,費希特認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麼抽象的世界主義,相反地,世界主義在現實中勢必會變成一種以建立理性王國為宗旨的愛國主義。之是以如此,是因為世界主義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會毫無作為,而是必然會表現出來,按照自己的方向進行工作和發揮作用,但是,它隻能影響它作為活生生的力量直接生存于其中的那個國家,而這個國家則以自己的手段,按照自己的法律,在自己的界限内不斷地引導它發生影響的活動。
(九) 費希特在《現時代的根本特點》中闡述的曆史哲學充滿了辯證法的内容。在他所講的那五個理性與反理性的沖突發展的基本時期,理性經曆了一個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曲折過程。我們可以把前兩個時期概括為理性首先直接通過本能,然後作為本能間接通過權威進行統治的階段,概括為盲目進行的理性統治日益式微的階段,而把後兩個基本時期概括為理性首先進入知識,然後借助技藝進入生活的階段,概括為明察秋毫的理性統治的階段,而介乎這兩個階段之間的第三個基本時期是把黑暗世界與光明世界、強制世界與自由世界結合起來的階段,是本能形态的理性遭到毀滅和概念形态的理性開始誕生的階段;這樣,理性的發展在其遭受反理性東西的沉重打擊的時期,也就進入了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的時期。費希特就此寫到:
人類在塵世中通過這一系列時期走過的整個路程,不外是向它最初所處的那個階段的回歸,無非是要複歸于它的原始狀态。但人類必須用自己的雙腳走出這條道路,它必須用本身的力量又使自身成為它從前不借自己的任何作用所成為的那樣,正因為如此,它首先必須喪失自己的原始狀态。
費希特的曆史哲學在德國古典哲學的曆史觀點的發展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他的《現時代的根本特點》不僅上繼了康德的傳統,而且下開了黑格爾的先河。如果我們把黑格爾的觀點與費希特的曆史哲學思想加以比較,就很容易斷定,黑格爾的曆史哲學在其基本觀點方面都是對費希特的繼承和發展。
【《現時代的根本特點》譯者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