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3.16章指出春秋的政治需要建立以庶民社會為中心的治理,而這種治理與傳統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狹義的為政相違背,傳統的政治欲速,下如13.15言魯定公所講的,一言以興邦,政治需要急功近利的效果。而另一方面,政治需要小恩小惠,才能滿足無法滿足的欲望。但是,仁學所要實作的以庶民為中心的治理,則與傳統的貴族治理完全相反,無欲速、無見小利,實行的是和風細雨式的潤物細無聲的政策,不講究小利,而是實作群眾啟蒙的大從。是以,傳統的為政與仁學的為政在思維、政策與方法上都完全相反 。在孔子孔之後,美德與政治的聯結,以美德來評價政治就成為了共識,如《荀子》曰: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還有著名的孟子仁政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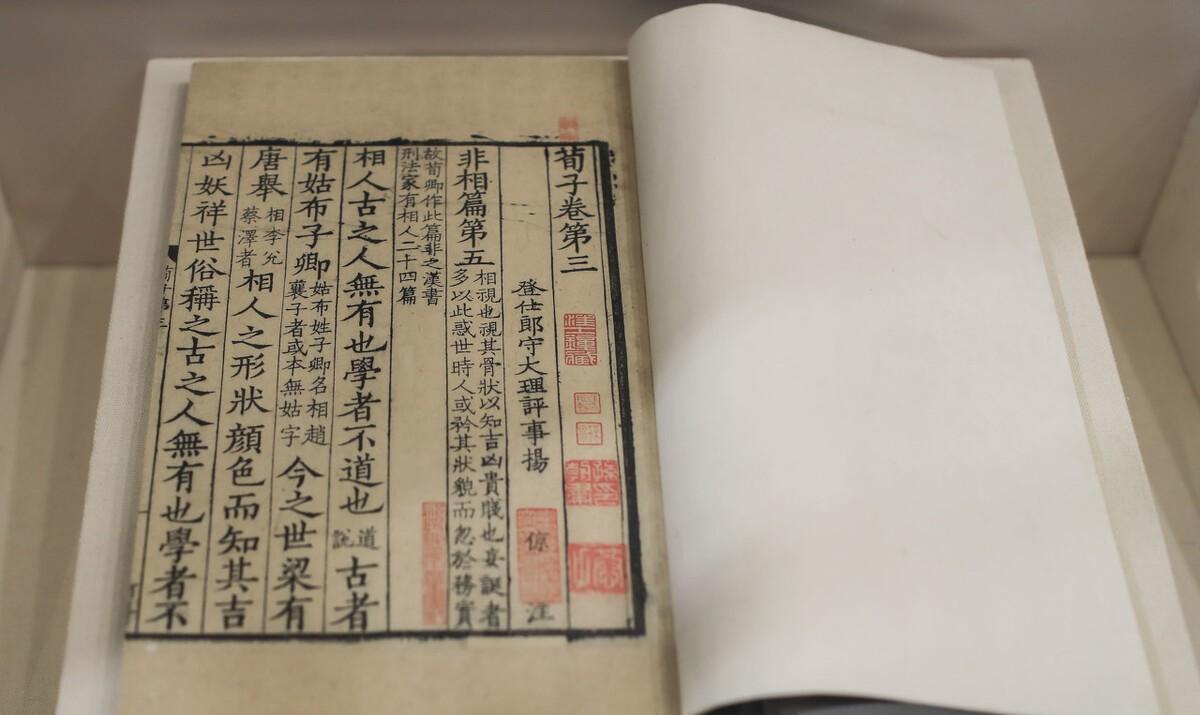
13.17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參考譯文】子夏做莒父這個地方的宰官,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子說:“不要貪求速成,不要隻見小利。貪求速成就達不到目标,隻見小利就辦不成大事。”
莒父:魯國西部的小邑。父,音“甫”。“莒”後加“父”,是魯人語音,如“梁父”等。《山東通志》:“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于城陽。漢始封劉章為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宰:地方長官。無:通“毋”,戒止之辭。利:好處、利益。《正義》:“利謂便國益民也。”達:到達。
傳統對本章的釋義,均依字面之義,即為政之道,無欲速,無見小利,其實,若與上文的幾章聯系起來,尤其是魯定公之問,一言即可興邦,何其速也!是以,需要探讨仁學為政為何能夠相對于一般的政治,能夠反其道而行?如何能夠做到無欲速?無見小利?
:漢代戴德《大戴禮記》曰:好見小利妨于政。 三國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論語注疏》曰:此章弟子子夏為魯下邑莒父之宰,問為政之法于夫子也。事有程期,無欲速成,當存大體,無見小利也。 南朝皇侃《論語義疏》曰:政貴有恒,不得見小财利而曲法為之。 南宋朱熹曰: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明末劉宗周曰:王道規模宏遠,蓋自純心中流出。一動于計功謀利之私,不免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旦夕而無宏遠之規,此霸術也。故為政者未論政,先論心,則孰有病于欲速、見小兩念哉?何也?欲速則政不達矣,所見者小則政之大者廢矣,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蘇轼進神宗書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驟。”皆欲速見小之病也。欲速、見小,兩念相因。程子曰:“有天德者,便可以語王道,其要隻在慎獨。” 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曰:為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興行,但不可見小耳。 清代《四書解義》曰:此一章書見治道貴以遠大為期也。蓋欲速則求治急,而無次第,求治愈急而行之愈礙,反不能達矣;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謀及一身而不及天下,謀及一時而不及萬世,将至所就小而所遺大,大事必不成矣。從來久道而後化成無欲,乃可言至治。所貴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也。 清代李颙《四書反身錄》曰:為政欲速非善政,為學欲速非善學。又曰:若求治太急,興利除害,為之不以其漸,不是忙中多錯,便是操切偾事。自古成大事者,眼界自闊,規模自别,甯敦大成裕,不取便目前,亦猶學者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 清代黃式三《論語後案》曰:管仲天下才,而弊在欲速見小。後世之稱盛治者,辄言霸王道雜,弊亦同此。無欲速、見小之心,此黜霸崇王之政也。 近代唐文治曰:此尊王黜霸之旨。告知以此,即“必世後仁”之意,千古政治之名言也。 近代徐英曰:老子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凡欲成天下之大者,不務近小,不求速成。務小求速,未有能成其大者也。凡惼(biǎn)狹之人,多務小而求速,故夫子教之以遠大。
春秋政治,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快速和小利,13.10章中的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就突出政治的短速的特點 。政治的首要任務是維持統治的秩序,任何違背秩序的現象都需要用有效、極端的方法予以鎮壓。13.15章中的“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是當時君主制度的普遍特點。任何與此秩序相背的雜音,都将會被無情鎮壓,如鄭國的鄭莊公與公子段叔的沖突,齊國公子小白與公子紀的沖突、衛國的衛靈公、蒯聩(kuǎi kuì) 和衛出公公孫辄的王位糾葛,還有晉國的大夫篡權、魯國的三桓亂政,都可以看出專斷的諸侯制度體系使得國君的個人品格、欲望得以無限放大,無法節制,一切依靠于君王個人的良知來節制。以齊桓公為例,激烈的王權争鬥和諸侯間激烈的競争,使得齊桓公對自身的處境和自身的品質有着清醒的認識,齊桓公憂患的“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
如《莊子》所記載的 “輪扁斫輪”說明齊桓公對智慧有着清醒的認識。
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斫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公對智慧的清醒認識。
如寡人有三邪,說明齊桓公對自身有着清醒的認識。
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緻,百官有司無所複。”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緻、百官有司無所複。”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能夠作用賢臣,簡政放權,說明他對政治有着清醒的認識。
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但這種清醒并不是建立在制度制衡的長效機制之上,而是建立在君王對外在競争壓力的感覺和個人良知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與君王的個人能力有關。而當外在的壓力或個人的良知喪失時,這種清醒就不存在了。在春秋時代,具有這種能力的君主可遇不可求,屬于鳳毛麟角,少而又少。齊桓公之清醒,世之罕見,但即便具有這種巨大能力之人,在權力巅峰日久,也會失去危機感,追求享受之時,任用易牙、豎刁、常之巫和衛公子啟方四大小人,自身和國家就處于混亂之中了,政治秩序亂了,更别說關注庶民的啟蒙了。由此而有感歎,
“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見仲父衣乎?”
關注眼前的利益,欲速、見小利,宏才大略的齊桓公尚且如此,世間其他又有幾人能夠反其道而行呢?
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複召而反。
确實如此,深得仁學有教化的子夏也不能避免欲速,見小利的特點,可見,這是常人的一般特點。世人講究的實效、效果,其實正是欲速、見小利的結果。可見,欲速、見小利其實是人之本性使然。
蔔商(公元前507年—前400年),姒姓,蔔氏,名商,字子夏,名列“孔門七十二賢”和“孔門十哲”之一,以“文學”著稱,被尊稱為蔔子。子夏個性陰郁勇武,好與賢己者處,曾任莒父縣令。子夏善于思考、歸納,能夠将孔子複雜的仁學思想簡單化,極易操作,對孔子的思想具有創新性地發展。
如将孔子仁學思想的基礎 :好學進行歸納,在《學而篇》中被采納作為經典定義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緻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如對詩的深入思考,深得孔子思想精髓,使孔子大為感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在學習過程中,能夠幫助其他同學解決疑問。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樊遲問仁。子曰:“夫妻。”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子夏對孔子的思想有着許多開創性的發展,孔子去世後,面對孔門喪亂,子夏前往魏國教學育人,收取李悝、吳起為弟子,被魏文侯尊為師傅。子夏不像顔回、曾參一樣嚴守孔子之道,而是一位頗有經世傾向的思想家。他不再關注“克己複禮”,而是與時俱進的當世之政,提出一套延展儒家正統政治觀點的政治及曆史理論。
但是,即便是如此對仁學有着深邃了解,跟随孔子多年者,仍不免有欲速,見小利的特點。
比如,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被傳統奉為經典、 圭臬,其實,這正是世人欲速、見小利的結果。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何其速也!為官幹祿,人無小利不活!但這種簡單化、單一化的歸納其實并非孔子仁學的思想,這裡沒有考慮政治之惡,沒有考慮膝雕開、闵子骞為代表的成人模式,将政治與好學作直線聯系,而否定了仁學的多元化模式。
再比如,子夏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這種抓大放小的思維也被世人奉為至寶,這樣可以迅速成才。但是,仁學的禮樂之道,正是嚴格地從小道做起,即便是子夏自己,也是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緻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為何又有大德、小德之分呢?仁學過于複雜,故“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一般人的欲速、見小利,阻礙了他們對事物的深刻認識。正如子夏自己講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緻其道。”成其事往往其世人的見小利劃上等号,而緻其道才是人生之大利,但世人往往視而不見。
正是子夏的重效果、重實踐的思維,使得他的思想很具有創新性,簡潔、易行,但同時,也不免于受到欲速、見小利的影響,是以,才有孔子教導的“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世間的實效、欲速、見小利,并沒有錯,它是個體在世間生存的法則,也是個體發展的最為基本的動力。為政其實離不開這些屬性。
但是,若是要将政治與美德聯系在一起,而美德涉及到另一個與世俗的世界完全不同的領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美德關乎人的内在人格塑造,世俗世界的法則在此并不适用,而需要适用智慧法則,或是仁學法則。是以,這就可以得出,在一般的為政問題上,如權力的集中、政敵的清除、親信的作用,其實是适用欲速、見小利的原則;而隻有在關乎民德民心,開啟民智的領域,也就是需要将美德與政治聯系起來的地方,才會有無見速,無見小利的問題。13.18章的父為子隐章,13.19樊遲問仁章,13.20章子貢問士章,均講制度倫理與内在人格問題,正好印證此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