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決定意識,閱曆決定文風。我們在賞析一個作家的作品時,肯定離不開分析他的成長過程,最好能從他的原生家庭一直說到他的一生風霜。對作家生平經曆了解得越透徹,我們就越能明白他為什麼寫這種内容,寫這種内容是為了表達什麼感情。對于屈大均詩作的賞析自然也離不開這種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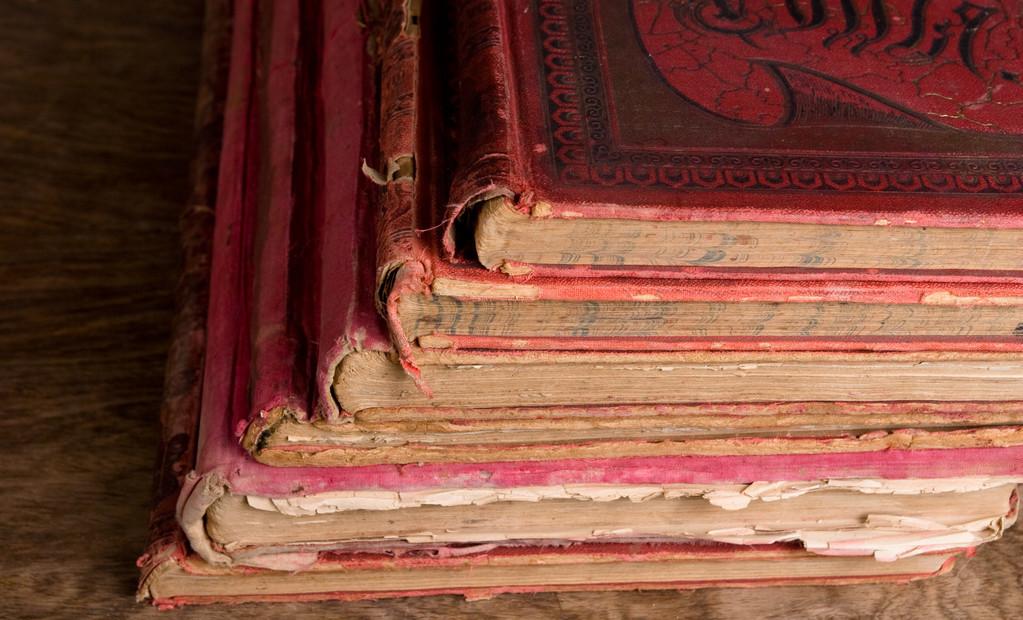
屈大均自幼聰明好學,“讀書過目成誦,每夜必就母黃紡績燈下,讀新書三十篇。晨起在父前背誦,不遺一字。”十六歲時“從陳邦彥受《周易》、《毛詩》,邦彥數賞先生文,謂為可教。”傳統的儒家教育培養了屈大均經世濟民的情懷。清兵滅明朝,屈大均随陳邦彥參加起義軍對抗清廷,後陳邦彥被俘殉節。屈大均是以就背負了國仇家恨之外的師仇,這也是他堅定抗清的一個原因。而從軍的經曆也使翁山詩迸發出高于其他遺民文人的聲調,顯示出超然獨行的豪邁氣概。這與辛棄疾的豪氣詞相類似,都是愛國壯志豪情與報國無門壯志難酬相碰撞所發出的呼嘯。
屈大均從學時曾經學屈原、學李白。屈大均以屈原後代自居,雖然未必是事實,但足以說明他對屈原的敬仰。他學習屈原《離騷》,對自己作品的命名也和屈原挂鈎,有《騷屑詞》,他甚至把《翁山易外》、《翁山文外》、《廣東新語》、《有明四朝成仁錄》、《翁山詩外》稱為“屈沱五書”(屈沱為屈原故鄉)。屈大均學屈原并非單純源于共同的姓氏,更深一點的原因在于二人相類似的遭遇,這使屈大均對屈原的作品産生了精神層次上的共鳴。另外他又學習李白,李白潇灑俊逸的人格和李詩的浪漫主義風格對屈大均産生了極大的影響。例如他的“白發不驚明鏡滿,秋霜隻怨雁門多。”(《客雁門作》)很明顯受李白“不知明鏡裡,何處得秋霜”(李白《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的影響。屈原和李白對屈大均詩歌創作的影響非常大,這也是他在困境中仍能振臂長嘯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他的交遊十分廣,與朱彜尊、王士祯、錢謙益等文士都有詩文來往,這對開闊他的胸襟懷抱十分有益。
屈大均曾有一段委身佛教的人生經曆。屈大均二十一歲“以國變托迹為僧。事函昰于雷鋒,法名今種,字一靈。”而他的《歸儒說》則剖析了他入佛又還俗的思想軌迹:
予二十又二而學禅。既又學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盡棄之,複從事于吾儒。蓋以吾儒能兼二氏,而二氏不能兼吾儒,有二氏不可以無吾儒,而有吾儒則可以無二氏雲爾。故嘗謂人曰,予昔之于二氏也,蓋有故而逃焉,予之不得已也。
雖然翁山明确指出遁入空門是因為“國變”,而且他從未真正的潛心向佛,但他在托迹佛門的時候未必不受禅學的熏陶。佛家學說的教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他看待國仇家恨的思維方式,進而影響到他的詩歌創作。
其一,翁山作詩喜用各種色彩詞,“白草黃羊外,空聞觱篥哀。”(《雲州秋望》),“白草”與“黃羊”勾勒出的畫面蕭瑟中帶有幾分生機;“白首難孤往,青山欲早歸。”(《漢口》)“白首”與“青山”形成生動的對比;“紫蒙近接黃花戍,黑水斜穿白草軍。”(《紫蒙》)這兩句詩歌更是運用了多個色彩詞來寫景,而“我昔化為一蝴蝶,五彩绡衣花作餐。”(《羅浮放歌》)雖無色彩詞出現,卻已讓人聯想到色彩斑斓。色彩詞的恰當運用不僅使詩句極富神韻,而且使詩人的感情表達得更微妙更傳神。
其二,動态詞的巧妙穿插。“帆随南嶽轉,雁背碧湘飛。”(《人日衡陽道中》)、“多少哀笳吹不散,五雲猶繞玉床飛。”(《鐘山》)、“水如奔箭穿霞壁,舟與浪花相拒敵。”(《上峽》)、“風助群鷹擊,雲随萬馬來。”(《雲州秋望》),這些動态詞賦予了沒有生命的事物以獨特的性格色彩,使詩歌所表達的思想内容更生動 ,更有氣勢。
其三,典故的含蓄化用。用典也是詩歌中常用的抒情達意的方式,這在翁山詩中随處可見,“遙尋蘇武廟,不上李陵台。”(《雲州秋望》)借對蘇武的敬重和對李陵的蔑視,來表達自己對明王朝的忠貞不二,以及對變節之人的憎惡。“朝與侯嬴飲,暮為朱亥留。”(《過大梁作》)借戰國時的侯嬴與朱亥來表明自己的壯志豪情。典故含蓄地表達出詩人的思想情懷,使詩人的感情明朗化,同時也增強了詩歌的浪漫主義色彩。
屈大均在清初的影響頗大,和陳恭尹、梁佩蘭号稱 “嶺南三大家”。不論是他本人忠貞不渝的愛國情結還是他雄健夭矯的詩風,都在清初産生了極大的影響,也鼓舞着其他愛國志士在艱難困苦中做不屈不撓地抗争。清王朝在屈大均逝世78年後仍不肯罷休,将其所有著作都列為應該焚毀的禁書,甚至将其子孫後代或流放或“從寬”問斬。清王朝這種斬草除根的做法,正是因為屈大均作品實在是具有很強大的号召力,而這種号召力正是清廷所畏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