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幻大師雷•布拉德伯裡在1950年創造了一個沒有書的未來世界。我們熟悉的消防員,在雷的世界裡不是救火救災的勇士,而是“文明的衛道士”——他們奉命燒毀書籍。華氏451度正是紙張的燃點。
雷的的創作具有很強的現實前瞻性,他幻想世界是一個受“反智主義”支配的世界。他的設想甚至比“反智主義”這個詞被創造出來的時間還要早了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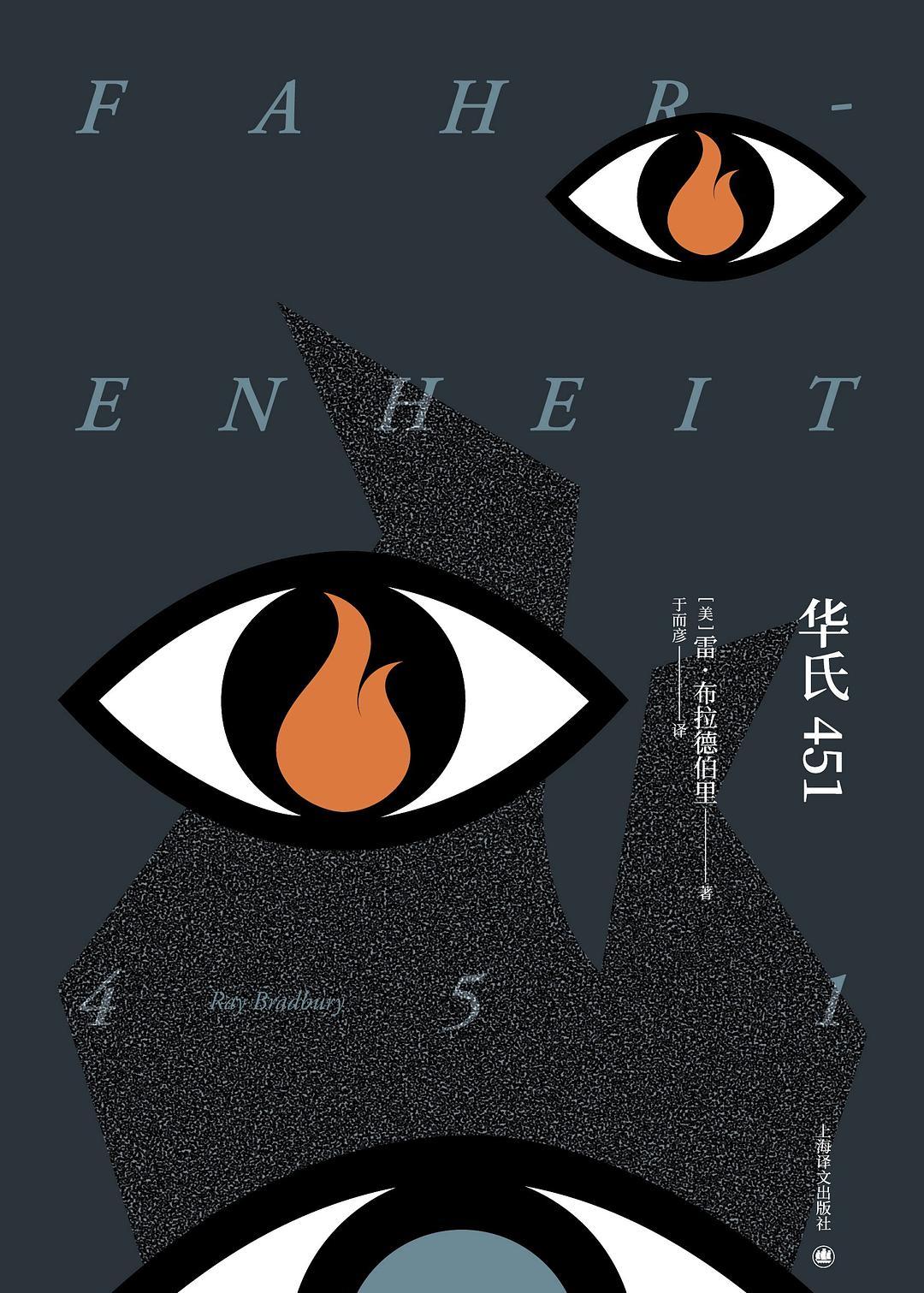
“反智主義”首次出現是在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書《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當中。這本書一經出版就在1964年獲得曆史學普利策獎。理查德用“反智主義”描述一種由于知識與無知的分歧産生的沖突表現。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人群之中,“反智主義”會呈現不同的結果。其中幾種比較有代表性的現象是:不假思索的跟風,反對真理以及讀書無用論。
《華氏451》中,統治者用強權貫徹“反智主義”,試圖扼殺普羅大衆的思想。故事開始的時候,主角消防員蒙塔格以手握銅管,噴吐火焰為榮。可自從他遇見那個充滿好奇心的女孩兒之後,一切就開始變得不一樣了。心中的求知欲望被激發出來,驅使他從一個執法者變成一個叛逃的反抗者。
蒙塔格是整個故事的串聯者、發問者,他的角色功能是帶着讀者去挖掘雷所創造的世界的真相。而我在本文想讨論的是書中的三個配角:蒙塔格的妻子米爾德裡德和消防隊長比提,以及教授費伯。這三個角色作為小說中的“工具人”,除了推動蒙塔格走向變革之外,他們還依次代表了三種階層——平民、底層管理者以及知識分子,在“反智主義”的強壓下,表露出來的人性本能的掙紮。他們的表現恰是如我們一般的普通人在壓力下常常采取的三種處世态度——逃避、壓抑和僞裝。
<h1 class="pgc-h-arrow-right">米爾德裡德 - 逃避,表面的快樂掩蓋不住内心的空虛</h1>
蒙塔格的妻子米爾德裡德代表着整個平民階層的日常生活狀态。他們用電視牆、開快車或者逛遊樂園打發時間。米爾德裡德在家裡也總是帶着一副海貝耳機,裡面不停地灌入音樂和談話。這個習慣,讓米爾德裡德練了一手讀唇語的好本事,和蒙塔格的交談要用上眼睛才行。
每家每戶都有電視間,米爾德裡德已經把電視間的三面牆都換成了電視牆,還在說服蒙塔格購買第四面。一有閑暇,米爾德裡德就泡在電視間裡,甚至和主婦們的社交也是在自己家或者别人家的電視間裡進行。大家坐在一起就是不停地讨論播過的節目劇情,稱電視裡的人為“親戚們”。
“親戚”的戲稱,反映了人們對真實世界中交際情感的淡漠。智能産品和商業生産的内容替代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需求。米爾德裡德泡在電視間,每時每刻地戴着海貝,其實是一種逃避,是對精神生活的舍棄。用破碎的、新鮮的事物不斷地填充、占據自己的思想,避免了自己的頭腦有空閑去産生思考的運轉。久而久之,思考的習慣就從生命中被剔除出去,記憶也失去了效力。米爾德裡德連4天前的事情也記不住。
這一現象割裂了人性當中的情感維系與歸屬,夫妻之間的感情名存實亡,鄰裡之間更不會建立友情,社會氛圍越來越冷漠。他們十分信服并且順從統治者的管制,表面上看起來十分快樂。
為什麼是表面的快樂呢?因為米爾德裡德試圖吞藥自殺。
蒙塔格發現米爾德裡德吃了過量的安眠藥,急忙撥打急救電話。上門的是兩個操作工,帶着兩種急救儀器,一種探入胃部吸收殘留的藥物,一種抽換血液。兩個操作工就像擺弄一具屍體一樣救治米爾德裡德,并且帶着滿不在乎的口吻說一個晚上要接九、十件自殺報案。第二天,清醒的米爾德裡德還以為是前天夜裡在派對宿醉,完全想不起來自己吞了一整瓶安眠藥。
這個情節可以延伸出兩種猜想,一種是人們自殺後,被操作工的儀器影響,忘記了前一天的行為,另一種猜想是這種大量吞服安眠藥的做法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人們的精神空虛到嚴重影響了睡眠,于是反複吞服藥物挽救睡眠。但不管是哪一種猜想成立,作者雷都通過這個細節向讀者展現了,快樂過後,人們普遍表現出焦躁不安的情緒壓力。
<h1 class="pgc-h-arrow-right">比提 - 壓抑,看似強壯的虎皮下是一具即将倒塌的枯骨</h1>
作為蒙塔格的隊長,比提代表的是最底層的管理者。他一面知曉曆史,一面維護着“反智主義”的統治。
蒙塔格對消防員焚燒書籍的意義産生了懷疑,想要請假逃班,比提嗅到了異常,上門對蒙塔格進行開導。比提作為勸導者,顯然已經身經百戰。他娴熟地向蒙塔格介紹消防員的起源。毀滅書籍的事業本來并不容易,但從電影、收音機、電視被發明出來開始,一切就變得簡單了。書逐漸變得小衆,資訊、知識的品質也在不斷下降。生活的樂子越來越多,頭腦的思考越來越少。“知識分子”成了少數族群,變成了罵人的字眼。為了維持大衆平等的心願,為了讓無知的大衆繼續沉浸在享樂當中,于是消防員們成為城市的維護者,焚燒書籍,清除具有求知欲的異類。
比提款款而談,甚至能夠引經據典,用知識攻擊知識。照常理,他該是個徹頭徹尾的統治者的走狗,但雷的創作妙就妙在,比提也在掙紮。他掙紮的方式是壓抑,不僅用花哨的言語和環環相扣的邏輯壓抑着蒙塔格的求知欲,其實也在壓抑着自己。直到當蒙塔格拿着噴火器,打開保險栓對着自己,他仍然帶着取笑、嘲諷,不停地激怒蒙塔格,迫使對方燒死自己。比提活夠了,他了解知識,卻在強權的壓迫下做着一份毀滅知識的工作,導緻身心疲憊。他一直用一種麻木自己也麻木别人的方式,回避尋找真理和追求精神生活,為自己和強權找了一個看似正當的理由——維護人們的快樂,驅除異類——支撐着消防員職業的行為動機。
<h1 class="pgc-h-arrow-right">費伯 - 僞裝,小心翼翼地适應着怪異的世界</h1>
費伯是一位退休的英文教授。蒙塔格第一次遇見他,他正往懷裡藏一本書。費伯見到消防員害怕極了,第一反應就是準備逃跑。蒙塔格第二次打電話找他,一提到書籍,費伯就緊張得急忙否認,認為蒙塔格的問題是陷阱,要落實他的罪名。他的敏感是在被強權的威懾下形成的。藏書的人不是随着房屋被燒死,就是被送進精神病院,作為一位曾經的教授,費伯怎麼可能不敏感,不害怕。
他是雷的世界裡被“反智主義”針對的少數群體“知識分子”。作為被排擠的人群之一,費伯生活得小心翼翼,他深谙城市中潛伏的各種危機,對每一個人都不信任。但他知道怎樣隐藏自己對知識的欲望,表現得像個“正常人”,僞裝自己融入身邊的群眾。他勸阻蒙塔格在主婦們面前讀詩,極力幫助蒙塔格在隊長面前保持鎮定,但還是沒攔住蒙塔格憑着本心進行了反抗。當一切無法挽回時,他真誠地幫助蒙塔格,為他指引出路,自己則逃去了另一個城市。
費伯的僞裝是為了能在夾縫中謀求生存。他是蒙塔格意識覺醒路上的引導人。費伯什麼都明白,但什麼都不敢說。因為他知道蚍蜉難以撼動大樹,是以隻能選擇默默地把自己潛藏起來。
<h1 class="pgc-h-arrow-right">《華氏451》與現實的關聯和啟示</h1>
雖然《華氏451》中描述的世界與如今的社會形态不完全一樣,但“反智主義”在美國依然嚴重,甚至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也漸漸顯露出來。
便攜智能裝置雖然拉近了大千世界當中人與人相遇的距離,但也将人們的社交注意力從線下轉移到線上。我們是不是逐漸忽視了與親人、朋友放下手機面對面交談的交往方式?而網絡對人們真實身份的隐藏,也讓大衆敢于公開抨擊真知和權威。“知識分子”呢,則抱着君子不與小人争辯的态度閉口不言。這不就是雷筆下的艾爾德裡德、比提以及費伯三個角色在書中的表現嗎?那麼在我們這些表現的背後,是不是也有所掙紮?
“反智主義”已然彰顯出它的威力,而我們很多人卻未曾察覺,甚至以無知為榮,還有那麼多人在說“讀書無用”。書籍承載了曆史中一部分人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而有沒有用則取決于讀者的思考和行動。樂觀的是求知也是人的一種本能。有人推崇“反智主義”,但也依然有人尊重真理與科學。有人沉浸享樂,但也依然有人享受學習和求知的過程。雖然生活中沒有強權壓迫着我們,但我們需要開始警惕“反智主義”的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