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快報訊(記者 陳曦)8月15日是“二戰”日本戰敗投降日,也是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曆史上意義最重大的節點之一。在抗戰勝利76年後,那一段浸滿血淚的曆史,和那一天的辛酸與榮光,依然在今天回響。近日,由南京大學大學生院專項支援,外國語學院德語系牽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學教席、南京大學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德國費希塔大學與海德堡大學的共同支援下,“拉貝日記與和平城市”國際雲科考項目正式啟動。來自南京大學14個專業/大類的36名大學生圍繞《拉貝日記》開展跨文化、跨學科、多元度的研究,進行文獻研讀、實地考察、線上線下訪談,深化對世界和平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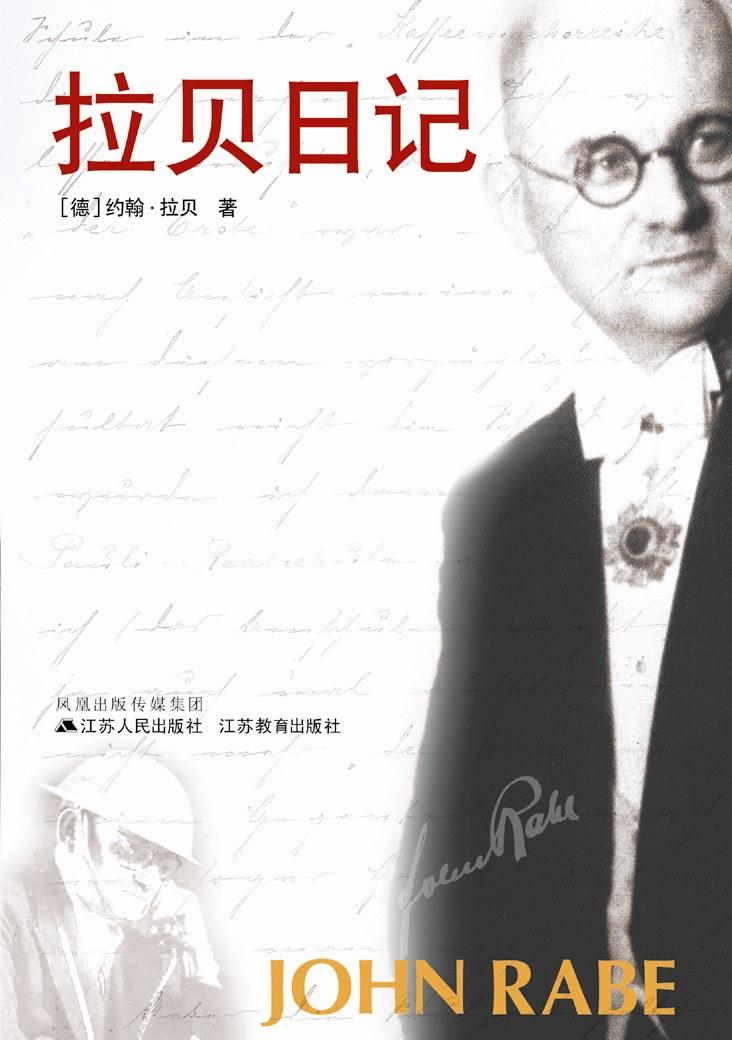
△《拉貝日記》首個中文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1937年南京大屠殺期間,德國西門子洋行代理人、納粹黨員約翰·拉貝在南京和國際友人一道建立國際安全區,拯救了25萬中國人的生命。回到德國後,約翰·拉貝遭到納粹迫害,被迫在此話題上保持沉默,因而後人對約翰·拉貝的了解及研究十分有限。《拉貝日記》正是約翰·拉貝在戰争期間冒着生命危險寫成的,但它卻一直躺在拉貝兒子住的閣樓裡幾十年,直到60年後的1997年才公布于世。它所記述的,都是拉貝的親曆親見親聞,非常具體、細緻和真實,無人能否定其可信度。它是對侵華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的血淚控訴,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所犯罪行的有力證詞。因為《拉貝日記》的重見天日,使得南京大屠殺曆史事件重新回到國際社會的視線,成為“二戰”曆史中不容忽視的重要部分。是以,《拉貝日記》的發現、譯介與傳播過程,具有重要的曆史研究價值和教育價值。
中國重新發現約翰·拉貝的第一人,是畢業于南京大學曆史系的黃慧英。1988年,在南京市檔案館工作的黃慧英發現了約翰·拉貝的檔案。從一段短短幾十字的關于成立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簡訊開始,她先後完成了國内首先披露約翰·拉貝生平的文章《南京淪陷期間一位德國友人拉比》《南京大屠殺中的庇護神》,并于2002年出版圖書《南京大屠殺的見證人:拉貝傳》。她在接受國際雲科考項目組采訪時表示,“自己發表的文章裡所見不多的史料,實則也收集了好幾年”,不過,曆史學者的使命感和拉貝的人格魅力支撐着她克服萬難完成了考證研究。
《拉貝日記》寫于南京,而《拉貝日記》的發現卻在海外,其得以公開,與已故曆史學者張純如的努力密不可分。1995年,張純如準備寫一本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書,來到南京搜集資料。在得知拉貝的資訊後,她寫信給德國《漢堡晚報》,請求尋找拉貝或其家屬的下落,希望擷取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資料。她輾轉聯系上拉貝外孫女萊茵哈特夫人,得知拉貝日記還儲存在拉貝家屬手中,便希望能将日記公布于世。
約翰·拉貝曾外孫克裡斯托弗·萊因哈特線上上接受項目組采訪時,披露了張純如和母親萊茵哈特夫人溝通出版的過程:“1996年張純如聯系我母親時,母親對出版《拉貝日記》感到擔憂,她覺得當年約翰·拉貝對德國政府許下的誓言是一種限制。與母親讨論之後,張純如認為拉貝家族幾十年的沉默已經兌現了誓言,世界對了解真相的關注顯然超過了個人利益。”
克裡斯托弗·萊因哈特很感激也很高興母親作出了公開日記的決定。他對項目組說,自己兒時就曾偷偷翻閱過曾外祖父的日記,“雖然曾外祖父在我出生前14年就去世了,但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幽默、熱夫妻類的人。”“正是這種人道主義本性讓他能夠在至暗時刻作出正确決定,為了‘他的中國人’留在南京”。
1996年《拉貝日記》公開後,國内出版界即着手将這一重大曆史發現翻譯引進到國内。為了解《拉貝日記》中文版的譯介出版過程,項目組分别采訪了編者和譯者。
△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輯汪意雲接受項目組通路
△《拉貝日記(影印版)》
1997年《拉貝日記》中文版出版的時候,汪意雲已經進入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輯部工作,她雖未直接參與第一版的出版,卻對當時全社為《拉貝日記》的誕生做出的努力記憶猶新。她向項目組介紹,1996年12月,《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五六篇報道,介紹拉貝外孫女萊茵哈特女士在紐約公開家族儲存的拉貝日記原件的新聞。身為黨媒的責任感和地處南京的使命感,使得江蘇人民出版社認識到出版《拉貝日記》意義重大、勢在必行。但由于當時交通、通訊不便,财力難以獨立支撐,跨洋交流的過程困難重重,蘇人社最終通過和江蘇教育出版社合作,在中國大使館的幫助下,才成功與拉貝之孫托馬斯·拉貝取得了聯系,并購得了日記版權。之後在南京大學德語系多位老師組成的翻譯組的幫助下,于南京大屠殺60周年祭前夕,也就是1997年12月,完成了《拉貝日記》首個中文版的出版。20年後,汪意雲也完成了“從旁觀者到參與者”身份的轉變,成為了《拉貝日記(影印版)》總責任編輯。
△拉貝的孫子托馬斯·拉貝(右二)
據譯者之一劉海甯講述,《拉貝日記》是他所有翻譯任務當中持續時間最長、介入最深、考證最多、記憶最深的一項。由于《拉貝日記》文本具有特殊的嚴謹性和史學參考價值,對譯文的客觀性要求極高。譯者了解到許多大屠殺細節之後,會不可避免地情緒化,如何在譯文中處理好個人情感,成了翻譯工作中的難題。
采訪調查中,項目組成員們深感三十多年前的故事依然生動,時常讓他們産生“曆史總是彼此相連”之感。“就像前輩所做的那樣,我們也在回溯、寫就曆史。如果未來有人也想了解《拉貝日記》,或許可以從中找到素材,加以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