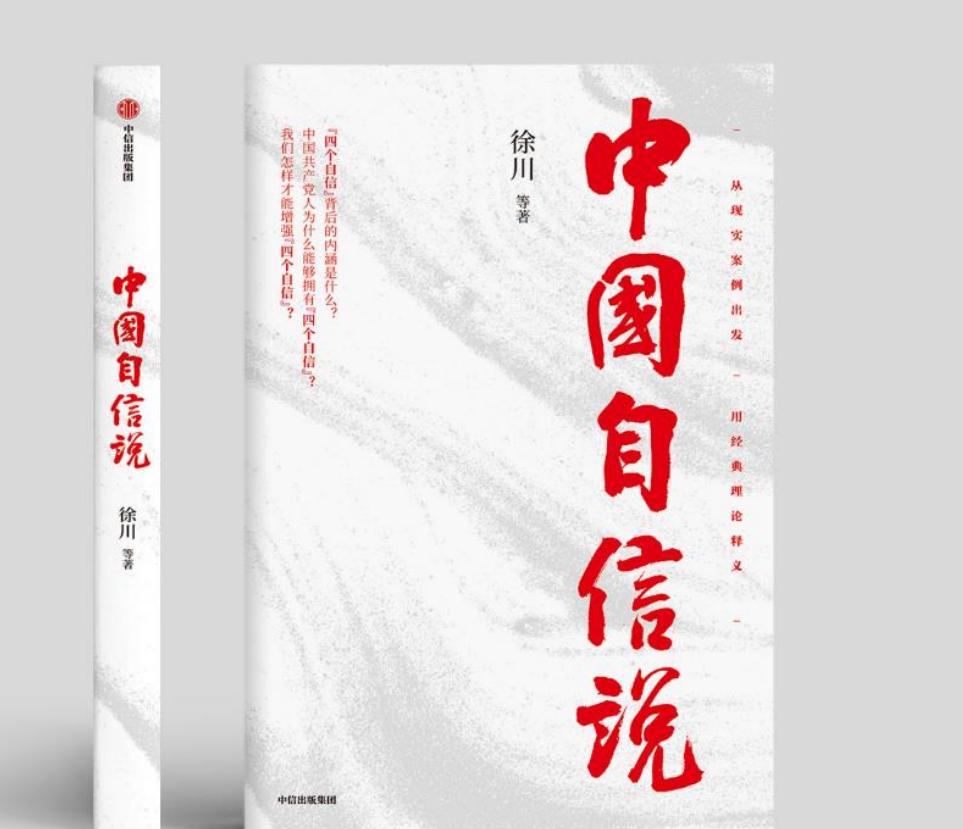
曆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曾感慨,中國在1405—1433年進行了七次遠航,規模、範圍遠超一個世紀之後的哥倫布、麥哲倫和達·伽馬等人,假如中國人像歐洲人那樣,搞出來一個地理大發現,那麼世界将是另外一個樣子。不難看出,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與資本主義邏輯中的殖民擴張有着根本不同。
“修昔底德陷阱”:西方的話語陷阱
什麼是“修昔底德陷阱”?實際上,它和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沒有直接的關聯,其提出者是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艾利森為了給21世紀的中美關系定性,根據修昔底德對當年“雅典實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這一曆史事件的描述,人為杜撰出了一個“一山不容二虎”的“修昔底德陷阱”。在艾利森看來,現存大國面對新崛起大國的挑戰,勢必會采取某些措施消除潛在的威脅,以保持自身大國地位不動搖,這将造成戰争的不可避免性。曆史中也确實存在古雅典與斯巴達之戰、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争、德國發動世界大戰的例子。之後“修昔底德陷阱”一詞便常常出現在分析中美關系的文章中。
2015年,艾利森來到清華大學,做了題為“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演講,“修昔底德陷阱”得到中國知識界和媒體界的普遍關注。2017年,艾利森出版了他的新書《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系統回顧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至今世界體系中的大國争霸。他的研究團隊認為,在世界上主要的16個崛起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案例中,有12次都發生了戰争,落入了這個“陷阱”。
崛起的中國與守成的美國及其盟國之間的關系困境,會不會引發“修昔底德陷阱”呢?
習近平主席在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的演講中說道:“我們要堅持以事實為依據,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鄰盜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鏡觀察對方。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實際上,“修昔底德陷阱”盡管在以西方為中心的近現代國際體系中能夠得到部分印證,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已經不适用了。美國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梳理了1500年以來的世界經濟變遷和軍事沖突,發現其間大國之間發生的戰争就遠遠超過16個。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各種國際沖突和地區戰亂依舊存在,但大國之間再也沒有爆發戰争。
如此看來,“修昔底德陷阱”代表了西方少數國家的一種成見。他們認定,中國的崛起會挑戰少數西方國家的霸權,全球性沖突是以将不可避免,其充其量隻是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術推論或猜想,要知道,“修昔底德陷阱”可被看作一種曆史現象,但它絕不是基于推論和猜想的曆史規律。在國際舞台上,少數西方國家非常善于使用“話語陷阱”來進行輿論打壓和攻擊,也就是把自身的價值觀包裝在一個看似中性的議題、理論或者概念裡,形成一種隐藏在強勢話語背後的陷阱或者圈套。
我們可以這樣還原“修昔底德陷阱”作為話語陷阱的本質:“修昔底德陷阱”在形式上是做古今對比,在方法上并不是根據曆史檢視現實,而是為心中早有定見的現實判斷套上了一層古典的外衣,使其成為一種僞經典概念。修昔底德本人的思想是國際關系和曆史研究的重要對象,這些研究并不容易為大衆所熟知,而經過精心包裝的“修昔底德陷阱”,則将兩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和古希臘曆史進行了簡單化、抽象化,實際上隻是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現代概念借來一個具有曆史感的名稱而已。這種包裝的迷惑性在于,容易讓不熟谙曆史的普通群眾和政治精英認為“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對曆史規律的總結,中美關系也将是這種邏輯的延續。
2014年1月,《世界郵報》創刊号刊登了對習近平主席的專訪。針對一些人對中國迅速崛起後必将與美國發生沖突的擔憂,習近平指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隻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适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各國經濟聯結空前緊密,現代國際關系完全是一幅全新的圖景,我們有條件、有能力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金德爾伯格陷阱”:西方的政策陷阱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
美國著名世界經濟史學家查爾斯·P. 金德爾伯格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災難起源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大強權,但又未能像英國一樣承擔起為全球提供公共産品的責任。美國盡管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未能接替英國扮演的角色,結果導緻了全球經濟體系陷入衰退、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對于全球化而言,就缺少了全球公共産品的提供者。
2017年1月,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他認為:中國崛起以後的動向可能不是“示強”,而是“示弱”,即不願承擔目前美國無力負責的重要國際公共産品的供給,進而使世界陷入上司力空缺、危機四起的險境。
如果說“修昔底德陷阱”說的是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是否會發生戰争的問題,那麼“金德爾伯格陷阱”指的則是新興大國能否提供公共産品治理全球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作為全球頭号強國的美國近幾年瘋狂“退群”。美國先是退出了 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留下日本等一群小夥伴目瞪口呆;接着又退出了《巴黎協定》,讓歐洲氣憤不已;繼而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賴賬5億美元,這種做法空前絕後;然後又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最注重人權的國家不想提人權了;美國退出萬國郵政聯盟的理由也令人匪夷所思;美國還退出了伊朗核協定;退出了中導條約,歐洲、亞太和拉美等地區的戰略穩定受到巨大挑戰;然後,美國退出了世界衛生組織……未來何去何從還需要邊走邊看。
與此同時,中國深入展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戰略,積極營造良好的外交關系,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例如,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周邊國家開展各類合作高峰論壇、亞太經合組織上司人非正式會議等。中國還倡導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
很顯然,中國一方面秉持“韬光養晦”,同時尋求“有所作為”。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方式依然是“決不當頭”,倡導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觀。
中國的崛起是一種從參與式崛起到融入式崛起最後到建設性崛起的程序。也就是說,中國不是通過戰争的方式,颠覆既有國際體系來崛起的,而是通過經濟上的對外開放,逐漸融入既有國際體系之中的,既有的國際體系為中國崛起提供了可持續性和制度性的收益。是以,維護和建設好既有的國際體系,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
在應對“金德爾伯格陷阱”方面,中國擔起了大國責任,展現了大國擔當。習近平主席在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視訊會議開幕式上緻辭時,提出了中國推進全球抗疫合作五大舉措:中國将在兩年内提供20億美元國際援助,用于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國家特别是開發中國家抗疫鬥争以及經濟社會恢複發展;中國将同聯合國合作,在華設立全球人道主義應急倉庫和樞紐,努力確定抗疫物資供應鍊,并建立運輸和清關綠色通道;中國将建立30個中非對口醫院合作機制,加快建設非洲疾控中心總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中國新冠疫苗研發完成并投入使用後,将作為全球公共産品,為實作疫苗在開發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擔負性做出中國貢獻;中國将同二十國集團成員一道落實“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并願同國際社會一道,加大對疫情特别重、壓力特别大的國家的支援力度,幫助其克服目前困難。
由此可見,中國崛起是負責任的崛起,中國的崛起并沒有導緻國際公共産品的缺失,隻是對既有的國際公共産品進行改革和創新,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世界需要全新的國際公共産品。中國正是全新國際公共産品的提供者,這充分展現了中國的世界責任!
(本文節選自《中國自信說》)
《中國自信說》
徐 川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本書從現實問題出發,以活潑生動的語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做了深入詳細的闡述。全書分為四個篇章,詳盡分析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背後的邏輯。本書為讀者解答了:“四個自信”背後的内涵是什麼?中國共産黨人為什麼能夠擁有“四個自信”?我們怎樣才能增強“四個自信”?本書為我們積極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理論大衆化的新樣闆。
作者徐川,黨的十九大代表,江蘇團省委兼職副書記,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現為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江蘇省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
作者:徐川
編輯:金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