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是由胡喬木先生創意督導,胡繩先生擔綱主編,集中共曆史研究諸學者名家之力而成,既有高度權威性又有一定普及性的黨史讀本,并以其“陳言大去,新意疊見”,不僅在當時引起廣泛的關注和好評,而且一印再印,即便是在20多年過去之後的今天,也仍然是廣大讀者願讀愛讀的黨史讀本。
在當下時興的網絡空間“豆瓣讀書”中,這本書被給出了近8分的高評價,其中有個評價說:這是目前最好的黨史,注意,不是之一。可見這本書的影響力并不因時間的流逝而消失,這也是一本優秀的曆史著作通常所應具有的品格。
在《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出版幾十餘年後的今天,由這本書的主要作者之一金沖及先生根據當年筆記記錄整理出版的《一本書的曆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披露了在這本書的編寫過程中胡喬木的多次談話概要,尤其是他對于中共黨史編寫方針和曆史評價方面的諸多看法,極具啟示意義。
如金沖及先生所言:胡喬木“始終極為關心這本書的寫作”;他“是公認的中共黨史研究的大師。他們是黨的曆史中許多重要事件的親曆者,又長期上司黨史研究工作,有着很高的理論思維能力,在随便談話中也往往能對黨史說出一些常人沒有想到的重要看法,可以啟發人們去思考。”
那麼,胡喬木對于《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的寫作,究竟起到了怎樣重要的作用呢?
作為資深政治家,又是中共黨史研究最初的開拓者,胡喬木對于《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寫作的關注,更多地表現在那些提綱挈領、要言不煩的指導性言論中,其中他着重強調、反複強調的就是“新意”。
諸如:“要使人看了覺得有新意”;“要走出一條新的路子”;“一定要有新的,過去沒有着重講述的,甚至忽略的,而現在需要解釋、說明、強調的内容。”
關于“新意”,他還有較長的一段言說:“老說那些說過多少遍的話,讀者不會有興趣,我們也沒有興趣。我們在觀察曆史,曆史需要不斷重新觀察,每次觀察要有新的内容。曆史是非常豐富的,可以從許多角度來觀察。人們的思想也不會像我們現在想的那麼簡單的幾條。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想法。社會生活是複雜的,要宣傳黨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實說出些新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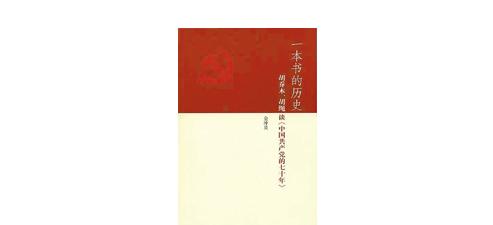
《一本書的曆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金沖及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胡喬木強調中共黨史的研究要有“新意”,看似科學研究的常識,其實細究起來,還真不是那樣簡單。中共黨史研究,可以說是主流學科,但是,黨史研究的定位,因為種種曆史的、現實的、政治的、其它的原因,又未必是那麼明确的。
不少黨史研究者,習慣于從黨的決議和檔案出發诠釋黨的曆史,結果便使得一些黨史論著,或者是陳陳相因,了無新意,或者是朝三暮四,應時而變,也就成了胡喬木所言,不要說“讀者不會有興趣”,就連黨史研究者包括胡喬木這樣的黨史研究上司者“也沒有興趣”。于此可知,胡喬木對于作為科學的曆史研究的本質不能不說是了然于胸的。
既然如此,那什麼才是胡喬木心目中的黨史“新意”呢?
胡喬木在有關《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的寫作談話中,在認清黨史工作戰鬥性的前提下,特别強調的是,“要加強黨史工作的科學性”;提出“我們需要用科學的态度,科學的方法,科學的論證,來闡明有關我們黨的曆史各種根本的問題”。
是以,在他對黨史的評價,尤其是對1949年以後黨史的評價中,那些被認為是不太好寫,有些“敏感”的問題,胡喬木卻并不避諱,直白道來,言談确實頗具“新意”。
例如,他明确提出,“‘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氣來講,這是人為的高潮”;“如果這可以肯定,曆史就是任意的。”“1957年以前,毛主席工作裡的任意性、工作指導中的任意性,已經表現出來了。講集體上司,很難說。”這樣的認識,與那些墨守成規之見相比,應該說确有其高明之處。
胡喬木對于黨史“新意”的了解,更多地可以從他對“極左”思潮和“文革”的态度反映出來。在有關《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寫作的談話中,胡喬木對“極左”思潮和“文革”持強烈的否定立場和批判态度。他認為,中共曆史中“左”的傾向具有“曆史的、盲目的慣性”,“對20年的‘左傾’要認真批評”。在這樣的認識指導下,胡喬木親自動筆,對這本書的初稿提出了不少頗具意義的修改意見。
例如,書中原稿有這樣的表述:“文革”造成更加廣泛的階級鬥争擴大化的迷霧。胡喬木批注說:“文革”不能稱為階級鬥争擴大化,因為這鬥争本身是捏造出來的。書稿據此修改為:“文革”造成到處都有階級鬥争的緊張空氣。
書稿中另一處的表述是:“文革”不是不可避免的。胡喬木認為:這樣的表述“太軟弱了,應該說這是完全錯誤的”。他特别強調說:“錯誤是深刻的,就要深刻地寫,不要讓讀者感到我們在維護,不敢接觸。”是以,胡繩認為,胡喬木“貫穿在這些修改意見中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聯系到那個特定的年代,不能不說,胡喬木對黨史要去陳言、有新意的突出強調,對于這本書的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胡喬木對于黨史研究“新意”的了解,不僅表現在寫作指導思想和具體内容方面,也包括對于寫作方法甚而是文字表達的重視。
他提出,寫書的思路和條理要清楚,不能“吞吞吐吐,躲躲閃閃”;“不能像講課那樣,講一堂,灌一堂”。通俗地說,就是論著作者的觀點和看法要明确,但是,觀點和看法的表達要留有餘地,給讀者留下思考的空間。“避免一種硬邦邦的強逼人接受的感覺”;“要寫得讓那些對黨史沒有多少興趣的普通讀者,讀了也有所收獲”;“使得黨史不拒人于千裡之外。你可以不是共産主義者,照樣可以看得津津有味。”
胡喬木身體力行,他為《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所寫的題記,簡潔利落,流暢可讀,很不像是我們慣常所見的那些正襟危坐的皇皇之作,充分表達了他的這種寫作态度。是以,著名的文史大家錢鐘書先生稱胡喬木的這篇《題記》寫得“思維缜密,詞章考究”。
胡喬木先生是革命家和政治家,然而,從他的黨史研究談話中,我們也可以領會他所具有的學者或文人的深厚底色以及他以曆史過來人身份的深入思考,這或許也是他作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司者的成功之處。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原載于北京日報2014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