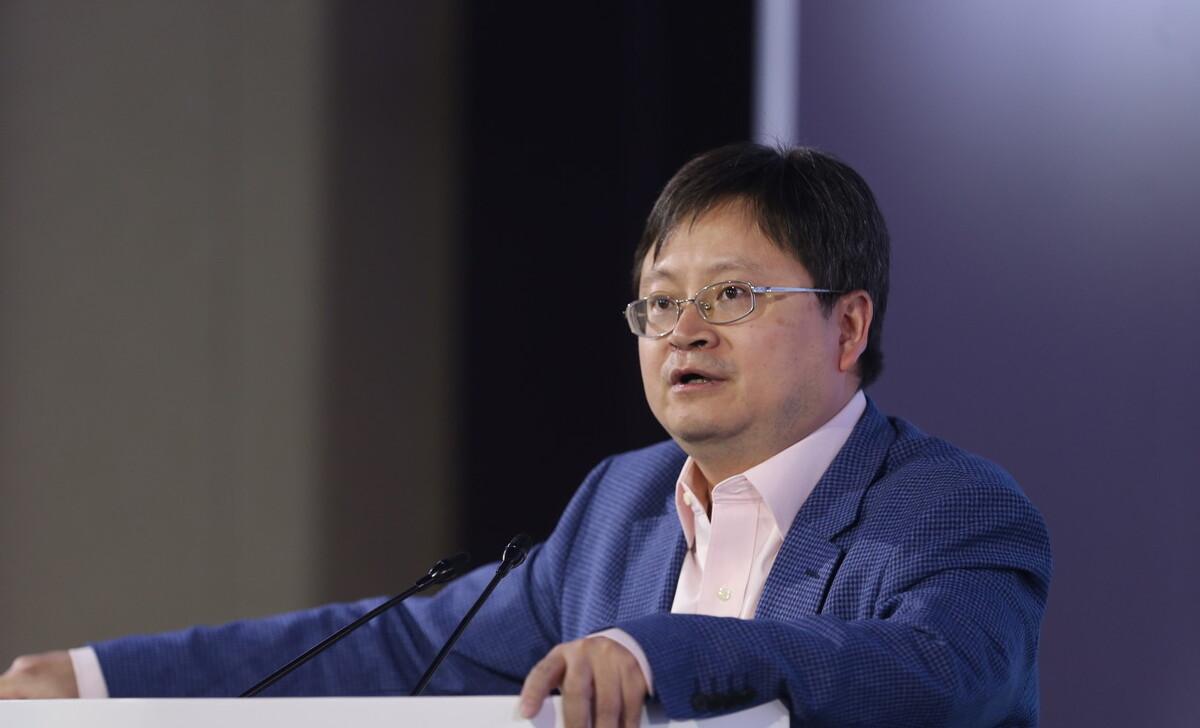
意見領袖丨管濤 劉立品
摘 要
二季度,我國國際收支繼續呈現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的平衡格局,人民币升值的估值效應推升對外金融負債,短期外債增加但風險總體可控,預計美聯儲Taper對中國對外經濟部門影響有限。
二季度,經常項目順差環比繼續減少,占GDP比重仍位于合理區間,其中貨物貿易順差變化較小,服務貿易逆差、初次收入逆差有所擴大。
二季度,資本項目逆差明顯收窄是其,主因他投資由逆差轉為順差;淨誤差與遺漏再次轉為負值,剔除該項後的線上資本項目為順差。
二季度,基礎收支順差帶動儲備資産增加,短期資本逆差占基礎國際收支順差之比較一季度有所回落,顯示一季度美債收益率飙升引發的“縮減恐慌”影響有所緩解。
截至6月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産和負債雙增加,對外淨資産減少,主要受非交易因素影響。其中,人民币升值的估值效應貢獻了同期非交易因素引起的對外負債增幅的八成以上。
二季度,我國對外投資收益率和利用外資成本率環比變動較小,但均較去年一季度明顯上升,主要原因在于,對外金融資産中的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占比提高,反映境内外彙流動性較為充裕,境内主體資産多元化配置需求增加;對外金融負債中的證券投資占比提高,反映出疫情暴發之後中國經濟率先恢複,人民币資産收益較好。
二季度,我國外債餘額有所增加。從期限結構來看,短期外債為主要貢獻項;短期外債占外匯存底比例上升,繼續創1994年以來新高,但仍然低于100%的國際警戒線,表明外債償付能力仍然充足。從币種結構來看,外币和本币外債對外債餘額增幅的貢獻率大體相當,人民币升值的估值效應貢獻了本币外債餘額增幅的23%。
二季度,民間部門對外淨負債規模進一步增加,但非交易調整正貢獻69%。考慮到目前民間部門貨币錯配已有明顯改善,市場對于匯率波動的容忍度和适應性明顯提高,預計美聯儲Taper對中國對外經濟部門影響有限。
正文
9月30日,國家外彙管理局公布了2021年二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正式數和2021年6月末國際投資頭寸表。結合現有資料對二季度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分析如下。
經常項目順差繼續收窄,主因是服務貿易和初次收入逆差擴大
二季度,我國國際收支繼續呈現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的自主平衡格局。其中,經常項目順差533億美元,資本項目(含淨誤差與遺漏)逆差33億美元(以下如非特指,資本項目差額均包括淨誤差與遺漏項),外匯存底資産增加499億美元(見圖表1)。
經常項目順差環比繼續減少,占GDP比重仍位于合理區間。二季度,經常項目順差533億美元,延續一季度回落态勢(見圖表2)。從支出法看,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正趨于減弱。二季度,經常項目差額占當季名義GDP的比重為1.2%,環比回落0.6個百分點;年化經常項目差額占年化名義GDP的比重為2.1%,環比回落0.4個百分點;二者仍位于±4%的合理區間,表明人民币匯率處于均衡合理水準(見圖表3)。
貨物貿易順差環比變化較小,進出口增長驅動因素不同。二季度,國際收支口徑的貨物貿易順差1195億美元,環比僅增加8億美元。其中,貨物出口7622億美元,環比增長9.8%,同比增長26.8%;貨物進口6427億美元,環比增長11.7%,同比增長43.6%(見圖表4)。根據海關總署公布的進出口價格指數和數量指數,我們可以計算數量和價格變動對進出口價值同比增長的貢獻率。結果顯示,二季度,出口數量和價格對出口額增長的貢獻率均值分别為108%、-8%,反映出口主要受益于海外需求恢複、出口訂單轉移紅利延續的影響;但二季度進口數量和價格對進口額增長的貢獻率均值分别為-106%、206%,反映進口主要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影響(見圖表5)。
服務貿易逆差環比有所擴大,運輸服務是主要貢獻項。二季度,服務貿易逆差283億美元,環比增加61億美元。其中,旅行逆差202億美元,環比減少40億美元(旅行支出減少36億美元),已經連續3個季度減少,創2014年以來新低,主因是4月份以來Delta病毒變異導緻全球(不含中國)新增确診病例明顯增加,對居民境外出行構成進一步限制(見圖表6、7)。當季,運輸服務逆差102億美元,環比增加67億美元,是服務貿易逆差擴大的主要原因,運輸收入和支出分别為261、363億美元,均創資料公布以來新高,可能反映了國際運輸費用上漲的影響(見圖表7、8)。
初次收入逆差環比有所擴大,主因是投資收益逆差擴大。二季度,初次收入逆差422億美元,環比增加128億美元。其中,雇員報酬和其他初次收入差額變化較小,環比分别僅增加了9.8億、5.7億美元;投資收益逆差由一季度286億美元擴大至430億美元,貢獻了初次收入逆差增加額的112%(見圖表9)。二季度,對外投資收益和外來投資收益分别為837億、1267億美元,均創資料公布以來新高(見圖表10)。
資本項目逆差明顯收窄,其他投資轉為順差是主要貢獻項
資本項目逆差明顯收窄,線上資本項目轉為順差。二季度,資本項目(含淨誤差與遺漏)逆差33億美元,環比減少311億美元(見圖表11);剔除淨誤差與遺漏後的非儲備性質的資本項目(即線上資本項目)順差633億美元,意味着二季度經常項目和線上資本項目為“雙順差”。這是2018年以來第4次出現“雙順差”情況,前三次分别是2018年三季度和2019年一、四季度(見圖表12)。
直接投資順差收窄,證券投資順差擴大。二季度,直接投資順差456億美元,環比減少301億美元。其中,對外直接投資增加119億美元,外來直接投資減少182億美元,均屬于季節性波動,符合曆史規律,并且一、二季度外來直接投資規模顯著高于往年,反映外資企業對于中國經濟繼續抱有信心(見圖表13)。當季,證券投資順差162億美元,環比增加127億美元,但增幅小于直接投資順差收窄幅度。其中,對外證券投資減少447億美元(其中股權投資減少469億美元,債券投資增加22億美元),主要反映了港股回調、港股通買入成交淨額減少的影響;外來證券投資減少320億美元(其中股權投資增加184億美元,債券投資減少504億美元[1]),反映中國股市流入資金依然強勁,但債市對于外資的吸引力減弱(見圖表14)。
外資淨增持人民币債券趨緩,主要與境内外利差繼續收窄有關。二季度,日均10年期中美國債收益率差154個基點,在上季環比回落50個基點的基礎上進一步縮小了33個基點(見圖表15);境外投資者通過債券通淨增持境内人民币債券1855億元,在上季環比減少109億元的基礎上進一步下降了1179億元(見圖表16)。
其他投資轉為順差,與對外貨币和存款、貸款淨流出(即資産淨獲得)減少有關。二季度,其他投資由上季度逆差1155億美元轉為順差17億美元,是資本項目逆差收窄的主要原因。其中,貨币和存款由逆差305億美元轉為順差244億美元(其中對外貨币和存款淨流出減少498億美元),貸款逆差從825億美元收窄至219億美元(其中對外貸款淨流出減少538億美元),又是其他投資差額變化的主要貢獻項(見圖表17)。我國對外貨币和存款、貸款淨流出環比變動方向與同期銀行對外金融資産中的存貸款餘額環比變動方向一緻,主要是經常項目順差收窄使得境内外彙流動性均衡性改善(見圖表18)。此外,其他投資中的貿易信貸資産方和負債方也發生明顯變化:資産方由一季度淨流入122億美元轉為淨流出163億美元,負債方由一季度淨流出28億美元轉為淨流入172億美元,主要反映了出口/進口規模環比增加導緻出口應收/進口應付環比增加的結果(見圖表19)。
淨誤差與遺漏再次轉負,占進出口比重仍然合理。二季度,淨誤差與遺漏額由上季度的+1億美元轉為-666億美元。這與同期貿易順收順差缺口擴大有關:二季度,海關可比口徑的銀行代客涉外貨物貿易收付順差630億美元,較海關統計的貨物貿易進出口順差1377億美元少了747億美元,而一季度貨物貿易隻少收了133億美元;貿易順收順差負缺口占海關統計的進出口總額比例為-5.0%,一季度僅為-1.0%(見圖表20)。雖然淨誤差與遺漏項負值較大,但其占當季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國際收支口徑,下同)比例為-4.7%,年化淨誤差與遺漏額占年化進出口額比重為-4.0%,自2018年二季度以來持續在±5%的合理标準以内(見圖表21)。
基礎收支順差帶動儲備資産增加,一季度“縮減恐慌”影響緩解
基礎收支順差帶動儲備資産增加,短期資本逆差收窄。二季度,交易引起的儲備資産增加500億美元。其中,短期資本(含淨誤差與遺漏)逆差489億美元,基礎國際收支順差989億美元,後者是儲備資産增加的主要原因。短期資本逆差占基礎國際收支順差之比為-49%,而一季度為-76%(見圖表22)。
外匯存底餘額增加主要由交易引起,非交易因素影響較小。截至2021年6月末,央行統計的外匯存底餘額為3.2萬億美元,較3月末增加440億美元。同期,交易引起的外匯存底資産增加499億美元,二者內插補點為-59億美元,代表匯率和資産價格等非交易因素引起的外匯存底價值變動(詳見《二季度國際收支分析報告:貨物貿易順差減少,短期資本流動沖擊減弱》2021年8月8日)。
外彙占款環比增加,但增幅遠小于銀行結售彙順差。二季度,外彙占款增加577億元,折合89億美元,遠小于同期銀行即遠期(含期權)結售彙順差603億美元。2017年以來,央行基本退出外彙市場常态化幹預,外彙占款變動很小。這種情況下,銀行結售彙順差主要轉變成為銀行對外資産運用。二季度,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産增加602億美元,其中外币資産增加324億美元(見圖表23)。
對外淨資産環比減少,人民币升值的估值效應明顯
對外淨資産減少主要受非交易因素影響。截至2021年6月末,對外金融資産90278億美元,對外金融負債70418億美元,淨頭寸為對外淨資産19860億美元,環比減少1540億美元。結合國際收支平衡表資料可知,交易引起的變動(含儲備資産的金融賬戶差額取相反數)貢獻了對外淨資産變動額的9%,匯率變動及資産價格重估、統計調整等非交易因素引起的變動則貢獻了91%(見圖表24)。
人民币升值導緻非交易引起的對外負債增加。在非交易因素引起的變動中,對外資産減少471億美元,小于對外負債增幅937億美元,後者主要受人民币升值影響。二季度,人民币匯率中間價累計升值1.7%。這導緻外商股權投資的彙兌收益為516億美元,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人民币股票資産的彙兌收益為94億美元,本币外債的彙兌收益為194億美元[2],三者合計805億美元,貢獻了同期非交易引起的對外負債增幅的86%。
對外投資收益率和利用外資成本率較去年一季度均有明顯提升
二季度,以年化對外投資收益占對外金融資産比例衡量的對外投資回報率為3.2%;以年化外來投資收益占對外金融負債比例衡量的利用外資成本率為6.3%。與2021年一季度相比,二者分别僅提升了0.05、0.07個百分點;但與去年一季度相比,我國對外投資收益率提升了0.4個百分點,利用外資成本率提升1.2個百分點(見圖表25)。
這主要歸功于去年一季度以來我國對外金融資産和負債結構的變化。對外金融資産中,儲備資産、直接投資占比均出現下降,但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占比分别上升2.8、2.3個百分點,反映境内外彙流動性較為充裕,境内主體資産多元化配置需求增加(見圖表26)。對外金融負債中,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占比均出現下降,但證券投資占比提升5.4個百分點(股權和債券投資占比分别上升3.9、1.5個百分點),反映出疫情暴發之後中國經濟率先恢複,人民币資産收益較好(見圖表27)。
此外,對外投資收益率和利用外資成本率上升還與基數效應有關。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響,海外金融市場發生巨震,境内主體對外投資收益降至230億美元,創2013年以來新低(見圖表10);疫情導緻國内企業生産工作停擺,外商投資企業利潤下降,即展現為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彙出減少,去年一季度降至356億美元,創2010年二季度以來新低(見圖表10)。
短期外債占外匯存底比例創曆史新高,但外債風險仍然可控
截至2021年6月末,我國具有契約性償還義務的外債餘額26798億美元,環比增加1532億美元。從期限結構來看,中長期外債、短期外債餘額分别較3月末增加440億、1092億美元,分别貢獻了總體外債餘額增幅的29%、71%。短期外債占外匯存底比例為47%,較3月末上升2.8個百分點,繼續創1994年以來新高,但仍然低于100%的國際警戒線,表明外債償付能力仍然充足(見圖表28)。從币種結構來看,外币外債(含SDR配置設定)、本币外債餘額分别較3月末增加692億、840億美元,分别貢獻了外債餘額增幅的45%、55%(見圖表29)。如前所述,人民币升值導緻本币外債餘額增加194億美元,這部分彙兌收益貢獻了本币外債餘額增幅的23%。
民間部門貨币錯配明顯改善,預計美聯儲Taper影響或有限
雖然我國對外淨頭寸長期為正,但将對外資産中的儲備資産剔除後,民間部門對外淨頭寸為負。截至2021年6月末,對外淨負債(不含儲備資産,下同)為13599億美元,環比增加2028億美元;占年化名義GDP比重為8.0%,環比上升0.8個百分點(見圖表30)。雖然民間部門對外淨負債規模和占比均有所上升,但交易引起的對外淨負債增加僅貢獻了31%,非交易調整貢獻了69%。其中,人民币升值導緻人民币計價的外商直接投資、股票和本币外債合計增加805億美元,貢獻了對外淨負債增幅的40%。
2015年“8.11”彙改之初,出現人民币貶值和貶值預期互相加強的情況,主要原因在于,彙改之前民間部門積累了大規模的貨币錯配,市場對于本币貶值十分敏感。不過,經曆了2015和2016年藏彙于民和債務償還的集中調整,民間貨币錯配大幅改善。目前,無論是民間部門對外淨負債規模還是占GDP比重,均遠低于2015年6月末(見圖表30),其結果是市場對匯率波動的容忍度和适應性明顯提高。是以,即便2021年年内美聯儲正式啟動Taper,人民币匯率或短期承壓,但預計對中國對外經濟部門影響有限。
注釋:
[1]境外對我國證券投資的主要管道包括,境外機構投資境内債券市場(包含“債券通”和銀行間債券市場直接入市)以及我國機構境外發行的債券(包括央行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币央行票據),“滬股通”和“港股通”管道,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RQFII等)管道。[2] 分别将2021年3月末和6月末外商直接投資中的股權投資、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資産、美元計價的本币外債餘額的平均值乘以二季度人民币匯率中間價變動幅度計算得到。
(本文作者介紹: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