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澤先生學習德語和法語,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積極翻譯和介紹法國異端和哲學,他對薩阿德,布列塔尼,巴塔耶和中音的作品和思想的介紹在日本産生了重要影響。除了對色情和幻想文學的興趣外,他還在神秘主義,自然科學,藝術,宗教和習俗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并輔以精神分析,符号學和結構主義等前衛哲學理論,并創造了許多不容易分類的有趣文本。
這些文本在當時的語境下非常前衛,不僅因為"文化不同"的内容和新理論,寫作風格和文體形式也極具挑戰性。時至今日,很難準确描述其寫作類型,既有跨學科的視野和方法,又有系統的審視,又有強烈的主觀叙事和抒情色彩,寫作是不可預測的:小說像文化,散文像曆史論文,曆史專著像虛構文學。簡而言之,他是一位風格和叙事魔術師。他獨特的才華吸引了很多關注,三島得到了日本戰後重要作家和藝術家的大力推廣,如Jifu,Shigeru Toyama,Hiroshi Yamashi和Keiko Takahashi。近日,後浪潮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惡魔幻影》,這是靜澤的另一本中文譯本。這是他比較早的作品,寫的"規則"和"簡單"比後來更多,是日本文化界"惡魔"引發的重要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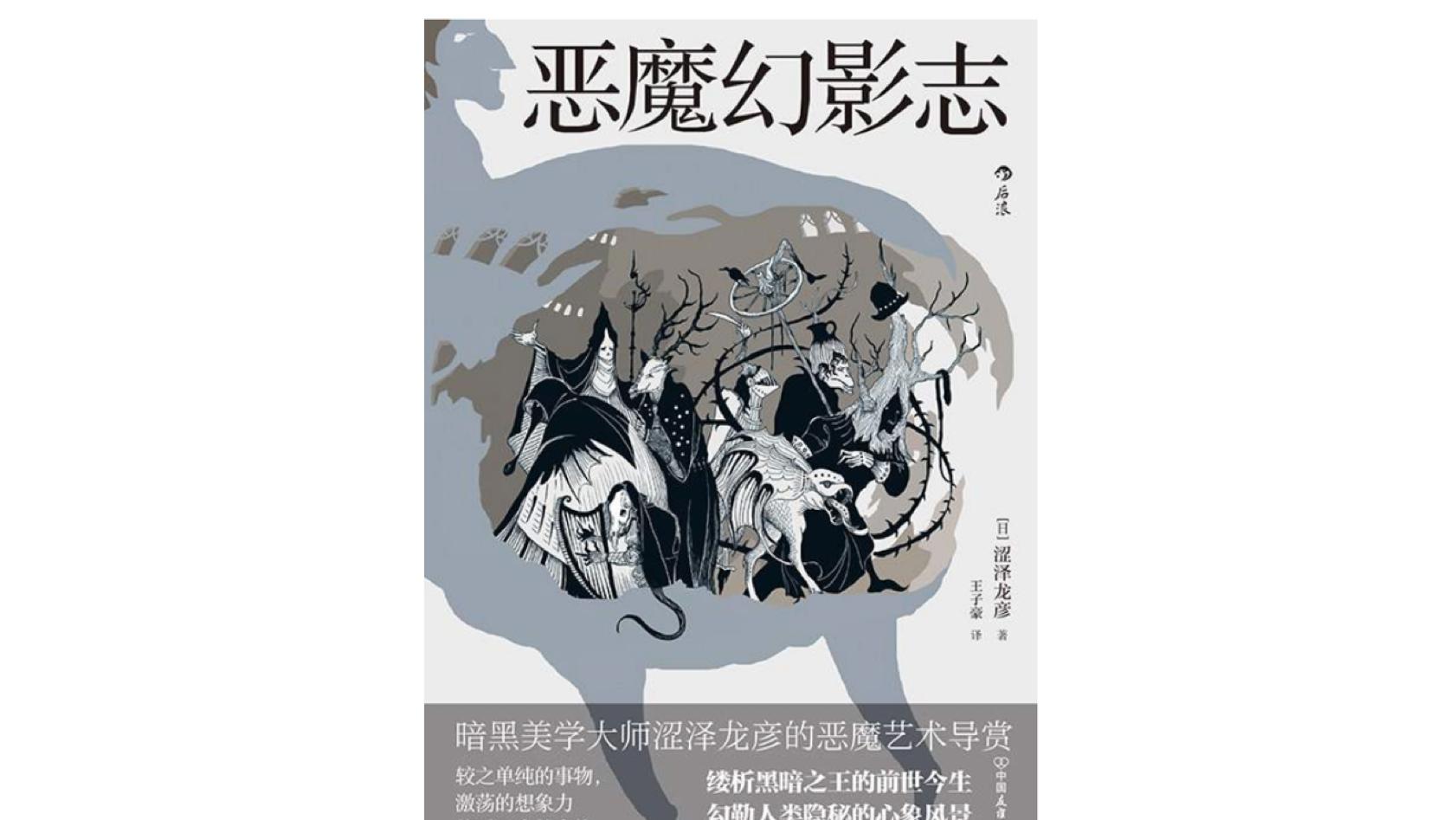
《惡魔幻影》,石澤龍岩著,豪親王譯,2021年10月版《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後
作者|王鵬傑
(清華大學藝術系四川美術學院藝術博士,從事藝術創作、批評、理論研究和策展工作)
澀谷風格的開始
《惡魔幻影》是石澤龍岩于1961年撰寫的八篇文章合集,1978年,在文集末尾,原文中增加了四十多頁的内容,擴充到九篇文章。全書的主要線索非常清晰,圍繞着"魔鬼"形象的起源、發展和變化,基本上按線性時間順序來描述;在論述過程中,靜澤不僅限于西方的曆史架構,其他非西方地區也曾被用來與西方文化現象進行詳細比較,包括埃及、中東、印度、中國和日本等古代文明都特别看重。當然,在澀谷的視野中,"魔鬼"是西方文明中最充分的展現,是以書中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對西方前現代曆史和文化的讨論上。"魔鬼"的巨大熱情,主要是因為"魔鬼"的變化總是打破曆史和現實的刻闆印象。曆史文化的每一次劇變,都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極大地改變"魔鬼"的形象和意義。在希澤看來,"魔鬼"成長和變異背後的驅動力來自基督教内外正統和異端的鬥争。前基督教時代的古希臘、羅馬等西方文化,以及古印度、古阿拉伯、古亞洲等西方的外來文化也參與了"魔鬼"的建設過程,極大地拓展了"魔鬼"變革的潛力。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澀谷還處在他早期的蒂默斯時代,不僅熱愛"魔鬼"文化,還對異端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此外,他對神秘主義、超現實主義、人類潛意識、怪物怪異的愛好也暴露無遺。可以說,施澤文學的基本特征在這個時候已經形成。本書所涵蓋的一些主題,如《菲斯特》、《老闆》、《黑社會》、《死亡》、《夢幻世界》等,在他的後續作品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此時,雖然不像他後期的作品那樣迷人迷幻,但也因為大量的惡魔意象和相當奇幻的味道。這不是一部真正的曆史作品,筆式舉止和機器的傾斜度都一樣,會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忘記這是一本書。就在我們想到,在閱讀有趣的文章時,大量的曆史資料,嚴謹的解釋,讓我們感受到了這本書的學術取向。這種閱讀經驗在他後續的作品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這本書可以算作龍燕寫作風格的第一部作品,在語言、叙事、質感和哲學上都達到了成熟的狀态。
為魔鬼的世界搶占先機
在東亞藝術史的傳統中,魔鬼主題早已被遺忘。這可能與主要起源于歐洲和阿拉伯地區的魔鬼概念有關,也可能與主流東亞文化傳統對異端的蔑視和壓制有關。此外,應該認識到,藝術史是從西方引進的,對亞洲來說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學科。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現代學術和藝術都是現代性的産物。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史學科都是在20世紀之後誕生的。在創作之初,自然界就注重學科的堅實基礎,如渴望從西方起源吸收藝術史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風格、形式、形象、實證這些基本概念由當地學者領悟、掌握,然後用了半個世紀。與中國相比,日本的藝術史學科建立得更早,發展更快。到20世紀30年代,學科的基本規範和方法已經成熟。日本藝術史學家注意到,對本土"怪物"和西方"魔鬼"形象的比較研究早于中國。20世紀上半葉,日本學者在研究西方"魔鬼"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各自為政,尚未形成清晰的架構認識。在藝術史世界之外,西方"魔鬼"的形象和家譜對普通日本人來說還很陌生,在戰後的日本,20世紀50年代、60年代也很少被問及知識。在這種背景下,更容易了解靜澤"魔鬼"藝術史的文化影響和曆史意義。
魔鬼的世界來自主觀妄想,澀谷是一個嘲笑僵化的機械反射理論(精神完全是真實物質世界的反映)的神秘主義者,他對魔鬼曆史的描述牢牢抓住了精神史的内在背景。魔鬼的每一次形式和意義的變化都與當時的思想運動和心理機制有關。人類的好奇心、恐懼、顫抖、渴望和祈禱以奇怪的方式創造了不斷變化的"魔鬼"。靜澤之是以能夠如此清晰地梳理魔鬼的血統,得益于對西方(但不限于西方)宗教史和社會思想史關鍵事件的精确把握,如二進制論意識形态結構的出現、北歐民族與羅馬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地獄與煉獄概念的興起, 三位一體和反三位一體結構之間的對抗,啟示錄的出現和普及,教會和異端之間的反複拉鋸戰,教廷和東方教會之間的分裂,黑死病蹂躏歐洲大陸,龍的形象的成熟,方濟各會天主教托利黨引領了辛勤工作的浪潮。除了積極探索思想事件之間的聯系外,澀谷還充分利用了圖像科學、風格比較等藝術史研究方法,通過相史互證,令人信服地诠釋了不同時期的魔鬼性格。澀谷充分認識到,一切奇特的事物都是意識和潛意識的标志,誕生于人類精神過程中的各種内在生産活動。
圖像科學、藝術史、概念史和後現代主義
澀谷很可能是第一位同時掌握符号學、精神分析和圖像科學的日本作家,他對冒險和實驗精神的文體探索激發了後結構主義的意識。這些不是靜澤所獲得的理論技術,而更像是某種天賦。他的才華遠不止于此,他對繪畫和雕塑等視覺藝術作品的風格興趣和形式主題非常敏感。他選擇讨論的藝術作品,不僅滿足了作者以其奇異的造型所具有的好奇心,而且在藝術的完整性和表達的獨特性方面也堪稱典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很多藝術作品都沒有得到重視,靜澤在圖像分析中從未見過任何原創作品(甚至還沒有在國外),但可以洞察到作品中許多細微的加工,可以看出藝術感的強度。
同樣值得強調的是,澀谷的神情令人震驚,這可能與他對自然的癡迷有關,他所欽佩的學者往往是各個年齡段的傑出學者。自然界現在似乎不是一門嚴格的現代學科,幾乎包含着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風俗學、曆史、宗教、技術、科技等知識,通過大自然擷取異常豐富的文獻和圖像資料,再加上廣泛的文學哲學興趣和驚人的洞察力,成為東西方的思想家, 古代和現代知識。在對圖像科學的分析中,他能清晰地指出不同時代"魔鬼"圖像的複雜含義,并能夠發現這些耀眼的符号與曆史趨勢之間隐藏的關聯。他不是一個真正的專業學者,但他博學的學位怕大多數人文學者隻能崇拜風。這些知識使他能夠巧妙地将圖像分析與概念曆史相結合,自然融合。
與專業藝術史寫作不同,Shize的"魔鬼"藝術史突破了風格史的束縛,也不局限于簡單而僵硬的藝術社會學,而是從神秘主義傳統進入,通過古典宗教和社會觀念的曆史諸多線索,進入魔鬼生成模式機制分析。考慮到基督教神學和異端和神秘主義對"惡魔主義"的貢獻,作者對多種文化體系的研究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嘗試,而且深入到他的思想體系的内在部分。例如,在泛基督教神學光譜中,猶太經典"Tamud"和Kabbalahism(希伯來神秘主義哲學),舊約聖經思想,"啟示錄"思想,新教思想經常被提及,作者對上述思想做出了生動的解釋。為了解釋魔鬼形象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象征意義,他運用了各種知識,但不僅像書房一樣放下書包,還能保留審美直覺。神秘主義者必須非常尊重感情,他的證據和論點通常是清晰而嚴謹的,以便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感受。當然,關于"惡魔"的文獻早已不在主流曆史視角之内,相關研究也總是與巫術、煉金術聯系在一起,是以總是被簡單地了解為迷信。讀這本書,讀者會發現,"魔鬼學"顯然不是迷信,而是在提供對人類幻想和黑暗意識的洞察。
靜澤龍岩的手稿
Shigeru采用了一種開放的思想現象學觀點,引用Enrico Castelli的話說,惡魔的東西是"不存在的,表現為純粹的冒犯"。靜澤通過一些案例得出結論,魔鬼是事物的流動、遷徙,不斷穿梭于不同的領域,它的存在是變化和運動的方式。比如魔鬼和天使之間不可避免的鬥争和沖突,在某些時候可能會變得模糊,有時魔鬼和天使會難以區分,甚至角色也會改變。魔鬼的形态是由二進制結構塑造的,二進制結構總是對應着某種對應的或相反的物體,但它的面卻從來都不是穩定的。它通常被視為恐怖和死亡的使者,但在中世紀歐洲人民的極度恐懼的驅使下,它也可以演變成一個值得期待和歡迎的對象。雖然它來自人類的内心深處,但既不是人類内在的東西,也不是客觀的東西,通過"擠壓客觀性達到盈餘狀态",過剩已經成為魔鬼不斷進出人類動機的遊刃有餘。
這種願景和了解與澀谷所持有的後現代主義世界感有關。在戰後的日本,第一個為後現代主義吸引公衆關注的理論家是淺田,有些人甚至認為他是後現代日本哲學的主要創始人。事實上,在他之前,一些思想家和學者已經認識到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本質。靜澤比淺田先生大29歲,他以神秘主義掌握符号學,進入類似于後結構主義的思想領域,形成了對理性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深刻批判和質疑。在這本書中,靜澤通過影射和論證揭示了他對理性世界的不信任,松開了現代思想的慣性,即一切都是理性的,并表達了對非理性精神的緻敬。他将不确定性、運動和颠覆視為體驗世界的基本方式。在《惡魔幻影》中,這種後現代的曆史觀和認識論已經形成。三年後,他寫了《宇宙之夢》,标志着什葉派後現代世界觀的成熟,精神質地更加獨特、奇特。
《宇宙夢之書》,石澤龍岩著,譯者:雷克,新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結束:替代野心
澀谷是日本現代異端文化的重要先驅,也是以反社會方式宣揚異端、批判和質疑現代文化單一性的先驅。他的文筆引人入勝,除了優秀的文學感、震撼人心的非正常知識、充滿異端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或許更為根本的原因,尤其是在東亞文化圈的集體主義文化圈中。就本書而言,"魔鬼"的主題被如此生動和精彩地讨論,以至于它為被工具理性毒害的"單向人"提供了另一個新世界。在東亞世界,主流文化對鬼魂等事物的讨論相當抗拒,戰後日本正處于國家重建和戲劇性變革的社會浪潮中,很少有人關心魔鬼的藝術。澀谷在這樣的時代卻是社會上如火如荼的建設和抗議運動,無動于衷,沉浸在魔鬼和夢想的神秘世界中。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本能地憎恨任何主流事物,包括安全運動時代的革命青年激進主義,并且經常與社會主流規範和觀念相沖突的行為。在寫這本書的同一年,澀谷因出版《邪惡的榮耀》(邪惡的榮耀)而被法院起訴,因為與靜澤的書的出版有關,這與日本社會的主流倫理相悖。這場曆時九年的訴訟,成為日本社會的一個衆所周知的事件。靜澤對這場漫長的訴訟持冷漠态度,表示輸赢并不重要,隻要噪音有趣。1969年,他被判有罪,被罰款7萬日元,他開玩笑說,禁區内的7萬元隻是由法院玩弄的,這從他對平常生活态度的蔑視中可以看出。
在他的研究和寫作中,他在色情、恐怖、神秘、畸形等主題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這種審美品味及其背後的價值取向,把世界上所有"合理"的刻闆印象都看成是假的。在這本書中,他積極地為異端邪說當魔鬼,除了我們熟悉的價值觀之外,建構了一種超然的另類世界觀。雖然這本書可以算是一本關于藝術史的專著,但白澤無視學術界的刻闆印象,沒有把它寫成學術專著,非常重視自己的直覺和想象力,甚至創造性地(和有争議地)組織了論證,以表明這些想象是足夠可信的。他的作品顯然是學術和意識形态的,但不是為學術界,也不是為文學界,純粹是為了他們自己與時代的目的截然不同。通過講述"魔鬼"的故事,我們探索了讀者了解更複雜和黑暗的現實世界的新途徑。從他後來的作品中,讀者可以發現,他寫作的最大動機是滿足自己的興趣,而"有趣"對他來說幾乎等同于生命的意義。他對異性戀有着濃厚的興趣,或許是因為它意味着走向無限美好的開端,它總是在某個邊緣地帶,總是遊蕩在理性認知、科學論證的世界之外,不會因為"知識"的不真實知識而被淘汰,其更新潛力也不會被耗盡。探索不同文化的道路是無止境的,以至于親近的人的生活意義變得不确定,充滿了未知。
作者|王鵬傑(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博士,四川美術學院造型學院任教,從事藝術創作、批評、理論研究和策展工作)
編輯器|走
校對|劉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