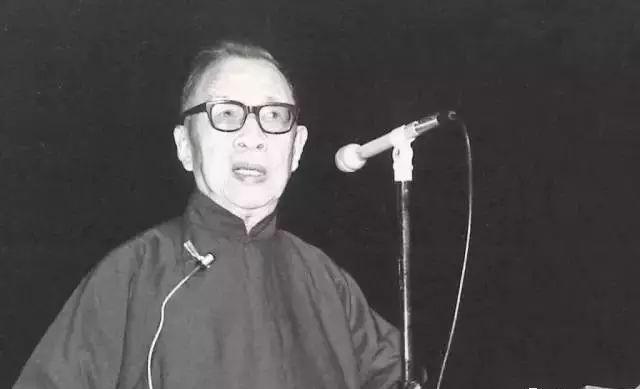
錢牧從童年貧窮,愛讀書,晚年寫自己的生活,爺爺的記憶隻提到了兩本書。其中,"手抄本《五書》一封信,由父親給黃洋木版戴着棉質腰帶包裹,而親書《手還活着》四個字",另一本是"大字镌刻的'曆史'"。這兩本書深深地打動了年輕的千木,"俞自知讀,即熱愛《曆史》,都是從這本書中汲取靈感的。
1909年,錢牧在常州高中三年級時,偶然看到學生看到《曾文正》,沒想讀就忍不住放下。第二天早上,錢沐跑到校外書店買書。當時,書店的門是一塊長木闆縫制而成,店裡剛開門,闆子還沒有卸下來,錢牧從門縫處并排沖進去,急忙問是否有"曾文正",連家人的書一起買。從此,書店就成了千木的私人圖書館,對他幫助很大。
1914年,錢牧在無錫縣第四中學任教,并将多年教學的《論語言》寄成一本《論中國解決方案》的書,送到商業印刷廠,待出版,著作權費和稿件費100元。但它不是現金,而是商業圖書館的百元代金券,你隻能買書(不限于商業圖書館的出版物)。錢牧拿着這百元代金券填補了自己子集曆史書的空白,他感慨地說:"從那以後剩下的學習和進步。這百元的圖書券,其實對俞炳彥來說大有裨益。"
錢牧自1930年以來一直在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并在北平生活了八年。教書做學就是到老書市場找書,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其中有永遠不會被遺忘的好書:
首先,顧祖軒《讀史前八卷輿論總結》,镌刻清代嘉慶年代。拿到後,錢牧在半月刊《玉功》上寫了一篇文章。
二是張世齋傳承的家族傳記。一天下課後,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毛子水特意到曆史系休息室找錢木,市場寄來了一本《章石齋的遺産》,不知道有沒有價值,想問錢牧的身份證明。錢牧仔細查了一下,發現這本書确實是張氏家族的傳記。這本書幾乎可以說是一本孤獨的書,極其珍貴。如果答案一文不值,這本孤書一定要回到老書店,錢穆可以自己拿了。但想到公共收藏可以讀給公衆聽,是以錢牧告訴毛澤東策展人可以買到這些藏品。
同時,錢牧讓助教一夜之間記錄了雕刻中未見的内容,共20多篇文章。當抗日戰争向南移動時,千木将這些手稿藏在大衣箱的底部,上面有木闆,以避免檢查(為什麼要檢查這些"舊紙堆",錢木沒有解釋,現在不多),轉移到香港,長沙,昆明,成都。四川省圖書館館長孟文東印制200本後,該書得以流傳。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毛子水沒有為圖書館買下《張師齋的遺産》,這本書被轉移到胡石家族的收藏中,最後消失了。
三、《竹書編年史》,北通周磊學琪著,共40卷。錢牧參觀了北平的舊書市場,在北平圖書館拿到了一份手稿。這本書是雷的家人捐贈的,蔡元培校長要求北京大學印刷,印刷後的副本送到了北平圖書館。錢牧看到,太陽藍書(抄本)一本,并将相關内容成自己的《前秦朱子》一書。1937年,千木把藍皮書送到書店印刷,書經發行。
錢慕濤的藏書,其目的還是學習。他有一本朱世禅的《竹書編年史》,糾正了王國校對員的許多錯誤。福賢曾訓示北足書店為他尋找這本書,好幾年來一直沒有結果。最後,錢牧的書不得不借用在陽光和藍色中複制,并收藏在中央研究所的圖書館。
錢牧回憶起他在北平的八年:"過去五年我買了5萬多本書,當時大約是20萬冊。月曆年的工資,削減食物和衣服,都花在這裡。"
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北京大學等學校位于邊境以南。錢木藏書量大,交通難,更難找地方存放書,而且每年夏天都要烘幹。一遍又一遍,千木臨時做了20個大箱子,把20萬冊的書放進箱子裡,和主人約定,房子不再租給别人,以此類推平安回來拿書。
勝利後,錢牧沒有回到北平,而是在家鄉江南大學任教。店主催促千木的朋友唐把書拿走。唐玉發現千木熟悉一本書估價拿,書本估價願意出價百石米價。這時錢木已經到了廣州,他吩咐唐帶了一本書妥善儲存,于是他回到了北平,還是以100石米的贖回價錢。
後來,錢牧搬到了香港,老朋友沈豔某為新亞研究所買書,拿到了"資本管理總書"之一。錢牧看了看,發現是他的大哥錢真摯(錢維龍爸爸)一生前的讀書,書上有很多大哥的筆迹。這本書現在在香港,其他20萬冊是可以想象的。此時,唐已經去世,錢慕貝藏書的下落也從未被查過。
來自世界,散落在世界上。書本上沒有滿滿的香,隻有人的命運才能得到它。
(本文參考書目:錢牧的《父母、老師、朋友的八十本回憶錄》,嶽麓讀書會,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