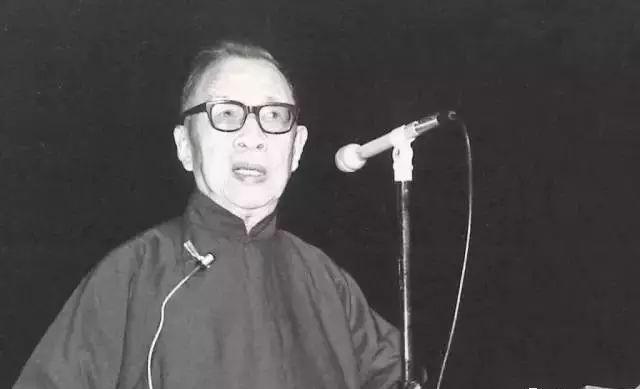
钱牧从童年贫穷,爱读书,晚年写自己的生活,爷爷的记忆只提到了两本书。其中,"手抄本《五书》一封信,由父亲给黄洋木版戴着棉质腰带包裹,而亲书《手还活着》四个字",另一本是"大字镌刻的'历史'"。这两本书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千木,"俞自知读,即热爱《历史》,都是从这本书中汲取灵感的。
1909年,钱牧在常州高中三年级时,偶然看到学生看到《曾文正》,没想读就忍不住放下。第二天早上,钱沐跑到校外书店买书。当时,书店的门是一块长木板缝制而成,店里刚开门,板子还没有卸下来,钱牧从门缝处并排冲进去,急忙问是否有"曾文正",连家人的书一起买。从此,书店就成了千木的私人图书馆,对他帮助很大。
1914年,钱牧在无锡县第四中学任教,并将多年教学的《论语言》寄成一本《论中国解决方案》的书,送到商业印刷厂,待出版,著作权费和稿件费100元。但它不是现金,而是商业图书馆的百元代金券,你只能买书(不限于商业图书馆的出版物)。钱牧拿着这百元代金券填补了自己子集历史书的空白,他感慨地说:"从那以后剩下的学习和进步。这百元的图书券,其实对俞炳彦来说大有裨益。"
钱牧自1930年以来一直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并在北平生活了八年。教书做学就是到老书市场找书,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其中有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好书:
首先,顾祖轩《读史前八卷舆论总结》,镌刻清代嘉庆年代。拿到后,钱牧在半月刊《玉功》上写了一篇文章。
二是张世斋传承的家族传记。一天下课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特意到历史系休息室找钱木,市场寄来了一本《章石斋的遗产》,不知道有没有价值,想问钱牧的身份证明。钱牧仔细查了一下,发现这本书确实是张氏家族的传记。这本书几乎可以说是一本孤独的书,极其珍贵。如果答案一文不值,这本孤书一定要回到老书店,钱穆可以自己拿了。但想到公共收藏可以读给公众听,所以钱牧告诉毛泽东策展人可以买到这些藏品。
同时,钱牧让助教一夜之间记录了雕刻中未见的内容,共20多篇文章。当抗日战争向南移动时,千木将这些手稿藏在大衣箱的底部,上面有木板,以避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这些"旧纸堆",钱木没有解释,现在不多),转移到香港,长沙,昆明,成都。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孟文东印制200本后,该书得以流传。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子水没有为图书馆买下《张师斋的遗产》,这本书被转移到胡石家族的收藏中,最后消失了。
三、《竹书编年史》,北通周磊学琪著,共40卷。钱牧参观了北平的旧书市场,在北平图书馆拿到了一份手稿。这本书是雷的家人捐赠的,蔡元培校长要求北京大学印刷,印刷后的副本送到了北平图书馆。钱牧看到,太阳蓝书(抄本)一本,并将相关内容成自己的《前秦朱子》一书。1937年,千木把蓝皮书送到书店印刷,书经发行。
钱慕涛的藏书,其目的还是学习。他有一本朱世禅的《竹书编年史》,纠正了王国校对员的许多错误。福贤曾指示北足书店为他寻找这本书,好几年来一直没有结果。最后,钱牧的书不得不借用在阳光和蓝色中复制,并收藏在中央研究所的图书馆。
钱牧回忆起他在北平的八年:"过去五年我买了5万多本书,当时大约是20万册。日历年的工资,削减食物和衣服,都花在这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等学校位于边境以南。钱木藏书量大,交通难,更难找地方存放书,而且每年夏天都要烘干。一遍又一遍,千木临时做了20个大箱子,把20万册的书放进箱子里,和主人约定,房子不再租给别人,以此类推平安回来拿书。
胜利后,钱牧没有回到北平,而是在家乡江南大学任教。店主催促千木的朋友唐把书拿走。唐玉发现千木熟悉一本书估价拿,书本估价愿意出价百石米价。这时钱木已经到了广州,他吩咐唐带了一本书妥善保存,于是他回到了北平,还是以100石米的赎回价钱。
后来,钱牧搬到了香港,老朋友沈艳某为新亚研究所买书,拿到了"资本管理总书"之一。钱牧看了看,发现是他的大哥钱真挚(钱维龙爸爸)一生前的读书,书上有很多大哥的笔迹。这本书现在在香港,其他20万册是可以想象的。此时,唐已经去世,钱慕贝藏书的下落也从未被查过。
来自世界,散落在世界上。书本上没有满满的香,只有人的命运才能得到它。
(本文参考书目:钱牧的《父母、老师、朋友的八十本回忆录》,岳麓读书会,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