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以為這是一部法醫電影,20分鐘後我看到它是一部屍體電影,起初我感覺像一部恐怖電影,最後我意識到這是一部宗教電影。一位"哭泣"電影觀衆評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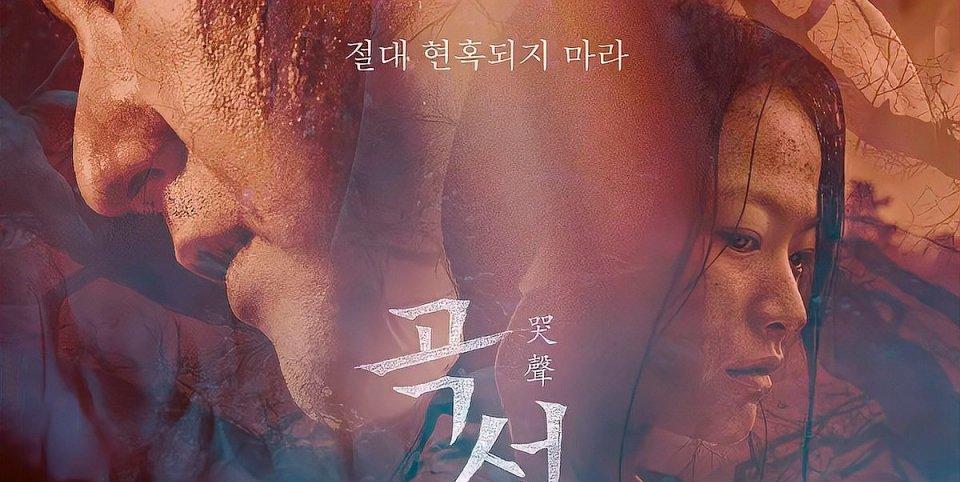
電影海報
毋庸置疑,南韓傳統犯罪片的特點——黑暗的色調、冰冷、壓抑的暴力美學——的結合,正是《哭泣》成為2016年戛納電影節"衆神"的原因。
這部電影的開頭提到了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與他的門徒的對話。門徒懷疑重生的耶稣是否有肉體和思想—— "但是他們驚慌失措,以為他們看到了靈魂",耶稣說,"看看我的手,我的腳,你知道是我,摸摸我,沒有肉體,你看,我有。"正是這種對話的出現将電影帶到了宗教的高度。無論是電影中跳神的巫師,還是祭司的助手,無疑給這部劇都有很強的宗教色彩。
據說導演也是某個教派的信徒,是以也有人說這是一部隻有信徒才能了解的電影,但我覺得這種說法太多了,但是對于聽介紹第一次看到劇的觀衆來說,最好接受第一次不了解自己的, 畢竟小編隻看了5次。
六年磨劍,想必導演也是煞費苦心,為此後續的《黃海》《追擊者》電影增添了濃厚的文化底蘊,影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質疑最大化。可以說,影片時長近三個小時,全片都在探讨這兩個話題,父女的猜疑,鐘龍對白衣女人的嫌疑,警察對村民的嫌疑,一步一步地将劇場推向高潮。影片結尾沒有直接指出懷疑是好是壞,結局更像是導演對觀衆說話——你曾經信任過嗎?你有沒有再次懷疑過?
導演羅豔珍說:"人類最可怕的感覺是,一個人不知道該依靠誰,很難分辨,我覺得是最可怕的。"而這句話,卻成了英雄鐘龍的真實寫照。面對村裡一連串因奇異病死亡,幾乎所有村民都将其歸咎于神秘的日本人。而警察鐘龍舉着無鬼神學的旗幟,村民們的懷疑嗤之以鼻,在這次調查中,也将卷入一場人生噩夢。
從從不信任鬼魂到親自邀請巫師到他們的女兒家,戲劇性的來回對比暴露了Chung作為一個人的脆弱性。"當你在戰場上,你的生命處于危險之中,你無法預測是子彈、火焰還是前方的雷聲,你的生命被一個念頭所束縛,你忍不住向一個'神'祈禱,希望會有一股外在的力量幫助你在别人眼裡感到荒謬, 甚至之前和之後。但是,一個人的信心總是脆弱的,當陷入一個痛苦的境地,一個人看不到出路時,他會以如此恐慌的方式尋求可能的救贖。"
這種觀點在影片中很多地方都有提及。
當警察一直無法找到真正兇猛的自我抛棄時,帶來了原本對十字架的不信任,希望它能趕走邪靈,但結果卻恰恰相反;我們甚至可以在地面上切開,體驗鐘龍的痛苦和糾結,因為他就是我們放大的每個人。
影片接近尾聲時,面對白人女子和巫師的陳述完全偏離,鐘的崩潰和家人能夠冷靜下來的強烈願望,都像錘子一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沃爾特·利普曼(Walter Lipman)曾經說過,"大多數時候,我們不先了解定義,而是先定義它,然後再了解它。"信不信由你,你相信誰?"成為鐘龍的命運選擇。
然而,最終,這部電影未能逃脫南韓傳統電影的悲慘結局 - 鐘國不顧白衣女性的勸阻,在第二聲雞聲中沖回家。他為之奮鬥的家園早已不複存在,他自己也未能逃脫死亡的詛咒。
羅豔珍,用他擅長陰郁濕潤的"髒亂"美學的導演方式,把人性的脆弱和不能直接撕開來展現給我們。悲慘的開場結局讓電影的主題對那些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人來說更加混亂。"說了什麼"和"誰是好誰惡"隻能在電影的細節中再次回答。
而這種悲慘的結局方式,也讓鐘隆所代表的弱者、無所作為的形象深深紮根于百姓心中,其表現出的怯懦無能也活了過來,或許引起我們更多的是思考和反思。比如《大熔爐》結局中女生性侵的不可能,代表平民的姜仁浩最終也得不到給女生哪怕一點點的道歉。這種對狼主現象的反應在現代社會中随處可見,我們聽不到受苦受難者的呼救聲,因為他們甚至沒有能夠為他們伸張正義的人。同樣暴露社會政治腐敗黑暗的是一部名為《活生生的恐怖》的南韓電影,其中因父親去世而安裝炸彈的樸振佑最後沒有聽到總統的道歉,在首爾漢江馬普大橋上引爆炸彈的聲音更像是一聲歎息和咆哮。誰将保護我們的權益,保護人民的權利,其中單向鏡窺視他們受保護的人。
毋庸置疑,南韓是一個能夠讓犯罪片質感十足、層次深刻、用不同方式制造痛苦,用最極端的劇情來激發我們深刻思考的國家。在《哭泣》的結尾,輔助祭祀找到了車禍後沒有死的日本曼庫尼亞人,但被全村視為"惡靈"的日本人,懷着憐憫的心情坐着,"我是來救你的,"他說。面對輔助祭祀的懷疑,他在影片開頭對門徒說了耶稣的話,魔鬼的形象就出現了。
這不禁讓人的背影涼快,前後遙遠的回聲,讓開頭的"路加福音"話語得到同樣的證明。你能觸摸到一個有形的靈魂嗎?什麼是好的?什麼是邪惡?面對命運,你能做出正确的判斷嗎?處于事件漩渦中心的人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
更令人苦惱的是,鐘龍的結尾回憶起過去和女兒一系列美好的過去照片,他說:"我們家孝順,知道爸爸是警察,爸爸會處理,爸爸會。"
但他真的有機會嗎?作為一個不聽媽媽話、事業無所事事、對警察沒有信心的大孩子,除了耳邊的哭聲,他活得還算什麼呢?可以做些什麼來改變?
片中鐘龍是一個無聊的人,普通人,懦弱的人,而他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正處在面前不斷的掙紮,到最後的習慣沉入生活的泥濘中,我們什麼都不做,什麼也沒做,原來對世界的好奇心被切成粗糙的茶米,悄悄地吞進肚子裡,我們知道自己不好看,卻無法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Chung一再提出問題,為什麼在他女兒被謀殺後會發生在我身上。這是對每個受害者被謀殺的第一反應。值得注意的是,誰被殺或誰被殺,對受害者來說,是飛進飛出的問題,但對于肇事者來說,卻是"随機暴力"的問題。羅還說,"我想知道的不是受害者的受害者,因為受害者處于某種心理狀态,因為某種原因做了一些事情讓受害者受苦,但為什麼是受害者呢?""
在對導演的采訪中,導演對影片想要傳達的内容也模棱兩可,是以大多數人對影片的評論也褒貶不一,所謂"千人有千哈姆雷特",也就适用于《哭泣》。
我所了解的"哭泣"傳達了一種開放式的恐懼。他用最極端的故事給我講了一個奇怪的故事,讓我懂得了最簡單的人生。在觀影過程中,我一直在扮演中龍的角色,我發現鐘龍的反應與如果我在這種情況下被選中會做的事情相吻合。我看了很久的鐘,仿佛看到了另一個自己。這種東西叫"共鳴",就是我突然跟劇的關系縮短了很多,我感受到了鐘龍心中的痛苦,最後無法回到天空的痛苦。
這是一部向觀衆投擲誘餌的電影,沒有明顯的主題,甚至結局也令人困惑,在廣度和寬度上都無休止地放大,你可能會看到你想看到的東西。
但影片并非那種無可挑剔,導演花了将近三個小時,不斷打亂故事,重建故事,隻是為了說:"在不可預測的事件中,人沒有分辨善惡的能力。"這似乎沒有必要,也許這是一種恥辱,在複出之後或多或少地留下來,"他說。
但正如我之前所說,每個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它具有普遍性。這仍然是一部值得一遍又一遍觀看的電影,我真的希望觀衆能夠大膽嘗試一下,也許會發現一部新電影。
或許正是這部被衆多影評人稱贊為"神片"的電影,讓普通大衆在一次搶臉後第一時間看,知道對《哭泣》有很多分析。我們或許無法達到逐幀解析的高度,但我們可以擁有最真實的感受和最獨特的視角,為影片注入新鮮血液,這或許就是影片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