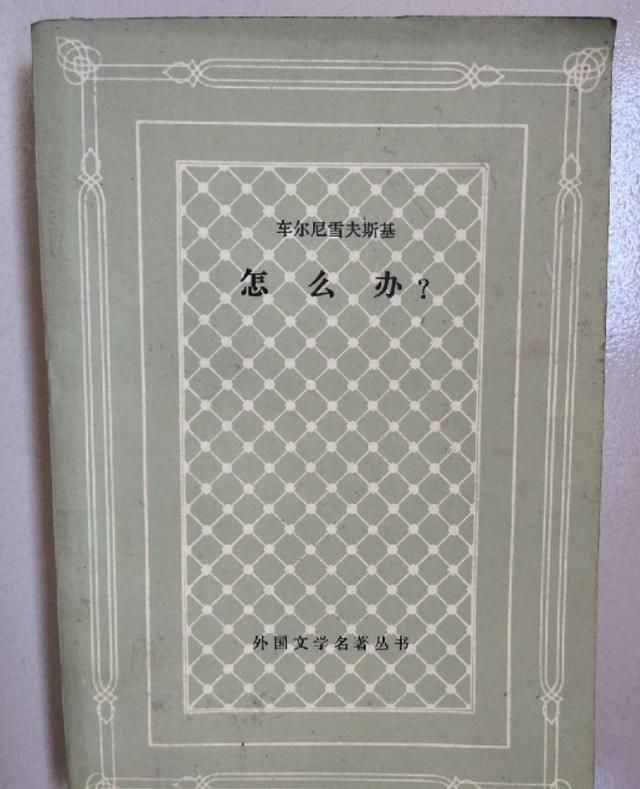
寫于1862年左右的俄國長篇小說《怎麼辦?》,其中的一些寫作技巧,今天看來,依然充滿着新鮮意味,可謂是曆久彌新。
1862年,距今多少年了?
160年。
發表《怎麼辦?》的1863年,中國還在清朝同治年間,鴉片戰争帶來的巨大的沖擊,正讓當時的中國社會,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而這時的俄羅斯社會,我們通過小說可以看到,已經擁有了完備的教育體系,醫學院能夠培養出社會需要的醫生,疾病治療能夠采取科學的手段,女性能夠自立地在社會生存,抛頭露面,開辦工場,男女青年可以自由聚會,暢談社會變遷、人生夢想、情感取舍,大街上能夠有馬車作為公共交通工具,莫斯科鐵路已經帶來了速度與激情。
可以說,《怎麼辦?》裡描寫的社會,與我們現今的社會,差距并不大,我們說它們都屬于現代社會,當沒有異議。而我們現在與清朝同治年間的差距,卻隔着一個時代,可以說不屬于同一個時代。
既然我們與一百六十年前的俄羅斯社會同屬于一個社會氛圍之下,那麼我們今天,了解那個時代的小說内容、背景與人物心理反而沒有隔閡與阻礙。
而同時代的中國文學,幾乎沒有一本拿得出手的。
同時期的中國文學裡的女性,能夠在社會上立足的,唯有妓女。一直到1903年問世的《孽海花》,還隻能把妓女作為主角。
往前推溯,晚清的小說中,沒有一部是以女性的社會形象作為小說的主要描寫目标的。
一直到五四運動期間,我們才将這一個時間點,稱着“覺醒年代”。
那麼,也就意味着之前的時光,還是沉睡的時代。
這也就了解了《怎麼辦?》發表時的俄羅斯社會裡彌漫的一些思想意識,可以與我們今天在思想上獲得共情的認同。
《怎麼辦?》裡的一些寫作手法,今天看來,依然不過時。
比如,《怎麼辦?》裡切入到人物的内心,捕捉人物的轉瞬即逝的閃念,記錄成文字的鍊條,基本構成了意識流的典型叙事技巧。
這種意識流技巧,能夠産生一種内心情緒的及時捕捉而呈現出來的真實感,讓讀者感受到心理的波動軌迹與流線型發展路徑,稱得上是小說創作中的一次技術革命。
當然這種革命,有時會走向一個極端,變成一種依靠純粹的意識流動而打造出來的不可捉摸的小說文本,導緻了大部分讀者都難以看得懂的類似《尤利西斯》這類純粹的意識流小說的出現。
而《怎麼辦?》裡的這種意識流技法,恰到好處,摻雜在現實的描寫中,帶來了叙事的靈動與内心呈現的鮮活。
我們摘錄一段,看看小說裡是如何直接介入到人物的内心,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全盤托出人物内心的心理起伏的。
下面這一部分是小說第二章的第16節,譯本采用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由蔣路翻譯的譯本。
小說裡的薇羅奇卡生活在一個小市民的家庭,父母強迫她嫁給一個花花公子,她希望過獨立自由的生活,與家裡的家庭教師所持有的現代觀念不謀而合,兩個人心有靈犀,心心相印,最後結成了夫妻。小說在這一部分描寫她與這位家庭教師結識不久,已經互有好感,商議好挑戰家庭權威,他們一起外出,達成了内心的默契,由此膽量倍增,竟然公開地招搖過市,結伴回到家裡,孤男寡女同出同進,其潛台詞是不言而喻的。
顯然,她與這個家庭教師結伴回到家裡,引起了母親的懷疑。而這時候,薇羅奇卡也對自己的未來決斷,并沒有狠下心來,作出一個明晰的抉擇。
小說在這一節中,表現了薇羅奇卡的内心困頓,直接将第三人稱,轉換成了第一人稱,以期更好、更近地開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這一節内容中,小說表現了人物面對前路茫茫而一度生出了結生命的糾結心理,大緻有三個遞進性的心理變化:
一是在走投無路的困頓中,萌生自殺之心。
小說裡寫道:
——這時薇羅奇卡正坐在她的房裡沉思:
我逼着他進來好不好呢?媽媽那麼死盯着我們。
我使他處在一種多困難的地位!他怎麼能留下吃飯?
我的天,我這可憐的人會發生什麼事啊?
他說他有一個辦法;不,我親愛的,毫無辦法!
不,辦法倒有,那就是跳窗。如果太痛苦,我就跳窗。——
這一節,從她帶着家庭教師回到家裡之後必然激起的波瀾,引發她内心的應對之策,她已經沒有它路可走,隻有選擇“跳窗”了斷人生。
二是描寫她對所選擇的自殺方式的延伸想象。
——我多可笑:“如果太痛苦,”——難道現在還不痛苦?
跳窗的時候好像迅速地飛翔一樣,——仿佛不是掉下去,而真是飛下去似的,——這大概是很惬意的吧。不過後來碰到了人行道上——啊呀,好硬!疼嗎?不,我想還來不及覺得疼,隻感到很硬!因為這隻是短短的一瞬間工夫;可是在這以前,空氣活像一床軟綿綿的絨毛褥子,那麼輕巧柔和地往兩邊讓開……妙極了……
不錯,但是以後呢?大家都跑來看,——頭破了,臉也受了傷,倒在血泊和污泥中……不,假如能在這個地方撒些幹淨砂子,——這兒連砂子也總是髒的……不,要撒最白淨的砂子……那就好了。臉不會跌傷,幹幹淨淨的,不會吓倒任何人。——
在這一段心理描寫中,小說為人物安排了設身處地、身臨其境的假想可能,把可能發生的事件的各種細節都考慮到了,可以說是面面俱到,甚至對悲慘事件發生後的自己的可怕狀态,都作了充分的設想。
三是描寫女孩再次更換另一種終結自己生命的方式。
這一節把一個女孩面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的患得患失的内心情态,描寫得活靈活現。
——在巴黎,窮苦的女孩子常常用瓦斯悶死自己。真是個好法子;太好了。跳視窗可不好。悶死才好呢。
他們正在那邊高聲說話。他們說起什麼?不,一點也聽不清。
我要留一張字條給他,把什麼都寫上。因為我本來對他說過:“今天是我的生日。”那時候我好大膽。我怎麼能那樣呢?因為當時我太癡情,當時我不懂事。
是的,巴黎的窮女孩子才叫聰明!好吧,難道我不會變聰明?你看,那多麼可笑:他們一進房裡,什麼也看不見,隻聞到一股瓦斯,空氣綠瑩瑩的;他們大吃一驚:怎麼回事?薇羅奇卡在哪兒?媽媽氣沖沖地對爸爸說:你幹嗎傻站着?打破窗子呀!——他們打破窗子,發現我坐在梳妝台旁邊,腦袋垂在梳妝台上,雙手蒙着臉。——“薇羅奇卡,你中了煤毒嗎”——我不出聲。——“薇羅奇卡,你幹嗎不出聲?”——“啊呀,她悶死啦!”——他們大哭大叫起來。嘿,這多可笑:他們居然會哭,媽媽還要告訴人家,說她怎樣疼我。
不錯,他倒是會替我惋惜。——好吧,我可以留張字條給他。
是的,我要看一看情形,然後像巴黎的窮女孩子一樣做法。我說了就做。我不怕。
而且這有什麼可怕?這種死法不是很好嗎?不過我要等一等,看他說的是個什麼辦法。不,毫無辦法。他不過随便說說,想安慰我罷了。
為什麼人家要安慰我呢?根本不必安慰。既然沒法幫助我,難道還能安慰我嗎?他本來是聰明人,但是他也這樣做。他為什麼這樣做?這是不必要的。——
在這一獨立成章的章回中,沒有什麼情節的進展,完全是一個女孩對改變自己命運采取的偏激手段可能帶來的各種可怕後果,作了豐富的聯想與勾畫,把一個女孩徘徊在生死邊緣的沖突性、排斥性、留戀性都顧及到了。
正是因為對人物心理把握達到了如此的細膩、立體、全面的層面,是以,才能栩栩如生地表現出女孩的抉擇的困難與猶豫,才能明白她為何要執着地走出逃脫家庭的那一個關鍵的一步。
可以說,在這一段的文學描寫中,經典地展現了意識流手法逼近人物内心所帶來的的真實感。
而我們始終要記住的是,這是一百六十年前的一位俄羅斯作家業已成竹在胸、娴熟自如采用的一種技法。
即使我們今天,也不能說這種技法沒有現實的啟發性。
這就是名著的價值與意義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