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樓
訪
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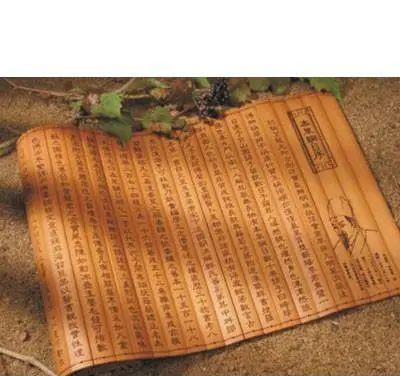
3.8日是所有女人的節日,在這特殊的日子裡,小樓邀請到了數位既是女性,同時也是關心和熱受詩詞的嘉賓。她們有的是高校工作者、有的是詩詞編輯、有的是社會從業人員……
本期主題
女性與詩詞
(2022-3-6晚8:00于小樓聽雨詩刊視訊号直播選粹)
直播嘉賓:劉能英、何其三、鄭虹霓 趙郁飛
主持人:章雪芳 視訊錄制:張帆
直播現場互動
詩友晚秋:
各位老師,填詞曆來崇尚婉約為美,請問你們于現代口語詞怎麼看待?
劉能英答:
也不能說是曆來崇尚婉約為美,自從詞被蘇辛光大之後,我感覺更崇尚以豪放為美,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嶽飛的《滿江紅》不美嗎?隻能說是詞的最初審美是婉約的,萬事總是在不但變化、不斷改進、改良。現代口語,隻要用得自然得體貼切,也是可以入詩入詞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沒有一定學養的人,多半看不懂,但他們的詩詞作品,不識字的人,也能懂,這說明他們也是拿口語入了詩入了詞的。
何其三答:
一般來說口語都帶有一點時代印記,有比較鮮明的時代特征,我自己在這方面也作了一點嘗試。比如我那首《車上看某人發微信》的轉結句:女兒心思最微妙,連發三條又撤回。這首詩一看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寫的。還有我最近寫的《小院有花》:家門未入已聞香,紅似雲霞白似霜。待我歸來才鬥豔,院花開得有情商。都用了現代的口語詞彙。
詩友閑雲野鶴:
老師好,辛苦了!我寫詩的時候,經常詞不達意,老師能否給點建議!謝謝
我也經曆過這個階段,這是很自然的事,就跟小孩子初學說話初學走路一樣,因為基本功還沒有練好,本來是要喊爸爸,結果喊成丫丫,本來是要往東走,結果兩條腿沒有協調好,走到東南方向了,這不用擔心,也不用焦慮,說多了,走多了,長大了,自然就不會喊錯跑偏。這沒什麼捷徑可走,就是多寫多練。
答:不客氣!這個情況應該絕大多數人都遇到過。我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是要格律娴熟,不要憑借工具書就可以秒知那個字的平仄;二是要增加詞彙量,多看經史典籍,甚至可以多讀古典小說,古典小說裡有很多很典雅很合用的詞彙可以選用。
詩友丁永海:
詩詞進校園,請老師們談談如何操作更見效。謝謝!
我現在是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駐校作家,也經常給學生們講詩詞課,關于詩詞進校園,我覺得應該分級而論,如果是進幼稚園,則讓他們能背誦一些詩詞,熟悉一下詩詞的語感就行。如果是進國小,因為國小生還有許多字不認識,正是學拼音的時候,能讓他們掌握押韻就行。到了中學,就要開始讓他們掌握平仄、對仗等基本知識了。而到了大學階段,基本知識就不是重點,重點是立意、結構、技巧、審美等等。
在詩教方面我沒什麼經驗,我很贊同兩位老師所說的,尤其是劉能英老師說的分階段,國小國中高中大學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把詩詞的種子播種到學生們的心中,我覺得特别有意義,甚至可以當作事業來做。
網名老**:
請問各位老師如何掌握運用什麼“韻”來表達自己的情感。
一般情況下,平韻表達悠揚、平緩之情,讀完之後餘音繞梁。仄韻多表達憤懑、抑郁之情,讀完之後弦斷音絕。當然,凡事也不是絕對的,隻能說大概是這樣。
我認為選擇含有感情色彩的韻字是用“韻”來表達自己的情感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灰”、“悲”、“愁”、“憂”,這些字本來就帶有濃重的感情色彩。李商隐的名句:一寸相思一寸灰,就用了“灰”做韻字,千古詞帝李煜的名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就用了“愁”字做韻字。
詩友雲上:
幾位老師如何看待老幹體詩詞?
我老公就特别喜歡讀老幹體作品,他覺得激情四射,朗朗上口。我對老幹體詩詞很包容,他姑且這樣寫,隻要他開心就好,有什麼事比自己開心更好呢?他有權利這樣寫,你有權利可以選擇不看,我老公也有權利選擇他喜歡,他喜歡的,就是最好的。
我覺得“老幹體”有它存在的條件和土壤,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世上有牡丹存在,有玫瑰存在,也有苔花和蒲公英的存在,世界是多元的,我覺得盡量的相容并包吧。還有我一般看事情,都喜歡從正反兩方面來看。寫“老幹體”的人他們至少過了格律這一關,在這一點上還是可取的。還有寫“老幹體”的人不在少數,他們逢着節日慶典就一夥隆地寫,這樣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詩詞,讓他們發動詩詞方面的“群衆運動”還是可以的,而且應該效果不錯。寫到這裡,我可不可以偷偷地笑一個?
詩友蘭州鴻宇鑫:
講點創作經曆和方法,如何能更好的駕馭文字。
這個問題提得好,但提得有點大,三言兩句還真的說不清。提得也有點晚,今天所剩的時間不多,我建議改個時間專題講最好。
我開始寫詩詞的時候,絕律詞啥都寫,而且膽子還特别大,喜歡逞能顯本事,詞喜歡挑《九張機》之類的長調寫,後來寫着寫着膽子反而小了很多,這可能是多了敬畏之心。後來專門填了兩三年的詞,劉能英老師對我說詞填得可以啦,可以轉換去寫其他的了。2018年因為我媽媽車禍住院,空餘時間更少了,就很自然地轉到寫絕句的方面去了。寫了兩三年的絕句,劉能英老師又說:你的絕句寫到很高的程度了,該寫其他的了!她針對我的詩詞所說的話,我基本當做了皇後娘娘的懿旨,我試着改變,後來發現不是我不轉變,而是我們在職的業餘作者時間真的不夠用,盡是碎片化的時間,沒有集中成塊的,寫長一點的作品做不到一氣呵成,斷斷續續的不連貫地寫,很影響積極性,尤其是影響作品的品質。是以我想如果要轉變的話,得等到我退休以後。這是我的創作過程和經曆,其實也包含了一些方法在裡面。
對于如何更好的駕馭文字,那真的需要多練多看,這個屬于基本功的範疇。
嘉賓鄭虹霓安徽六安人,文學博士後。阜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中心阜陽師範大學分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國詞學研究會理事、中華詩教學會理事、上海大學中華詩詞研究院特邀研究員等。出版詩詞集《華章霓彩》、專著《唐宋詞對六朝文學的接受》等。
問:
鄭老師,您好!您最喜歡中國古代女詩人(詞人)是哪位?
答:
更偏向說詞人,這樣就很明确,必須是李清照,盡管她的詩也寫的很好。這裡我遵循的是比較規範的說法,如果籠統來說,古代詩歌是包括了古體詩、近體詩、詞和曲的。如果論古體詩,我們要說的就是蔡琰,民間更熟悉她的字——文姬。
現代女性比李清照幸福多了吧,她再有才也隻能在閨中舞文弄墨。
也不好說,李清照有她讓人豔羨的地方,尤其是與趙明誠青梅竹馬、琴瑟和鳴,這樣的文學知己兼夫妻,可不是随便誰都能有的啊!再說了,現代講究的男女平等,女子一樣要工作,也很辛苦。如果說古代女子更多春恨,主要擔心的是紅顔易老,那麼對于現代的女性呢?有時候還要跟古代士大夫一樣,懷着“悲秋”的情結。要考學、上職稱、應對各種考核。回到家還有一大堆家務要處理,相夫教子的古訓也少不得遵循。是以往往既有春恨,又懷秋悲啊!這時候更需要詩詞來調節,自我拯救,哈哈。
李清照的愛情有人說也不是很完美啊!
那看你從哪個角度來說了,首先我們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苛求古人。比如關于趙明誠納妾的問題,那是古代婚姻制度使然。再有就是關于李清照再嫁的問題,即使大學者也有不同看法,但我覺得還是不要糾結的好。再嫁、離婚都無損李清照的形象,她是著名詞人,同時在那個動亂年代,她也是一個弱女子。
您是如何走上創作詩詞的道路的?
從小受母親影響,我很喜歡讀詩詞,國小畢業那年暑假就在家抄寫背誦《千家詩》。國中時曾經嘗試寫,也不懂格律,基本就是模仿吧,好像模仿林黛玉寫過關于花的長詩,自己抄到折扇上。
您在什麼情況下會有寫詩詞的沖動啊?
這還真不好說,對我來說,寫詩詞純屬愛好,又不是謀生手段,寫作比較随性,沖動情況也有,但不是每次都因為沖動促成了寫作。但是,沖動會導緻不寫不可,甚至影響睡眠。
當代女詞人您比較喜歡的是誰呢?
按照《昭明文選》的體例,我隻說已經去世的前輩吧。首先當然要數沈祖棻,程千帆先生的夫人,也是我們師祖母啦!以前買不到她的集子,我隻好影印了程先生箋注的《沈祖棻詞集》。特别喜歡她的真性情和對時局的關注,她的小令委婉動人,見功力!沈先生詞的好處這裡就不展開了,我還想說兩位前輩女詞人,一位是宋亦英,安徽當代詞壇的開拓者,她與程千帆先生有通信,曾為沈祖棻寫過作品。還有《安徽老年報》的創始人鄒人煜,既是雜文家,又善于寫詩詞。我有幸在學生時代得到她們的指導,多次到她們府上拜望,她們的詩詞富有時代感,宋老詩詞很好地實作了現代與古典的結合,既有哀婉動人的悼亡詞,又有大聲镗鞳的時事詞。鄒老則是用詩詞寫雜文,特有正義感,是一位敢愛敢恨的女子。
嘉賓張一南1984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士、博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大學生詩詞刊物《北社》主編,現為北大中文系教師,中華詩教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中古文學,著有《晚唐齊梁詩風研究》《跟學詩詞》《年輕人的國文課》等。
張一南老師,您好!您是北大的教育從業人員,在您看來,中國女性詩詞寫作傳統是怎樣的?
中國古代女性詩詞寫作總的來說是落後于男性的,因為女性沒能受到平等的教育。往往隻有财富上非常充足、思想上又較為文明開化的家庭,才會讓女孩讀書。能讀到可以寫詩的程度的,更是鳳毛麟角。是以,“才女”的出現,是一個家族完成士族化的一個标志,也是社會安定繁榮的一個标志。
在此前提下,我們應該看到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我認為中國人從來沒有将才女視為“閣樓上的瘋女人”。一個女孩子,隻要有機會成為才女,就會受到整個社會的鼓勵甚至追捧。她會是父母、兄弟、丈夫乃至公婆的驕傲。人們對女性的創作批評比對男性要寬容得多。盡管這離今天我們要的男女平等還很遠,但這說明,我們的文化裡,是有着欣賞、崇拜才女的傳統的,我們應該把這個傳統發揚光大,而不必把“閣樓上的瘋女人”的枷鎖搶過來,加在自己頭上。
能入北大的所有女性學子和教育工作者,都可以稱為才女,您認為,“才女”的形象應該是怎樣的?
我很喜歡葉嘉瑩先生說的那個概念,“穿裙子的士”。
我們首先是士,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隻要遵守“士”的行為準則就可以了。至于“穿裙子”,隻是我們一點細枝末節的特征。與此同時,我還是“養貓的士”、“吃火鍋的士”。
人們在談論“才女”的時候,總是混淆“才”的特質與“女”的特質。其實“才女”是較具有男性氣質的一種女性,因為傳統上“才”是由男性壟斷的。女性讀書識字,成了詩人,就有了一些才子氣,與不讀書不識字的傳統女性有了差別。她們比傳統女性更有個性,更大膽表露自己的想法,她們可以出遊、飲酒、唱和,也更有家國天下的擔當。
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識階層,一般會表現得比較“溫文爾雅”,比如說,更為理性溫和,有禮貌,有節制,對美好事物有向往和追求。這些看起來比較“陰性”的氣質,其實是知識階層共有的,并非才女所獨有。而我剛才講的那些偏“陽性”的氣質,也是知識階層所共有的。也就是說,才女擁有知識階層的陰性氣質,是因為她是知識階層,而非因為她是女性,與此同時,她也具備知識階層的陽性氣質。
在“穿裙子的士”比較稀少的時代,才女身上的“裙子”顯得更為引人注目。一些比較淺薄的男性,過于重視她們作為“女”的一面,對于這些繼承了中華文化傳統的詩人,隻強調她們身上的女性氣質。其實,要找這樣的女性氣質,又何必到才女身上去找呢?我們今天的才女,隻需要好好修煉作為“士”的氣質,而無需刻意修煉作為“女”的氣質。
您走上詩詞道路,得到過哪些女性的幫助?
我的導師和對我學詩幫助最大的幾位師長都是男性,我非常感激他們對我的教導和嚴格要求。今天的女性有條件接受平等的教育,應該取法乎上,不必覺得自己有什麼特殊。
對我影響大的幾位女性,并不是直接教我寫舊體詩的。
我六七歲的時候,我母親鼓勵我:“你可以試着寫詩。”我母親是知青,他們那代人說的“詩”是指現代詩,我一開始是寫現代詩的。人是不會自動知道自己應該寫詩的,需要一個人告訴她“你可以寫詩”,這個人其實對詩人的文學生命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後來,時任《詩刊》編輯的李小雨先生看到了我的詩,對我多有鼓勵。她當時說了一句話:“你其實可以寫舊體詩。”我當時是抗拒的,說:“我這輩子是不會寫舊體詩的。”現在看來,真是一個早就破了的flag。
冥冥之中鼓勵着我的,其實還有我的太奶奶,也就是我奶奶的母親。她生活在清末民初,與丈夫詩詞唱和了一輩子,留下一本自己編的集子。“文革”期間,我爺爺不得不忍痛把這本集子燒掉了,實在是特别可惜的事。我奶奶也能寫詩,我小時候還見過她因為想念兒子,寫下兩首七絕,都是押平水韻的,我還抄下來了,但我也沒能見到她其它的作品,這也是很可惜的事。
我奶奶和太奶奶的詩也許不見得特别出色,不足以進入文學史,她們的作品也沒能流傳下來。但她們讓我從小直覺地認識了這樣的女性:她們認真地學習過作詩,能夠熟練地運用格律和句法的規則,能想到用詩詞來表現她們的真情實感、記錄她們的人生大事。後來我知道了,像這樣的女性,在清代和民國還有很多。而且她們離我這樣近,是跟我血脈相連的。
人們總是感歎中國的文脈中斷了,其實想想,她們離我們也不遠的,不過是我們的奶奶和太奶奶。我雖然沒有見過我太奶奶,也沒有見過她的詩,跟我奶奶的交集也不多,但她們的存在足以鼓勵我,去好好地看書,把她們被從這個世界上抹去的詩再寫出來。我們中華的文化就是這麼強韌,可以靠閱讀在斷層後一次次地重生,不需要口傳面授,隻需要祖先給我們一個信心,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
還有我媽媽小時候的保姆,做了一輩子丫鬟,沒有機會上學,卻自己學會了認字,看了一輩子《紅樓夢》。她的存在,也給我很大觸動。我想,如果我生在那個時代,或許也會是一個偷偷學會認字的丫鬟,一個學詩的香菱,或者運氣稍微好一點,像我太奶奶那樣,躲在深閨裡,給丈夫寫詩。我也許會很卑微,但我一定是愛詩的。過去一定也有我這樣的人,将來一定還會有。
您怎樣看待女性詩詞創作的前景?
女性創作,在中國曆史上是少的,是異質元素。但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不斷地包容吸納異質元素。寒庶的孩子可以上升為士族,異族的孩子可以漢化為華人,那麼,原來不承擔中華文化傳統的女孩子,隻要時機成熟,也可以擔負起中華文化的傳統來。隻要你足夠聰明,中華就不會浪費你的才華;隻要你熱愛中華文化傳統,中華就不會辜負你的深情。從前沒有過的,不代表以後不會有。我相信,未來的女性中,會湧現大量一流的詩人,她們将擔負起中華文化的傳統。
能否給學習詩詞創作的女生提一點建議?
不要覺得自己有什麼特殊,要老老實實繼承三千年來以男性為主的古代士人創造的詩學遺産。不要去想什麼“女性天然的優勢”,即使用女性口吻寫作,也不要直接自己出場,而是要學習男性模仿女性口吻的方法。用自己的口吻出場,僅限于像過去的男性士人一樣詠懷言志的時候。
嘉賓趙郁飛文學博士,吉林大學青年教師。研究方向為明清至近代文學、女性詩詞、網絡詩詞等。在《文學遺産》《中國詩學》等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出版《晚清民國女性詞史稿》等。
趙郁飛老師,您好!您的研究方向其中一項是女性詩詞,能否簡述下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傳統?
中國女性文學創作其來有自。《詩經》即記錄了大量女性詩作,為文學史家林庚感性地稱為“女性的歌唱”。然而自此迄明代,女性詩人的出現幾乎是偶然而随機的,即文采卓著如蔡琰、謝道韫、李清照者,亦可謂“獨闖文壇”。直至明代才打破“有傳統而無系統”的狀況,開始出現女性文學家族的傳承,再至清代,女性文學的發展始稱群星麗天、蔚為大觀,胡文楷《曆代婦女著作考》收錄女性作家四千餘,其中清代占3660人。且清代女性文壇、女作家的生存狀态與創作意識頗透露出一些富于現代氣息的片段;至近代随男女平等思想資源的滲入,中國女性文學呈現出全新的面貌。整體可概括為:曆史悠久、逐代走高、至清代臻于極盛。
您覺得當代對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研究情況如何?
對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的研究,實際上在民國時即掀起熱潮,最早的通代婦女文學史誕生于1916年,其他專門論著、總/選集等等也在繼承了清代文獻的基礎上出現了很多成果。近數十年即在現代學術規範下,由起初的李清照研究一枝獨秀漸次向廣、深、細發展;特别是近些年,明清女性文學研究可謂碩果累累,越來越多的學者選擇将目光投向此領域,令人欣慰。另外,北美漢學界的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研究也為國内提供了珍貴借鏡。
八卦一下,您最喜歡的女詩人/詞人是誰?
研究工作要求眼光博廣而用心平允。以個人取向來說,偏愛兩位杭州人——清代吳藻、近代陳小翠。
嘉賓劉能英中國作協會員,中國自然資源作協駐會簽約作家,中國地質大學特聘駐校作家,魯院第22屆高研班學員。
劉能英老師,您好!一年一度的三八節又到了,在這特殊的日子裡,您既為女性同時也是一位詩詞愛好者,并且還是一位詩詞編輯。您曾經工作于《詩刊》社,近幾年又跟蔡世平老師一起主編《詩詞月曆》等書,對女性的寫作以及以女性為對象的寫作,有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心得嗎?
答:每年到這個時候,總會涉及女性寫作或是寫作女性的話題。這兩個問題,我覺得離我都有點遠,因為我雖是女性,但相當于是男性,我所寫的對象當中,涉及女性的還真的不多,偶爾有幾首,都是應制的,我記得寫過的有:
蔔算子·唐群英
壯氣溢潇湘,試向東瀛聚。雖是閨中女子身,為國雙槍舉。
生既不逢時,死亦何曾懼。結得同盟第一人,換了江山主。
這個唐群英,是辛亥革命先驅之一,跟鑒湖女俠一個級别的人物,雖是閨中女子身,為國雙槍舉,妥妥的男子漢氣概。
減蘭·谒昭君墓
茫茫漠北,一捧黃沙埋國色。我谒之時,綠葉成陰子滿枝。
漢家風度,千百年來猶可睹。不為君顔,隻為黎元社稷安。
王昭君雖也是深宮女子,看似柔弱,做的也是安社稷撫黎元的爺們兒的事。
西江月·劉外婆
一襲青衫昨補,滿頭白發今盤。布鞋初入大觀園,到處繁華照眼。
生活已然清苦,言辭何必尖酸,總将笑意綻衰顔,算有神仙也羨。
真正寫女性,當女性來贊美的,還就是這首劉外婆。
當然,我的作品中,還寫過許多懷念、祭奠我母親的,說來也慚愧,回過頭來細讀這些作品,也全然沒有從女性的角度來描寫過她,我母親這一代人,母性特點很鮮明,但女性特點乏善可陳。我母親一生在田間勞作,勞動強度、穿着、都跟男人無異,我甚至從來沒有見過我母親紮過辮子,别過發夾,擦過雪花膏之類的。
我雖然有個弟弟,但他從小身體瘦弱,是以我們家從小就把我當男孩子養,我記得我填過一首詞:
攤破浣溪沙·野趣
為采池邊那朵花,草蟲驚我我驚他。偶見槐陰陡坡下,有西瓜。
解帶抛衣斜過坎,屏聲斂氣倒攀崖。隔岸卻聞村婦喊:小心呀。
從這首詞裡,可以看出,我妥妥就是一個調皮的混小子。
是以,無論我是作為女性寫作者,還是為女性而寫作,都是有愧的。
您認識的當代女性詩人當中,您最喜歡哪些人的作品?她們的作品各有哪些特點?
我所認識的幾個女性詩友中,紅霞姐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個,2012年我們共同參加《秦中行》歌行體詩歌大賽頒獎典禮,她喜歡打扮,也會打扮,總是收拾得漂漂亮亮,一年四季喜歡穿裙子,女性十足,但第一次讀她的作品,《安塞腰鼓》,寫得大氣磅礴,飛沙走石,不看作者,真以為是男人寫的。
那一次頒獎會,還認識了安徽籍選手王勤,她是我見過的表裡如一的女性詩人之一,跟周燕婷姐、宋彩霞姐、奚曉琳姐一樣,外表溫順,柔弱,詩也寫得含蓄、纏綿。特别是燕婷姐那句“雨驿風亭休怯酒,長條恰夠佳人手”,至今還在回味。當然,以上這些朋友,都是見過面的,還有許多沒有見過面的,比如葉嘉瑩的“對酒須拼沉醉,看花直到飄零”,素衣的“重來我在東風外,隔着桃花看路人”等等。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跟何其三認識的,(其三,你還記得我們是怎麼認識的嗎?)我跟她算是一家人,都是自然資源局的公務員,雖說一家人更親近一些,但每次讀她的作品,隻要感覺不太好,就一點情面不給她。她的作品,每有奇思,卻總是疏于細節,這本該是男人易犯的錯,沒想到她作為女性詩人,比男性犯的更多。以前總是直接在她的朋友圈裡留言,後來想想,她也是名家了,應該顧及一下她的感受,于是轉到私聊。她倒是滿不在乎,甚至很樂于跟我交流。我覺得好朋友之間就應該是這樣。在朋友圈給你點個贊,是很簡單的事,動動手指就行,但若想指出你哪兒不足,則需要燒好半天腦,還擔心萬一措辭不當或是辭不達意,得罪了人。這方面我跟她已經達成了共識,互相之間,隻說缺點,不說優點。公開點評作品也是這個态度。
您在寫作這條路上,得到過哪些名家的指點?
答:寫詩十年來,我得到過太多人的指點,可以說,凡是跟我有過交集的人,不管見面沒見面的,有心還是無心的,我都或多或少受過他們的教益。記得有一次跟熊東遨老師一起在晉江采風,他跟我說,女性寫詩,就該有女性的樣,太剛易折。
我覺得這話說的真有理,但也不全對。我覺得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應該具有雙重性,蘇東坡既有“大江東去”的豪放,也有“不思量自難忘”的婉約。李清照亦有“生當作人傑”男性的氣概,亦有“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女性的嬌柔。
是以,我的寫作,還是很随性的。導緻多半時候男性化,熊老師說的有道理,女性寫作還是應該有個女性的樣,今後應該慢慢多從女性角度來寫,或者說多為女性而寫。
嘉賓何其三安徽宿松人。出版詞集《何其三詞三百首》(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詩集《何其三絕句三百首》(黃山書社)。
何其三老師您好!您已出過個人作品集兩本,您的大作每次在小樓刊發時,都會有詩友找您購買個人詩集。您在詩詞圈裡算得上一位"高産"女詩人,請問您是怎麼跟詩詞“相遇”的呢?
與詩詞相遇完全是個偶然。我父親對詩詞感興趣,我也是以很早就與詩詞有接觸。有段日子,恰好有空閑的時間,于是決定把興趣變成愛好,并開始看格律方面的書籍。與詩詞相交的過程,于我來說是一個洞開窗戶的過程。窗子開了,透過這扇窗,我看到了美不勝收的别樣的風景,生活也因為這扇多開出來的窗子,變得精彩紛呈。
請您談談古人和今人在詩詞創作的優勢劣勢各有哪些?
有人認為詩詞已經沒有了生存的土壤,是以也沒有生存的必要。這種論調過于悲觀,我不贊同。生存的土壤肯定是有的,隻不過比較貧瘠而已。文言文是中國古代官方層面的專用文字,是書面語言。随着時代的發展,文言文退出了曆史舞台,現在隻出現在博物館和研究文獻之中,相應的,以文言文為基礎的詩詞,确實有它的特殊性,它有格律這個門檻要過。詩詞的格律要求,無形中設定了門檻,這個并不算高的門檻攔截了一波人。
我私下裡把古人和今人在詩詞創作上的優勢劣勢作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優勢劣勢各自有之。我認為古人在大氣候上占優勢。古代以詩取士,詩人可以借此揚名立萬,可以憑此平步青雲,這對詩詞的促進和刺激,無疑是巨大的,唐詩宋詞是以達到巅峰也毫無懸念。必須承認,屬于詩詞的最好的時代,已經如煙雲般消逝了。還有,詩詞是古人的日常,滲透到生活的每個角落,而今人的日常與詩詞毫無瓜葛。與古人比大氣候不行,氛圍和重視程度也等同雲泥。有人或許會問:難道今人一點優勢都沒有嗎?也不盡然。比起古人,我們學過實體、化學、數學、英語,懂的東西多,知識面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隻攻文學,隻讀死書的已不多見,同知識結構比較單一的古人比,今人的思維更活躍,生活圈更廣闊,寫作内容更豐富,這是我們的優勢。
當代人是怎麼看待詩詞“傳”與“承”?
詩詞特有的語言結構,使它含蓄,婉轉,帶有特别的意趣和美感,字少意多,以一當十,這反而使詩詞的内容和意境發散性更高,也更顯古典風雅,配上特有的音韻規則,讓詩詞獨特的美近乎天成。淵博的學識,深厚的文化底蘊,尤其是豐厚的舊學功底,是詩詞作者駕馭詩詞的缰繩,其實這就是“承”。
有人說我們現在寫的詩詞是高仿品,這個觀點我不認同。我看了好多今人的詩詞作品,他們并沒有一味模仿,很多作品優秀得讓人眼前一亮,品過之後餘香滿頰,毫不誇張地說,同唐詩宋詞相比,也毫不遜色。原因何在?那就是在繼承詩詞古典雅正和熟練掌握格律的同時,加入了自己的東西和時代的元素。作品裡凸顯了自己的個性和打上了時代的印記,散發着濃郁詩味詞味的同時,也帶有了現代的風尚,這就是今天詩詞作者呈現給讀者的真品正品而不是仿品,完全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何仿之有?
現在我們像仰望星空一樣,仰望着前人,千百年後我們的後人終将仰望我們。要将詩詞的接力棒,傳遞到他們的手上,讓詩詞代代相傳,這其實就是“傳”。還有人說,當代那麼多優美的古風小文,古風歌詞,屬于詩詞傳承的範疇嗎?我認為不是。那些東西是非古的,是僞古的,不過借點古味,營造一種仿古氛圍。但也沒必要全盤否定,它比詩詞通俗,更容易為大衆接受,閱聽人面更廣。可以說它是詩詞的近親,對傳承詩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當然,我并非提倡一味地向現實低頭。要堅持守中有變,變中有守,發揚相容并包的精神,吸收和接納有用的,才能讓詩詞煥發新的活力。
都說詩能言志,何老師,您在詩詞創作中怎麼看待“托”與“寄”。
小衆文學的劣勢在于,我們的現實生活或許不需要它,但我們的精神生活有了它,會變得更美好。它讓我們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實,它可以撫慰我們的心靈,進而成為人們的精神寄托,這就是詩詞生存的土壤。要創造出好的作品,需要有情懷和寄托。除精神寄托外,創作的作品,也要有寄托,要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美人香草,并非實際上的美人香草,要看到那些附着在曆史虛鏡上的形聲色意。自古以來,秦時明月,漢時邊關,南朝煙雨,宋代殘陽......曆史的風雨煙雲,或托于古巷,或附于丘阿,我們或以詩表,或以詞生。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中,那深深的印痕,其實都可以賦之于詩詞,這就是“托”。寫詩詞有時如同解數學題,要大膽想象,小心求證,善于生發和鋪展。拿起筆的同時,放飛想象,箋紙鋪開,就不要把自己當做普通人,腦洞要大開,要能上天,能入地,要無所不能,這就是要善于“寄”。一個事物,單從表面來寫,未免膚淺,如果想象它的前世今生,想到它獨特之處和經曆,就可以展開,就可以生發。一塊石頭,可以聯想到精衛填海,聯想到曹雪芹的《石頭記》,聯想到鄭闆橋的竹石圖,聯想到它曆經億萬年所經曆的滄桑。深入到事物中去,深入到時間深處,去探尋它的三生因果,寫出它的今昔對比,寫出興衰和滄桑,寫出它們的命運,把它們拟人化,或把人物化,人和物平等對待,那麼草也不是單純的草,石頭不是單純的石頭。總之,世間的萬事萬物,詩人都可以用生花妙筆,賦予它情感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