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樂夜話,每天胡侃和遊戲有關的屁事、鬼事、新鮮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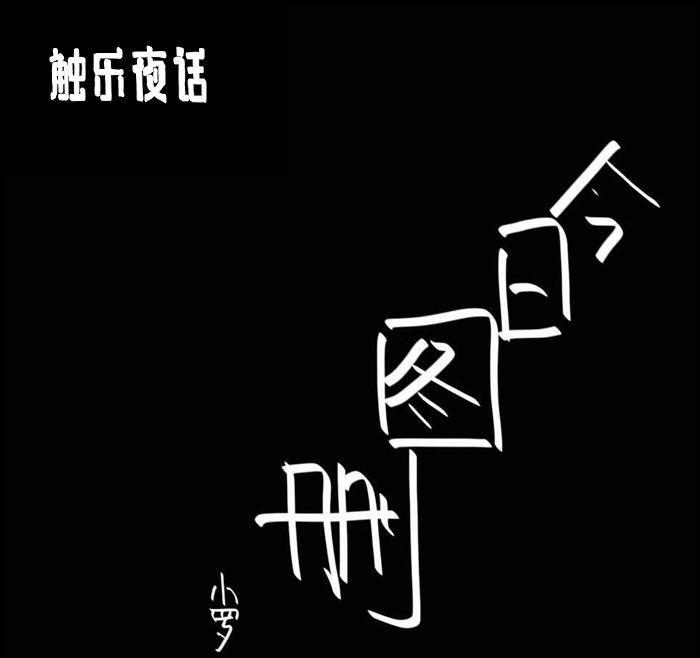
圖又無了!(圖/小羅)
在春節前幾天,有一個叫“啫喱”的社交軟體悄然流行,一度還登上了國區App Store免費榜的榜首。我是從同僚袁偉騰老師那裡收到好友邀請的。他分享給了我,我們又分頭分享給了其他同僚。
作為社交軟體來說,啫喱的核心玩法其實并不新鮮,就是虛拟形象+虛拟社交——說白了,以前的QQ聊天視窗加上旁邊的QQ秀不就是這種玩法最古早的呈現嗎?可能是最近這些年産生了許多新的概念,人們也有了比較多元的社交需求,是以這些軟體又像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我之前也多多少少嘗試過另外幾個類似玩法的新産品,但我現在連它們的名字也想不起來了……可見,哪怕能用上新的概念,哪怕經典的設計思路已經擺在那兒了,要把一款社交軟體做得受人歡迎還是不容易。
但啫喱跟那些産品似乎有所不同。首先呢,它提供給使用者的捏臉和換裝選項,雖說數量不多,自由度也不高,但審美是過關的,甚至可以說是讨喜的。其次呢,它的社交理念也比較合我的心意,它不鼓勵使用者跟陌生人交朋友,反而設立了每位使用者隻能添加50名好友的限制。在它的産品文案裡,它說自己的定位是“友情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目的是讓使用者能在自己的核心朋友圈裡展示真實的自我。
今天的我!
另外,它提供了相當簡單有趣的互動方式。加入啫喱的朋友們會出現在同一個“廣場”上。在這個廣場,你可以看到朋友們的虛拟形象,看到這些虛拟形象在做什麼和說什麼,甚至還能看到朋友本人的大緻位置(如果雙方願意開放的話)和手機電量。想跟朋友互動的話,可以簡單地戳一戳對方的虛拟形象,對方将會在手機上收到一個提醒,也可以直接在背景的聊天視窗發起對話。
當然,這些設定并不足以吸引所有人。當我和袁老師暢遊啫喱時,我也發現并不是所有同僚都喜歡這種難以被歸類的實驗性社交軟體。陳靜老師和祝思齊老師全程都不感興趣;馮昕旸老師試穿了幾件衣服以後表示“這跟咱們《最終幻想14》差遠了”,但還是換上了粉色發辮和JK制服,遠遠地在背景裡遊蕩;楊宗碩老師給自己取名“京廣發”,又換上一套白色的背帶褲——不知道有什麼寓意,但後來他不再登入,“京廣發”也就一直以一種僵硬的姿勢矗立在原地,像一座沉默而孤獨的燈塔。
我喜“啫喱的原因之一是,我能從中觀察到我身邊的同僚們(哪怕僅有幾位!)在不受限制的時候是如何展示和表達自己的,并且思考這些展示和表達是否能跟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性格互相印證。
說起來有點複雜,舉個例子,就拿祝佳音老師來說吧,我每每看到他穿着永遠搭不到一塊兒的衣服(比如上身穿黃色的格子衫,下身穿粉色的條紋短褲,手裡拿着一個綠色的汽水罐),小人要麼是臉朝下趴着,地上一灘血的,要麼是平躺在地,雙手交叉放在胸口的——整體顯示出一種又喪又欠。他的小人平常也不太說話,就是靜靜地站在一旁,感覺在暗中觀察;僅有的幾次說話都是關于工作壓力的,可能是用來震懾其他同僚的也說不定。
但有些同僚看起來完全不會被震懾到。比如說袁老師吧,他是除我以外另一位啫喱愛好者。作為全編輯部最年輕的同僚,袁老師不但在日常生活中顯示出令老人們都驚歎的青春活力(一口氣練習幾十個小時直到一命通關《師父》,以及此時此刻正在用工作時間打“刀塔”),而且在啫喱裡也不遺餘力地展示出這種驚人的精神頭兒。
袁老師每天操心的事情隻有:稿子寫不完了、遊戲打不完了和毛絨玩具又髒了……
跟祝老師不同,袁老師喜歡嘗試軟體裡最時髦、最漂亮、最引人注目的那些服飾,比如粉色的西裝外套,内搭亮眼的白色羽絨服,新出的長款海軍服也是第一時間就換上!而且他的小人在螢幕上永遠是那麼快樂——幾乎令人嫉妒的快樂你知道嗎?不是在快樂地奔跑,就是在扭動着比心,就連偶爾歎着氣說“稿子的思路卡了”,過了幾個小時再看,小人就已經在一個畫闆前激情創作了!小人頭頂上的氣泡寫着:“又有思路了!”
快樂的袁老師在春節期間經曆了慘無人道的催稿……(我猛戳!)
啊,真令人生氣,你說是不是?我隻比袁老師大了4歲,心裡還隻當自己20歲呢,有時候看到未成年提示還會多想一秒說的是不是自己呢,在袁老師和馮老師被我招進來之前我一直都是編輯部裡年紀最小的呢——我怎麼就老了呢?而且在袁老師的面前,我格外意識到自己的衰老。
我和袁老師的差別在啫喱上非常明顯,比起袁老師那個總是積極進取的青春小人,我的小人就像在國貿返工的任何一個上班族女性一樣,表面上還撐着一個精緻靓麗的外殼,内裡的精神早已被生活幹翻。我會花很長時間精心打扮我的外表——眼睛眉毛嘴唇腮紅自然不用說了,都是選最好看的;衣服那可更講究了,除了一身完美搭配的服裝以外,我還會仔仔細細地挑選配飾,從帽子到項鍊到耳環到手上拿着的小道具,沒有一個不是大膽搭配,小心選用的。
但這樣的我每天都幹嘛呢?我最喜歡幹的事情是放空,也就是用各種不同的姿勢躺在地上,有時呈一個大字型,有時翹着二郎腿,看上去既若有所思又頭腦空空,好像正在思考全宇宙人類的命運,又好像什麼也沒有想……
如果說啫喱有一刻曾經打動過我,那就是它讓我想起了多年前上網的感受。多年前上網的時候,哪裡會去想什麼“做不做真實的自己”這種問題呢?哪裡會去管别人對自己的評價?而别人的評價哪裡又會像今天這麼糟糕?就隻管做自己呀!就隻管說話,隻管交流,隻管分享,隻管吵架好了——吵架又有什麼關系呢?總歸是沒有人會害了你的。總歸你是安全的。
現在這種安全感已經少有了。朋友圈分組屏蔽加3天可見,既不讓人靠近,也不讓人了解,能不說話的時候就絕不說話,大部分轉發都是關于工作。但哪怕做到這樣也不夠,隻要你待在朋友圈裡,待在那個倒黴的、麻煩的、想删掉大多數人但大多數人都不能删掉的朋友圈裡,你就會看到不想看到的東西,你就要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資訊洪流,并忍受随之而來的劇烈情緒波動……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絕不能再忍耐了,但想了想還是決定再忍耐一會兒。我讨厭這樣。
與之相比,啫喱确實一度讓我感到溫暖舒适,但這并不代表啫喱是個理想的社交軟體啦。事實上,在最近一兩周裡,因為它的更新進度緩慢,能玩的新鮮事兒都玩遍了,熱情如我和袁老師也逐漸不再釋出自己的動态。我也并不認為啫喱能夠解決那些屬于時代的病症,更有可能的是啫喱繼續發展下去,直到那些病症找上門來,我們又不得不迷茫地遷徙到下一個平台……啊,你能了解嗎?你不斷地逃跑,從一處逃到另一處,但那個東西總是追上來。
最後你隻能說,這世界已不是我的地頭,就當我在宇宙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