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衆日報記者 朱子钰 李夢馨 通訊員 王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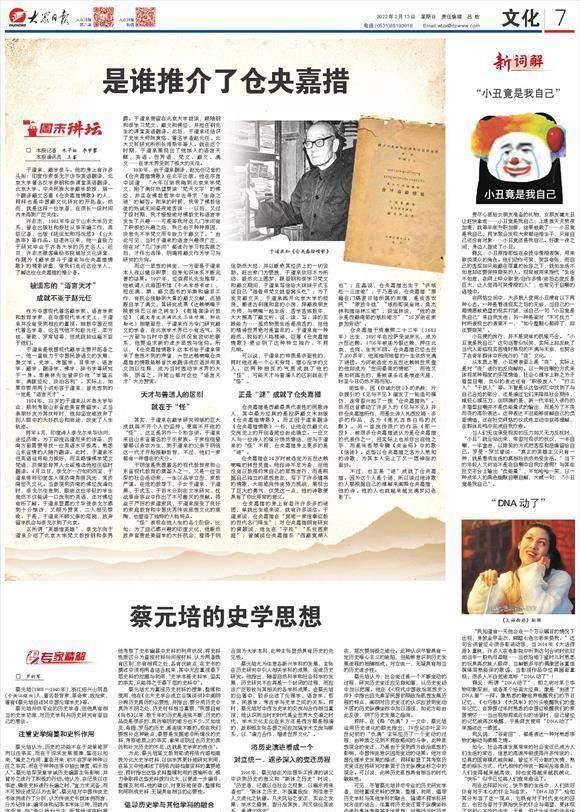
于道泉和《倉央嘉措情歌》
于道泉,藏學泰鬥。他的身上有許多頭銜:印度作家泰戈爾訪華英語翻譯,北京大學著名漢學家鋼和泰課堂英語翻譯,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藏學教授,第一個翻譯藏文名著《倉央嘉措情歌》的人,同樣也是中國藏文化研究的開拓者。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學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未得到廣泛關注。
許志傑,1983年畢業于山東大學曆史系,曾在出版社和報社從事采編工作,進階記者,出版《陸侃如和馮沅君》《山大故事》等作品。自退休以來,他一直緻力于研究畢業于齊魯大學的曆史名人。近日,許志傑做客垂楊書院城社文化講堂,作題為《藏學泰鬥于道泉與倉央嘉措情歌》的精彩講座,帶我們走近這位學人,了解這位倉央嘉措的推介者。
被遺忘的“語言天才”
成就不亞于趙元任
作為中國現代著名藏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學家,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于道泉并沒有受到相應的重視。細數中國近現代著名學者,論名氣他不如趙元任、李方桂、箫乾、羅常培等,但成就卻絲毫不亞于他們。
于道泉是大陸現代藏學主要開拓者之一,他一直緻力于中國民族國文的發展,集文學、史學、考據學、目錄學、語言學、藏學、翻譯學、佛學、辭書學等研究于一身。季羨林先生曾評價他“學富五車,滿腹經綸,淡泊名利”。實際上,如果非要用兩個詞形容于道泉,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語言天才”。
1924年,23歲的于道泉從齊魯大學畢業,順利考取山東省赴美官費留學。正當親朋好友為其歡呼時,他卻堅定地放棄了别人眼中的大好機會和前途,改變了人生軌迹。
同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通路,途經濟南。為了迎接遠道而來的詩聖,濟南方面需要尋找一位英語水準極高、熟悉山東省情的人随行翻譯。此時,于道泉不但英語運用能力極好,而且略懂佛學梵文梵語,濟南教育界人士遂推選他擔任臨時翻譯。4月22日,泰戈爾一行如約而至,于道泉帶領印度客人觀濟南秀麗風光、賞濟南悠久文化。當參觀到濟南的佛經流通處時,泰戈爾注意到,眼前這位年輕的學生竟然不僅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還對佛經有所了解。于道泉顯露的才華使泰戈爾感到十分驚訝,又頗為贊賞,二人相見恨晚。于是,于道泉不顧父親的阻撓,放棄留學機會與泰戈爾到了北京。
正所謂“英雄惜英雄”,泰戈爾向于道泉介紹了北京大學梵文教授鋼和泰男爵。于道泉便留在北京大學就讀,跟随鋼和泰學習梵文、藏文和佛經,并擔任鋼先生的課堂英語翻譯。此後,于道泉還結識了史學大師陳寅恪、著名學者趙元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等人。就在這個時期,于道泉展現出了他驚人的語言天賦,英語、世界語、梵文、藏文、滿文……在學術界受到了極大的關注。
1930年,由于道泉翻譯、趙元任記音的《倉央嘉措情歌》在北平出版。他在序言中說道:“六年以前我跑到北京來學梵文,抱了滿懷熱望要讀‘梵天文字’的佛經,并且在佛教哲學中去尋求‘生命之謎’的解答。剛來的時候,我帶了佛教信徒的熱誠無間晝夜地苦讀……以後,又過了段時期,我才慢慢地對佛教史和語言學發生了興趣……可是等我對這幾門學問有了積極的興趣之後,我已由于種種原因,決意先不學梵文而專緻力于藏文了。”由此可見,當時于道泉的語言興趣很廣泛,但在對“幾門學問”都進行學習和實踐之後,才作出選擇,明确将藏文作為學習與研究的方向。
而這一思想的轉變,一方面是于道泉本人夜以繼日積累,自身知識體系不斷完善的結果。1927年,經袁同禮先生推薦,他被調入北海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擔任滿、蒙、藏文圖書的采集和編目工作,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藏文文獻,還抽暇自學了滿文,其研究成果《達賴喇嘛于根敦珠巴以前之轉生》《乾隆禦譯衍教經》(藏文原文及滿漢文三體對照,附校勘記)相繼面世,于道泉作為專門研究藏文的學者,在北京學術界已小有名氣。另一方面與當時中國社會狀況有密切的聯系,他要追求新的進步思想與信仰。是以,《倉央嘉措情歌》這本書給于道泉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聲譽,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情歌能夠首次被翻譯成漢語并用英文加以注釋,成為當時轟動學術界的大事,胡适之、許地山都對這位“語言天才”大為贊賞。
天才與普通人的差別
就在于“怪”
其實,于道泉在藏學研究領域的巨大成就離不開個人的堅持、更離不開他的“怪”,這正是另外一個形容詞。于道泉來自山東省著名的于氏家族。于家祖祖輩輩都以務農為生,到于道泉的父親于明信這一代才開始接觸教育,不過,他們一家都有一種潛在的天分。
于明信是大陸著名的現代教育家和山東省現代教育的創始者之一,又是一位資深的社會活動家,一生以品學立世,家教嚴謹。在他的教導下,子女于道泉、于道源、于式玉、于若木分别在文學研究、抗戰革命事業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得益于嚴厲的家道家風,于道泉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中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的熏陶,也塑造了獨特的人格特點。
“怪”表現在他人生的各個階段。比如,為了自己感興趣的印度文化,他斷然放棄官費赴美留學的大好機會,惹得于明信勃然大怒,并以斷絕其經濟上的一切資助、趕出家門為要挾,于道泉依舊不為所動,毅然北上圓夢;跟着鋼和泰學習梵文和藏文期間,于道泉寫信給大妹妹于式玉說自己“每餐用梵文就着窩頭吃”;為了攻克藏文關,于道泉離開北京大學的樓房,搬進古刹雍和宮的小房,拜藏族朋友為師,與喇嘛一起生活,苦學苦練數年,大大提高了藏文聽、說、讀、寫、譯的實踐能力……雖然物質生活是清苦的,但他的精神世界絕對是富足的。于道泉有一種超然、脫俗的人格精神,巨著《倉央嘉措情歌》便證明了這種特立獨行、不同凡響。
可以說,于道泉的特質是多面性的,同時他還是一個心無旁骛、潛心治學的文人。這兩種相反的氣質成就了他的“怪”,可能天才與普通人的差別就在于“怪”。
正是“謎”成就了倉央嘉措
倉央嘉措是西藏最具代表性的民歌詩人,其中最為經典的是拉薩藏文木刻版《倉央嘉措情歌》。而正因于道泉翻譯《倉央嘉措情歌》一書,讓他在漢藏文化交流史上的開創者地位由此确立。一位文人與一位詩人的緣分悄然締結,但與于道泉的“怪”不同,倉央嘉措身上更多的是“謎”。
倉央嘉措在14歲時被標明為五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他作詩不足為奇,但他沒有以教規限制自己的思想言行,而是根據自己獨立的思想意志,寫下了許多纏綿的情歌,大膽地向傳統勢力挑戰,展現出了巨大的勇氣,僅憑這一點,他的詩歌便具有了非比尋常的意義。
倉央嘉措的身上有着許許多多的謎團,單就出生地來說,就有許多說法。于道泉說,倉央嘉措在“寞地一家信奉紅教的世代名門降生”;對倉央嘉措頗有研究的黃颢說,他生在“宇松”“系貧困家庭”;曾緘說倉央嘉措系“西藏寞湖人也”;莊晶說,倉央嘉措出生于“沃域松—三窪地”;于乃昌說,倉央嘉措“原籍在門隅夏日錯所屬的派嘎,是貧苦農民”“做放牛娃”“域松即吳金林、桑傑林和措結林三地”;段寶林說,“他的故鄉是西藏南部的域松地方”“15歲前在家參加勞動”。
倉央嘉措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生,1697年在拉薩受坐床禮,成為六世達賴。1705年被誣為假達賴,押往北京,去向、生死不明。倉央嘉措已經去世了300多年,他孤獨而短暫的一生依然充滿了謎團。為何被標明為五世達賴轉世靈童的他卻成為“世間最美的情郎”,而他又是如何離去的,是被謀殺還是浪迹天涯,時至今日仍然不得而知。
前些年,因《非誠勿擾2》的熱映,片中援引的《見與不見》催發了一輪造句模仿,連帶着興起了一撥“倉央嘉措熱”。然而這首感動了許多人的《見與不見》并非倉央嘉措所作,而是女詩人紮西拉姆·多多的作品,名為《班紮古魯白瑪的沉默》。另一首流傳很廣的作品《那一世》,被很多倉央嘉措迷認為是倉央嘉措的代表作之一,但實際上也并非出自他之手,而是朱哲琴專輯《央金瑪》中的歌《信徒》。這些以倉央嘉措之名為人熟知的詩歌,為其本人籠上了又一層神秘的面紗。
不過,也正是“謎”成就了倉央嘉措。因為這個人是個謎,是以讀過他詩歌的人都根據自己的了解來闡釋倉央嘉措,他的詩、他的人也就越來越充滿夢幻色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