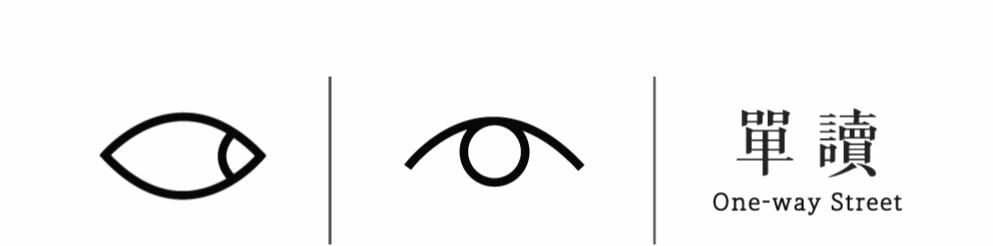
張潔(1937 年 4 月 27 日-2022 年 1 月 21 日)
當地時間 2022 年 1 月 21 日,作家張潔在美國因病逝世。張潔曾憑借《沉重的翅膀》和《無字》,兩次獲得茅盾文學獎,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徐泓曾于 2014 年寫作短文《速寫張潔》,在聽聞消息後,授權單讀重發此文,以紀念張潔。徐泓與張潔交往廿年有餘,這篇文章生動描繪出張潔的才情與性情,不管是對文字、繪畫,還是紛雜世事,她都曾一往情深。
原文連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79e2710102z3r9.html
速寫張潔
撰文:徐泓
77 歲(2014 年)的女作家張潔,十月下旬,在北京舉辦個人油畫展。開幕式上,她雙手作揖,向文壇和讀者告别。灑脫,決絕。
現在,她已經回到了美國的家中。
去年,她賣了北京二環路邊的房,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區買了一套小小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老房子,簡陋,但樓下有一個公共大花園,很美。”
她常常坐在花園裡一棵樹下的長椅子上。她說:“那個角落裡的來風,沒有定向。我覺得那從不同方向吹來的風,把有關傷害、侮辱、造謠、污蔑等等的不好的回憶,漸漸地吹走了,隻留下了有關朋友的愛、溫暖、關切、幫助等等的回憶。”
這次回來,張潔的心情确實比以往平和。感謝、感恩之情,常在嘴邊上、笑容裡。
張潔的油畫作品
***
我和張潔交往二十年,印象中的她,心直口快,憤世嫉俗。從不超脫,從不置之度外,也從不媚俗。無論身内事,還是身外事,她左突右沖的,糾結着、焦慮着、疑惑着、挑剔着,但一往情深。
文如其人。王蒙也曾經為張潔獨特的文字魅力驚歎:“有時坦率得近乎愚傻,熱烈得近乎爆炸,憂郁得近乎自戕,勇敢得近乎以身試陳法陋習。”
大器晚成。張潔 41 歲才開始寫作。但毫無疑義,她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曾囊括了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國家級所有的文學獎項,被譽為“大滿貫”作家。《沉重的翅膀》和《無字》,使她兩度獲得茅盾文學獎。
她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也很高:張潔獲得意大利 1989 年度“瑪拉帕爾帝”國際文學獎;1992 年當選美國文學藝術院榮譽院士;鮮為人知的是,1986 年張潔就曾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張潔的小說作品《沉重的翅膀》和《無字》書封
張潔是個謎。
有評論家說,似乎還沒有哪一位當代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像張潔這樣從唯美走向審醜,在極其明快的風格變換中顯示出自己的文學年齡,仿佛從文學的少女時代一下子跨入了成年的時代,又迎來了文學的更年期。
10 多年前,我曾經直截了當地問過張潔這個謎底:“你為什麼從寫人性美轉向揭露人性惡?”
她說:“失望。對一切的失望。”
她對這個世界失望:《無字》以母女三代的故事寫了 20 世紀。張潔說:“這個世紀是一個大謊言橫行的世紀,是一個上當受騙、充滿比死亡還痛苦、還可怕的世紀。”
她對人性失望:“人和人之間是不能溝通的。”張潔說,“如果說亂世的不确定性多少還可以觸摸,而人性的不确定性,簡直讓人絕望。”
她對文學失望:過不了幾年文學就會被人徹底遺棄,取而代之的将是“小時代”。
她作品的風格形态轉型速度也令人驚詫。抒情的、幽默的、荒誕的、調侃的、政治諷刺的、意識流的、懸疑的,一本書一個面孔,一種别樣的閱讀體驗。張潔的才華,在于舉重若輕,遊刃有餘,不同的風格,任她信手拈來。
她說:“我不喜歡形成所謂的‘風格’,那是畫地為牢。我喜歡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當然也是一種‘野心’,看看自己能否勝任各種形态。”
文字是她的鐘愛,我多次聽到過她的表白:再沒有什麼能像我的文字那樣,讓我從容地獨立于世;我曾狂妄地說過,哪怕天下人都讨厭我,我也會因為這些文字而活得自由自在。
張潔
這次她的轉型更加勇敢、決絕。
這位“文字世界的寵兒,自行斬斷了文學家叙事的本能,放下語言的利器”,開始用畫筆再次尋找自己,用畫筆再次試探與這個世界究竟能否對話。
婚姻失敗,母親去世。張潔 70 歲以後自我放逐,生活狀态幾乎一半是“獨行俠在路上”。她背着行囊遊曆世界,她喜歡乘坐大巴,拿着一個傻瓜機,走走拍拍,走哪兒算哪兒,看到路邊小鎮合意的旅店就住下。她自嘲這是“窮遊”。“流浪的老狗”既是張潔的網名,也是 2013 年她一本新書的書名。
書中她說:“對于路上遭遇的種種,他一面行來,一面自問自解,這回答是否定還是肯定,他人不得而知,反正他是樂在其中。不過他是有收獲的,他的收獲就是一腳踏進了許多人看不見的色彩。”
張潔的世界由文字變成了色彩。于是有了這個油畫展,于是有了這個以“無字”的形式與姿态,向文壇與讀者的告别。
▼告别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