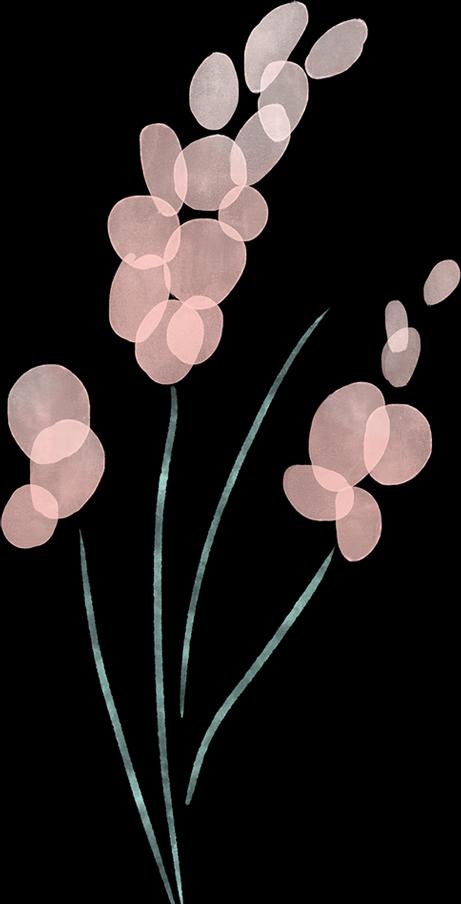
也談俄國文化的“白銀時代”
語言中總有一些用不俗的名詞,“黃金時代”“白銀時代”等都是這樣的詞彙,每個民族的文學史中似乎都有被這樣命名的時期,而此類名稱所指的繁榮或珍貴又絕不僅限于文學範疇。
如今,被冠以“白銀時代”之稱謂的一段俄國文學和文化,又突然成了我們一個熱門的話題和熱門的出版選題,報刊上以此為題的文章不斷亮相,光是以“白銀時代”為題的叢書就接踵出了四套(作家版《白銀時代叢書》六種,學林版《白銀時代俄國文叢》五種,雲南人民版《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化叢書》七種,文聯版《俄羅斯白銀時代精品文庫》四種),真可謂熱鬧非凡。
《白銀時代的星空》劉文飛
這樣一種熱鬧的場面,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從閱讀客體的角度看,20世紀之初的俄羅斯文化的确是五彩缤紛、碩果累累的。在“白銀時代”,帕斯捷爾納克所言的“天才成群地誕生”的罕見現象又一次在俄國出現。使人難以想象的是,在那短短的20餘年時間裡,在革命和戰争此起彼伏的社會背景中,俄羅斯這一無論就文化傳統還是就經濟實力而言在歐洲都并不十分強大的民族,卻向20世紀、向全世界貢獻出了一大批的大師與傑作,并為諸多文化門類在20世紀的走向開了先河,如哲學中的宗教存在主義,文學理論中的形式主義,詩歌中的阿克梅主義,美術中的康定斯基,音樂中的斯特拉文斯基,等等。那的确是一座文化的富礦,我們在近期同時推出幾套叢書,其中卻很少有相同作家或作品的“撞車”,這也能使我們強烈地意識到那一時期文化積澱的深厚。然而,由于意識形态方面的原因,這一時期的文化不僅未能在十月革命之後得到持續發展,反而受到了有意的冷淡,甚至是有意的遺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閱讀和研究。可以說,在當今的俄國,“白銀時代”也同樣是一個新的閱讀熱點。另一方面,從我們主觀的角度來看,中國讀者對俄羅斯的文學和文化一直有着一種較強的“閱讀期待”,而在蘇聯解體之後,傳統的“蘇聯文學”似乎突然“貶值”了,與此同時,新的俄羅斯聯邦卻始終未能提供出足夠多的、具有征服力量的新閱讀文本。于是,我們将期待、選擇的目光投向絢麗卻又陌生的“白銀時代”,乃是十分自然的。當然,促使我們關注“白銀時代”文化的,也許還有在20世紀之末梳理20世紀文化遺産的某種潛在願望,還有對“世紀末情結”有可能在“白銀時代”文化中得到撫慰、赢得共鳴的某種希冀,還有學術圈中欲描繪出一幅20世紀俄國文學完整畫面的刻意努力,等等。客觀的、主觀的原因,必然的、偶然的因素,共同制造出了目前這個“白銀時代文化熱”。
大陸學者關于“白銀時代”的讨論也很熱烈,單就“白銀時代”這一稱謂的來曆,就有了諸多意見。起先有人說,是俄國學者馬科夫斯基在20世紀60年代出版于慕尼黑的一本俄語詩歌專著中首次用“白銀時代”界定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國現代主義詩歌思潮;後來,有人在俄國學者的論述中發現,馬科夫斯基本人稱,是俄國哲學家别爾嘉耶夫最早提出了這一名稱;最近,又有人從俄國的相關資料中發掘出,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是俄國詩人奧楚普,他于1933年在巴黎的俄國僑民雜志《數目》上刊出了一篇題為《白銀時代》的文章。其實,“白銀時代”這個名稱是誰最早提出的并不重要,因為這個名詞畢竟不像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或昆德拉的“媚俗”等詞那樣是由作者獨創出來的概念,被賦予了特定的含義,而是一個人人都可以用,并且也一直被沿用的詞,就像“文學”等詞一樣,其内涵和指向已十分确定。我們不知道“文學”一詞是誰最早提出來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作為整體的文學持有一個大緻相同的了解。
在是否使用“白銀時代”這一概念的問題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見。至今仍有一些學者(主要是一些老輩或老派學者)很反感“白銀時代”的提法,認為它并不構成一個“時代”,他們很留戀蘇聯時期學者那個明确卻累贅的概念:“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似乎一用“白銀時代”的概念,就是擡舉了這一時期的文學,就是讓它與其前輝煌的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其後繁榮的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平起平坐了。其實,将蘇聯這一領域的主要研究者(如索科洛夫等)的研究成果與當今有關“白銀時代”的著作做一個比較,發現它們在研究的範圍和對象上并無太大的差異;再者,“白銀時代”文化的總體傾向與其前、其後文化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不能因為其持續的時間短而忽視其獨具的内涵和外延。是以,“白銀時代”不構成一個時代的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再看一看實際情況:在歐美斯拉夫學術界,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啟用了“白銀時代”的概念,大學裡一直開設有以此為題的課程。以其為内容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在俄國,這一概念也已經被廣泛地接受和使用了,就是以前那些用慣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之概念的學者也轉而采用更簡潔、更順口的“白銀時代”了;而在我們這裡,“白銀時代”的說法即便不能說深入人心,至少也已讓圈内人士耳熟能詳了。是以,現在來談論是否該使用“白銀時代”的提法,似乎也已經沒有意義了。
但是,在目前關于“白銀時代”這一概念的認識和了解上,有兩種傾向是值得關注的:一種傾向是将“白銀時代”的内涵寬泛化,另一種傾向是将“白銀時代”的性質意識形态化。
俄國文化的“白銀時代”,通常是指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之後和蘇維埃文化之前這一時間段中的文化,它橫亘在兩個世紀的交接處,時間跨度為20餘年。關于“白銀時代”的分期,目前還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它大緻的起止點還是得到了比較一緻的界定,即托爾斯泰之後和十月革命之前。當然,你可以說與托爾斯泰的後期創作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安德列耶夫等人的創作就已經顯現出了與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有所不同的一些特征;當然,你還可以說,十月革命并未能截然阻斷“白銀時代”的文化慣性。任何一個時代都與其前後時代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任何一個時期的劃分因而也都是相對的。相比較而言,“白銀時代”的劃分倒還有着更為牢靠的依據,因為,作為其開端的俄國象征主義詩歌運動,有着與傳統俄國文學迥然不同的美學風格和藝術趣味,而注重個人價值和藝術創新的“白銀時代”文化必然會在倡導集體和集權的十月政治革命後不久迅速地中止。面對這樣一個相對清晰的文學史分期,我們的一些學者卻仍想做某種“擴大化”的工作,在盡量拉長、抻寬“白銀時代”。有人欲加大“白銀時代”的規模,認為其上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限為斯大林時期的開始;有人則欲增加“白銀時代”的内容,認為它不僅應該包括當時已近尾聲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新起的無産階級文學,而且還應該包括進普列漢諾夫等的社會主義學說和列甯的國家與革命學說。在已經出版的一套關于“白銀時代”的“叢書”中,絕大部分作品都寫于20世紀20年代末或30年代,無疑已是“蘇維埃時期”的作品,“叢書”中的另一部小說屬于批判現實主義晚期,真正意義上的“白銀時代”作品也許隻有一部。我們認為,應該賦予“白銀時代文化”以一個相對穩定、相對明确的界定,否則,失去了其内在規定性的“白銀時代”概念,便會面臨外延泛化的危險,乃至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再一種傾向,便是在對“白銀時代”的了解上添加了很多的意識形态意味。上述一些人士對“白銀時代”概念的反感,其中就包含這方面的原因。他們認為,“白銀時代”的一些作家後來大多不接受十月革命,在革命後流亡國外,與後來的蘇聯文學一直處于對立狀态,因而是不應大加宣傳的。令人奇怪的是,有些鼓吹“白銀時代”文化的學者卻也持有與此相同的思維模式,他們認為“白銀時代”文化的意義,就在于革命時與現實的距離和革命後與專制的對峙。這裡,在低估或高估“白銀時代”的人士身上都出現了一個“時代倒錯”現象,即忽略了“白銀時代”是出現在十月革命之前,完全依賴其與之後時代的聯系或其在之後時代中的命運去看待它,是難以對它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的。于是,我們聽到了關于“白銀時代”文化為“頹廢”文化的指責,我們聽到了關于那一時期的作家“世界觀落後”“脫離人民”的說法。于是,我們更常在關于“白銀時代”的文字中讀到某些作家的“悲劇”命運以及關于這些命運的感慨。有意無意之間,人們在将“白銀時代”的文學等同于蘇維埃時期的“境外流亡文學”“非官方文學”乃至“持不同政見者文學”。例如,人們最近在談論“白銀時代”文學時,就時常提及包括肖斯塔科維奇和葉夫圖申科作品在内的花城版的《流亡者文叢》,有人還将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等也歸入了“白銀時代”作家的行列。這一切都在強化“白銀時代”文化與蘇維埃文化的對立,并欲在這種對立中分出一個高低來。文化與專制,知識分子在集權統治下的命運,這隻是“白銀時代”文化的一個内容,不是其全部,而且還隻是一個後來附加上去的内容。再者,對于文化與專制,也可以有多種了解。比如在談到曼德爾施塔姆的遭遇時,似乎是阿赫馬托娃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換一種社會制度,曼德爾施塔姆的命運也不一定就會好到哪裡去。最近出版的一本索爾仁尼琴傳記寫道,流亡到美國之後的索爾仁尼琴,與“金錢專制”下的美國社會同樣是格格不入的,該傳記的作者因而稱索爾仁尼琴為“永恒的持不同政見者”。可見,糾纏在文化與專制之沖突這一點上,并将這一點視為“白銀時代”文化之“重點”,是不恰當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總之,給“白銀時代”的文化添加過重的意識形态色彩,既妨礙我們客觀、冷靜地評判其價值和意義,也不利于我們養成曆史地接受文化遺産的良好習慣。
那麼,俄國“白銀時代”文化的主要意義究竟展現在哪些方面呢?我們認為,首先,是那一時代的藝術家所展現出的空前的藝術創新精神。俄國宗教存在主義者在20世紀之初開始了對現代意義上的存在問題的思考,自他們開始,“生存意義”“終極關懷”等命題成了20世紀現代主義哲學的主要内容;俄國形式主義者在20世紀之初開始了對文學“内部規律”的探讨,文學研究開始了其“科學化”的曆程,文本、語境、詞,乃至聲音和色彩,從此成了精心研究的對象;象征主義、阿克梅主義、未來主義是20世紀之初俄國現代主義詩歌的三個主要潮流,它們風格不同,主張各異,但在進行以詩歌語言創新、以在詩歌中綜合多門類藝術元素為主要内容的詩歌實驗上,它們卻表現出了共同的追求;從康定斯基起,繪畫的“三要素”被否定了,原來可以用點來構成線,用點來構成面;從斯特拉文斯基起,音樂的單階被徹底重建了,“十二音體系”極大地豐富了音樂的表現力。如今,人們意識到,20世紀是一個文化藝術上的現代主義世紀,而在世界範圍内幾乎每個藝術門類的“現代化”都起源于20世紀之初的俄國,這不能不讓人感歎“白銀時代”俄國文化人巨大的創新精神。“白銀時代”将作為一個“創造的時代”而載入人類文化的曆史。
其次,在進行空前的藝術創新的同時,這一時代的人卻也保留了對文化傳統的深厚情感,隻有以俄國未來主義詩歌為代表的“左派藝術”對文化遺産持否定态度,而那一時代大多數的文化人無疑是珍重文化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一次在回答“什麼是阿克梅主義”的問題時說:“就是對世界文化的眷念。”這個回答是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義的。在那個時代,遠至古希臘羅馬的神話,近至德國的哲學、法國的象征主義理論,都為俄國的知識分子所關注。俄國東正教中有一個“第三羅馬”的概念,認為基督教的精髓在羅馬衰落之後轉至拜占庭,在拜占庭被伊斯蘭教勢力統治之後又轉至莫斯科,因而,17、18世紀的莫斯科就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中心。雖然這一理論并未為東正教赢得世界範圍内真正的統治地位,但是,這一理論所折射出的面對整個西方文明的責任感,在俄國知識分子,尤其是“白銀時代”俄國知識分子的身上卻一直有着比較充分的展現。是以,他們敢于以世界文化的捍衛者自居,他們才可能在相對偏僻的北疆對人類的生存狀态和曆史命運做溫暖的思考。
最後,與對文化的眷念相關,“白銀時代”的文化人普遍顯現出了一種心靈的真誠。20世紀之初是一個動蕩的時代,革命與戰争此起彼伏;那也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今天充斥着世界的各種欲望在當時也曾膨脹。然而,就在那樣的時空中,俄國的知識分子卻展現出了布羅茨基所言的“文明的孩子”的赤子情懷。在兵荒馬亂的歲月,他們居然能專注地端坐在書房裡,潛心寫作;在欲望膨脹、價值重估的年代,他們始終保持着對藝術價值和自身價值的堅定信念;在充滿彷徨和疑慮的世紀之交,他們在匆忙而又認真地整理着過去世紀的文化遺産,并同時為新世紀文化的走向确定了一個基本的架構。他們的生活方式也許無法扭轉當時的社會風氣,但他們卻保持了文化的繁榮和延續;他們的思索和發現也許不是縱貫世紀而皆準的真理,但他們精神勞動的成果顯然沒有在百年或更短的時間裡“随風而去”。如今,在功利原則深深侵入文人生活的時候,20世紀之初俄國文化人的那種心境和信念是尤其讓人感動和羨慕的。
在熱烈地談論“白銀時代”文化的時候,我們也要保持一份冷靜。在閱讀中,往往有最新的東西就最時髦就最佳的定式選擇;在研究中,填補了的空白往往更受推崇,一些研究者又總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将自己喜愛、熟悉的對象“唯我獨尊化”。目前,除了少數出于意識形态立場而對“白銀時代”文化持否定看法的人士外,大部分研究者似都在毫不吝啬地鼓吹“白銀時代”。相對而言,關于“白銀時代”的冷靜看法則較少。比如說,與極具公民責任感、人道主義精神和道德感的俄國文化傳統相比,“白銀時代”的文化顯得過于關注自我和内心、過于貴族味了;比如說,在關注世界文化遺産的同時,“白銀時代”文化對俄羅斯本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和整理則相對較少,等等。隻有在注意到并思考了這些問題之後,我們才可能對俄羅斯“白銀時代”的文化有一個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