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知村神秘之處還有,這裡地廣人稀,居民超不過三百人。但卻人傑地靈,是個人文荟萃,名家會聚的風水寶地。
和我同輩的人中,就有擔任過陝西省舞蹈家協會主席的李開方。他主編了《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內建 陝西卷》《中華舞蹈志 陝西卷》,享受國務院授予的專家特殊津貼,編著有《舞蹈基礎理論》《簡明中國古代舞蹈史》《舞蹈美學教程》《舞蹈藝術欣賞》等六部,成果斐然。1975年,他為我所在銅川歌舞團編排了舞蹈《送糧路上》,演出大獲好評。其間我們親密合作,深感他為人之寬厚大氣,藝術上才華橫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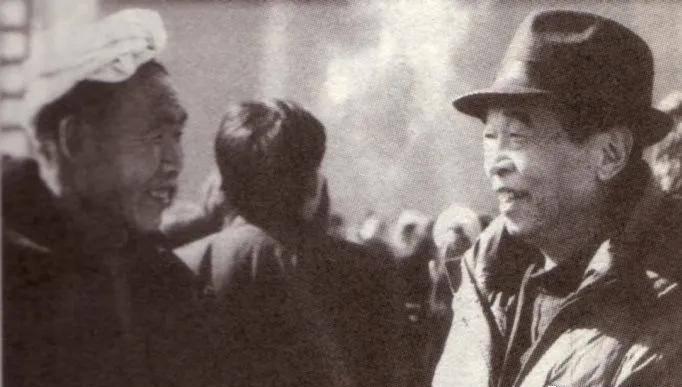
李開方與民間藝人
再就是陝西省歌舞劇院交響樂團、陝西省樂團指揮、陝西省合唱協會會長馮長路。他的指揮演出曾獲國家級一、二等獎,省級一等獎五十餘次,他本人也多次獲指揮獎。成為陝西樂壇指揮中的獲獎專業戶。馮長路兄是上海音樂學院畢業,他弟弟馮永祿是我的發小玩伴。
還有,西安市棋類運動協會的副主席兼秘書長,著名棋類競賽的裁判員、象棋高手張豐。他還是中國立體象棋專利的發明者,著有《象棋成名局賞析》《象棋弱勝強戰例》《西安象棋五十年》等,其論文《中國立體象棋的設定》榮獲優秀科研、學術成果特等獎,及國際優秀論文獎。為把中國古老的象棋推廣到世界,貢獻了自己卓越的才華。此項工作,并得到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上司人的關心和重視。
張豐之弟張興林是我國小六年的同班同學。他的小弟張泰麟,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小提琴拉得好,而且是一位山水、花鳥、人物皆擅長的畫家。張豐家學淵源深厚,伯父張劍平(又叫張鴻業)是國民政府中将參議。家住南四府街36号院,這個大院也叫張家大院,抗日戰争時期任孫蔚如部陝西警備一旅一團團長,出征參加中條山戰役,易俗社當年編演的《血戰永濟》,其中就是寫的他的事。張豐的父親張鴻志曾在馮玉祥主辦的西北軍校上學,後又從黃埔軍校(長安黃埔軍校七分校)十五期畢業,任過鳳翔師範等學校軍體教師;母親劉滐卿出身于鳳翔教育之家,外祖父劉少甫身兼縣教育局長和陝西省立鳳翔師範學校教務長之職。其母親能書善畫,剪紙作品《保衛和平》、刺繡《梅蘭竹菊》1957年曾榮獲陝西民間藝人大賽的二等獎。
我的同學中的能人還有任志成,住在四知村三道巷最後一家院子裡,是個獨院。後門就臨含光裡那個大澇池。他家是從河南遷到西安的,記得他父親特能幹,在家裡不但養奶牛、奶羊,還精于果樹栽培嫁接什麼的,他家院子有一種蘋果和梨嫁接的樹,我還吃過這樹結的奇異的果子呢。
志成上國小時就特機靈,動作靈活,飄忽來去,被送外号“老鼠影”,傳神得太!五十多年後有同學說這外号是我起的,我急忙否定。回憶起,我還真不敢掠人之美。國中以後,任志成漸顯才智過人之處,一心想着升高中考大學,其志甚堅,讓我這個對考上大學沒一點兒自信心的退縮者,很是佩服。因我國中畢業壓根兒就沒報考一所高中,能考上個中專技校就算燒高香咧!
任志成
一心想上大學的任志成高中畢業卻遭遇上山下鄉,被分到蒲城。1968年11月,時為西安插隊下鄉第一批。當年,我是唯一送他和另兩個同學陳浩、李志豐下鄉的老同學了。天蒙蒙亮時,趕到他們所上的西門外的西安三十一中,随後我們坐在一輛敞篷的大卡車上,随全市下鄉的車隊在西安西大街、鐘樓、新城廣場巡遊一圈,以顯示響應毛老人家号召。經過長途奔波五六個小時,才颠到了蒲城縣的蘇坊公社寨子大隊。
記得在蘇坊公社,農民們演平劇《沙家浜》折子戲,招待知青,演到郭建光和傷病員在蘆葦蕩中時,鬼子巡邏船過來了,郭建光本應手朝後一揮,說聲“隐蔽”,誰知演員忘了台詞,看大家不動,緊急處吼一嗓子:“都圪蹴哈!”我看在場的沉浸在興奮激動中的知青們,都沒有覺察。而我卻想,我的才子同學任志成,該在這廣闊天地圪蹴下咧!誰知志成名字叫得好,有志者事竟成嘛!不出三年,以工農兵學員身份,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學能源動力系,可以稱得上我同學中第一個考上大學的,還是國家重點大學。後又任西安重型機械廠大鑄鋼分廠廠長和西安消防器材廠廠長,幹得雖不是驚天動地,但事業也是異常之紅火。
搞文學,當專業作家的除筆者本人外,還有和任志成是鄰居,他倆一起從國小上到高中,一同上山下鄉插隊蒲城縣蘇坊公社的陳浩。當然,陳浩仕途順暢,曾從新城區辦公室主任,幹到西安市委副秘書長。後來又任《西安晚報》社長兼總編輯。
陳浩家也是獨院,但家中人口多,兄弟姐妹七八個,一大家人十幾口。記得陳浩父親在家養牛、養羊、養兔,六十年代有什麼一身雪白紅眼睛的安哥拉長毛兔、青絲藍兔,我也鬧不清,價高得一塌糊塗,一對兔一兩千元,能折合現在的五六萬元。派出所和西大街公社派專人盯着陳家,怕他們倒賣。陳家養的有奶牛、奶羊,記得我們小時有關中民謠唱道:“泥瓦匠,住草房;紡織娘,沒衣裳;賣鹽老婆喝淡湯。種田的,吃米糠;炒菜的,光聞香;編席的,睡光炕;做棺材的死路上。”我想,陳家也應該是:養奶牛的喝涼水。誰知一問陳浩,他卻說鮮牛奶、羊奶,不好存放,五十年代老百姓窮,喝奶的少,賣不動了,陳浩他爸就逼着孩子們喝,把陳浩喝得聞到奶腥味就發嘔想吐,喝傷了,一輩子再不喝奶。今天想來,那年月個體養殖戶也不會加工酸奶、奶粉什麼的。也沒個防腐劑什麼的新玩意兒。
當年,報載:西方英美帝國主義把賣不動的牛奶,倒進大海。除過說生産過剩,莫非情況和陳家有類似之處。陳浩家窮,孩子多,上國中還拿着助學金,當然舍不得倒了……
一次同學聚會,說起陳浩一輩子不喝奶。在座的四知村兩位同學張興林、任志成,都說他們也是一輩子喝不成奶,都是家中曾養過奶牛、奶羊,從小就喝傷了。讓我聽了稀罕,看來這反成咧:養奶牛、養奶羊的不喝奶!
陳浩的大哥叫陳海,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是一位資深的文物修複專家。陳浩跟我說:“我大哥參加過秦兵馬俑博物館的銅車馬、法門寺佛指舍利的影指的修複工作。”
美術上還有十幾歲就享有小神童之稱的畫馬天才韓少立,他畫的馬聞名畫壇,為西安一絕,繪畫大師齊白石還寫信贊揚、鼓勵過他。我小時候是少立兄的忠實粉絲。退休後,我們一起被聘為西安市文史館館員,一起開會采風,見面機會比小時候還多哩。
其他門類也不乏名人,有造槍炮的軍械專家、進階工程師,有國術名師,有紮耳針為陝西一絕的針灸大夫,有陝西省籃球隊的隊員等等。我國小同學陳愛梅戲曲學校畢業,她姐姐就是秦腔界的名角。
畫家張正
還要說的就是陝西省山水畫研究會副主席、西安山水畫院院長的畫家張正。張正的爺爺張茂茹是一位文化學者,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曾任國民二軍胡景翼部的軍需處長。西安最早的一批電影院,位于北大街鐘樓附近的明星電影院,就是他老人家建立的,因其思想進步,抗戰期間在電影院播放了蘇聯電影《列甯在一九一八》而被關閉查封。住四知村甲字六号的郗曉鋒,民國年間當過報社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郗曉鋒曾寫詩盛贊張茂茹先生:“設身處世似子房,智勇兼備如孔明。”還有題詞“壽臻耄耋,九如三多,緬懷儀采,吾侪楷模。”張家的大門朝北對着西梆子市街,後門朝南開在四知村的一道巷。當年,四知村住戶稀少,張家祖上即張正的太爺在這裡開了不少菜園子,以後無償讓别人蓋房占地,到六十年代前後,還留下四知村二道巷一個菜園子,老人們稱為張家菜園。因西梆子市街地勢高,他家的樓房是四知村的制高點。每當巷子裡的小娃娃們放鴿子時,鴿子飛上幾圈,累了,就紛紛栖落在張家宅院樓頂的屋脊上。
張家和我們家,尤其是和我住白鹭灣的外公家,當年都是通家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