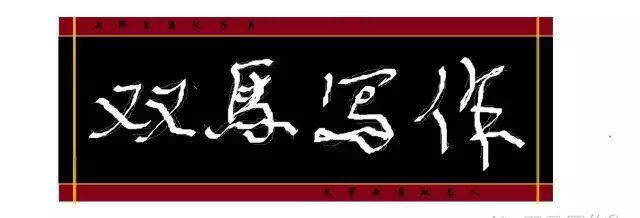
藝術的本質
如果把有實物(或事實)參照的定義,稱為形而下,那麼藝術無疑是形而上的。這裡定義往往不可能實作,事實上也從未真正實作過。曆史上,關于藝術起源的讨論,其實質是想通過對藝術定義的形而上向形而下的轉換。概念,無非就是通過“象征”的形式,從“不科學”逼近“科學”,而這種科學性的衡量标準,從來隻以大衆情感對“像”與“非像”間的那條鴻溝,作出非理性的人為劃分。
斯賓塞指出,藝術與審美本身就是作為高等動物的人類所特有的“消遣”。相比柴米油鹽,顯然這類高雅的消遣隻能定義為“遊戲”。然而,這隻是藝術活動的一種特征,隻為差別相對低下的勞動形式。是以相比而言,普列漢諾夫對“勞動先于藝術”的了解,更為精準而活潑。假設藝術作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作為同樣消耗精力的勞動生産,它又能是什麼?它必當首先是勞動,其次才是遊戲。
遊戲說并未直指起源,更别說本質,但“遊戲之色彩”依然看上去那樣鮮活,這是因為勞動不需要美,而藝術以及相關審美活動與美息息相關。這種趣味性的選擇,比起精力的耗損似乎更有說服力。無疑,藝術活動無論作為勞動,還是遊戲,作為人類社會生活的附屬品,消耗人多餘的精力是必然的事。可是如果人們将生活本身,就看作一場遊戲,那麼這樣的套娃定義就失去了效用。這時遊戲概念已變化了把戲,并不是尋求好玩,而是對苦樂情感的體驗。體驗可以是極端或中性的,或者是無方向,無選擇,無目的的,因為本來生命運作就是件被動的事。那麼,這種藝術起源說,和普适之創造說一樣,等同于廢話——生命來到世間,天生被賦予了創造的使命,哪怕是毀滅這類最醜陋的創造。
是以,在探讨藝術起源時,文學家或學者們隻是抱着輕率或偏愛的态度,去嘗試定義他心中的藝術。這種定義多數無效——它隻是事物特性的某一側面的呈現。其中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也隻是定義者心中比較浪漫的臆想。這種臆想式的起源論,還有阿爾杜塞的多元決定論:任何文化現象的産生,都有種多樣的複雜原因,而非一個簡單原因造成的。這同樣屬于“廢話哲學”。它隻是提供了這樣一個類似的借口,諸如“泛神論中神的數量是數不清的”,以論述追溯藝術起源的不可能性。這本身不就是臆想的最好證明嗎?
而與之孑然相對的,愛德華泰勒似乎找到了真相。《原始文化》作為神話,宗教,語言,藝術,習俗之文化發展研究巨著,巫術被擺到了極為重要,甚至可能是正确的位置。如果僅僅作為藝術起源,我想這類形而下的結論足夠了。可我們所探讨這種起源性的目的,并非真的想要搞清藝術的來源——産生第一次藝術行為的那種沖動。我們想要了解的更為深沉:浮冰之下的那六分之五。這顯然不是因潛意識對鬼神敬畏而作的祈禱或祭祀。這不是心理底層的研究,榮格那套集體無意識在這裡也不适用。那種普适的文明起源,單單就不适用于藝術。生存和勞動都無關于藝術,盡管藝術最起初的功用會涉及到對生存的訓練。即便如德國學者古魯斯所言,遊戲并非沒有實際功利,就像貓在玩耍線團時,也為将來的捕食做準備。但這也隻是打破斯賓塞對其“遊戲說”的純然無功利的高尚看法,而這本身無關藝術。
那麼藝術的本質究竟是什麼?似乎起源論對其并無多大助效。看來,最接近的還是德谟克利特和亞裡士多德的摹仿說,以及克羅齊的表現說,或者托爾斯泰的再現說。摹仿是藝術行為的方式,而表達和再現是過程,然而他們的共同點又是什麼?象征。依我看,這是對于藝術這種具體行為的共性把握,也是對藝術這種形而上抽象概念的核心内涵解釋。想要兩全摹仿說與表現(再現)說,象征是直通橋梁。
事實上,摹仿說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就人類生活言,大部分勞動行為與科學研究,也基于對自然或生活的摹仿。自然,本身就是一個遊戲平台,而人類則是資料采集的主體(也是樣本)。人類依據各類自然屬性和資料,來擷取經驗,進而學習和成長自身。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饋贈。從捕獲陽光到補給水源,從利用走獸到摹仿飛鳥,這些都是運用自然規律而獲得實效利益的生活本身,是文明通過學習和複制自然進而自組織演化的程序。一切的一切,都基于摹仿。正如我們不能将推犁耕土,水車翼行視作藝術,我們也不能将文明發展的本質替代藝術的本質。從邏輯概念上講,文明之概念完全覆寫了藝術,這種最底層的共性必然也會在藝術上呈現。是以,摹仿必然是藝術的重要特性,沒有摹仿,也無法産生藝術。同樣的,沒有摹仿,也就沒有勞動生産。兩者間的差别在于,摹仿的範圍和對象不同。
是的,藝術沒必要摹仿事物的機能。它隻是重構一個形象,如同詩歌,将内在的心靈賦予具象的辨別。托爾斯泰對藝術的了解盡管感性,但已極為接近真相。他說:“一個人為了要把自己體驗過的感情傳達給别人,于是在自己心中重新喚起這種感情,并用某種外在的标志把它表達出來……這就是藝術的起源。”和克羅齊不同,他并沒說藝術的本質是直覺。克羅齊用抽象解釋抽象,反而讓人更糊塗。直覺是什麼?是重構形象嗎?它的來源真的是情感嗎?直覺的心靈過程是怎樣的,它又如何牽涉到情感的表現?這些他都沒說清楚。如同一堆亂麻,想讓人以高超的悟性去解開,是不可能的。
是以,我說藝術的本質是象征,這是基于對摹仿形象和表達情感的綜合共性的提取。象征的方式是從心靈過程中擷取一個新形象,去取代原始的現實形象,而它擷取到制作這個形象的過程,是通過摹仿。而情感和思想作為底層和終極的表現物,是作為目的呈現的。一個寫實主義雕像或繪畫,再現真實并不是目的,象征這種“真實”而使人獲得的情感才是這件藝術品的真實意義和價值。就如同局部的真實——斷臂維納斯,和将之複原成整體的真實,同樣作為情感的象征物,兩者意義就并非局部與完整的差別。真實本身就包含殘缺,未必事物隻有完整才能表達情感,是以再現真實不代表再現完整,甚至作為藝術象征手法,情感這東西本身就是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完整。然而,這種抽象的論述可能會導緻誤解:并不是說美從那個完整中失去了什麼,而這本身就是一種嶄新而完整的“殘缺美”。自然,作為感受這種美的情感亦然。
2022.2.4于鳳凰新村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