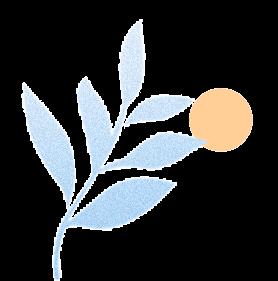
引導關注
俗話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結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無論男女,一過30歲還未娶嫁、未生育,街坊鄰裡、父母親戚,就變得比你本人還要着急。生怕你“剩”在家中,成為出不了手的“大麻煩”。
然而,如今的90後、00後女性,卻甯願單身被催婚,也不願草率地結婚,有些女性甚至打起了不婚不育的主意。
對此,《下流社會》一書中解釋到,單身比例的攀升,是因為現如今的男女,對人生失去了熱情。是以,“下流”不僅僅是收入的低下,其人際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熱情、學習意願、消費欲望等,也全都較之一般人來說變得低下。
細想之下,這話說得不無道理。
一個人對人生都失去了熱情,哪還會結婚生子呢?但是,反觀現階段的90後、00後女性,她們在職場拼搏時朝氣蓬勃、與朋友觥籌交錯時熱情洋溢,她們生活精緻、裝扮靓麗,全然沒有對人生失去熱情的頹唐。
說這樣的女性進入了“下流”階段?确實有些言過其詞。
那為什麼如今的90後、00後女性,甯願被催婚,也要不婚不育呢?本文将結合以下三點,來讨論一下這個問題。
當然,婚姻确實具有階層流動的功能性。有些并不怎麼獨立,也并不想要通過自己努力改變生活品質的女性,就是想要通過婚姻生育,來改變後半生的生活。是以,她們會想盡辦法去迎合男人,也是可以了解的。
由于這些人的婚姻,本身就是一場交易。并不存在男女平等之說,隻是單純意義上的“資源置換”,是以本文探讨的90後、00後新時代女性中,并不包括這部分人。
1. “多變”的男人,
讓女性對婚姻充滿絕望
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很多女人不是不想結婚,而是不敢結婚。被問及90後、00後女性為何會婚育推遲,或終身不婚時,高贊回答竟然是,“看沒看,今天那個家暴的?”
這幾天,西安某公司職員當着孩子的面,毆打孩子母親的事情,引發了熱議。素日裡在公司唯唯諾諾的一名男職員,回到家竟是另一副面孔。看來魔鬼和天使,在撕下面具前,真的不好辨認。
結婚前,這名男子也是百般體貼的。嘴上說着“我養你”,心裡念的“全是你”。然而,這世上哪有什麼無緣無故的愛,所有的饋贈,早已标好了價碼。
女人做夢也沒有想到,昔日大方、體貼的“稱心人”,婚後竟會變成吝啬、暴躁的“讨債鬼”。他可以一筆勾銷掉女人作為全職媽媽的所有付出,也可以全然不記得之前對你的種種承諾。
總之,他可以一夜之間,變成你之前不認識的模樣。
在他們眼中,“養你”已經成了一件不值得的事情。而此時的你,一旦把自己變成了他們的“附屬”,就不可能得到尊重和諒解。男人隻會覺得你的一切都是他給的,不會記得你曾經為了他,為了這個家所做出的犧牲。是以,他有權利對你做任何事。
《蝸居》裡面的宋思明就是如此。
宋思明一窮二白時,是原配姜淼淼陪着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功成名就後,宋思明卻忘記了姜淼淼的所有付出,也忘記了他們曾一起度過的苦日子。轉而奔向了不愛他,卻隻會利用他的海藻。
男人的“多變”,讓90後、00後女性發現,這世上本就沒有一成不變的感情。男人也許隻在乎自己,甚至是身體,根本不在乎感情。
在《11個男人對心理師說》這本書中,心理咨詢師布蘭迪·恩格勒接待了許多被感情困擾的男性。在這過程中,布蘭迪發現,男人終其一生,不過是在尋找一個适合自己的女人而已。他們即便與女人相愛,也不能保證男人在身體方面保持忠貞。
既然男人需要的,是适合自己的女人。那他們在不同時期,内心渴望的女人類型也會是不同的。落魄時,他們需要的是能照顧他們、幫助他們的女人;成功後,他們需要的是能令他們開心、讓他們心動的女人。
是以在這種情況下,一旦身邊的女人,無法滿足他們的預期。男人就變了。這個時候,通常道德感低的人,就會四處撩撥,尋求慰藉;而道德感高的人,雖然守住了身體的忠誠,卻控制不住精神的厭惡。
“多變”的男人,讓女人覺得恐懼,且毫無安全感。看過了一次次的不确定,和背叛後,90後、00後女性便對婚姻充滿了絕望。是以她們才會認為,不結婚遠比嫁錯人要好得多。
2. 男女關系在家庭生活的不平等,
讓女人在結婚與不婚之間搖擺
人都渴望自由,特别是對于90後、00後的新時代女性而言。但是,家庭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關系,卻讓結婚成為了一個難題。90後、00後的新時代女性因為不想繼續成為“落後”婚姻形式的犧牲品,是以她們選擇了不婚。
我相信“不婚”并非她們所願,隻是婚姻中不能承受的重,吞噬了婚姻的美好,讓渴望獨立、自由的90後、00後新時代女性,不得不去尋找一種舒适的生活狀态。
是以,在我看來,解決90後、00後女性不婚不育的關鍵在于,消除男女關系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改變舊有的婚姻形式。
《女性主義有什麼用?》一書中提到:“許多現代女性主義者認為,隻要婚姻以落後的形式存在,它就永遠不可能為異性戀關系中的男女提供平等---因為它使妻子在成為父權制單元的一部分時,失去了她們的姓氏、獨立以及自由。”
什麼是“落後”的婚姻形式?
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來看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模式,是怎麼樣的?對此,女權活動家朱迪·布雷迪在《我想讨個老婆》一文中,解釋得現實又露骨:
“我想讨個老婆,她會照顧我的生理需求。我想讨個老婆,她會使我的家幹淨整潔。她會照顧我的孩子。也會照顧我。我想讨個老婆,她會洗衣、熨燙、修補,必要時更換,她會把我的物品放在合适的位置,以便我在需要時能立即找到。”
在舊有的婚姻形式中,老婆似乎成為了“超人”。
可笑的是,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來,一部分女性,居然還在身體力行地追求着這種完美的主婦理想。
進入到21世紀後,當男人想要繼續補充這段小詩,“我想讨個老婆,她會上班賺錢,和我分擔一切生活開支。她會省吃儉用,為我買喜歡的遊戲裝備”時,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了。
想要在婚姻中做“超人”的女性,竟然惶惶然地領下了任務。
《春暖花開》裡的葉曉薇就是如此。兒子體弱多病,丈夫在外國打工。葉曉薇一邊上班,一邊照顧孩子,獨自一人承擔着婆婆和小姑子的重擔,并沒有覺得有任何不妥。
《親愛的自己》裡的張芝芝亦是如此。為了養家、照顧孩子,做着一份簡單、沒有挑戰的工作。四季可以更換的衣服就那麼幾件,賺的錢自己舍不得花,卻要補貼婆婆家。稍微有些照顧不周,還會被丈夫不留情面地斥責。
自己賺的錢自己不能花,照顧家庭、孩子和婆婆,似乎成了女人的分内事。這樣的情況,90後、00後女性看在眼裡,既恐懼又憤怒。她們想要去改變,又自知力量薄弱,于是慢慢拒絕了婚姻。
《紙牌屋》第四季中,克萊爾被一位年輕的母親問道:“你後悔沒生孩子嗎?”克萊爾反問道:“你後悔生孩子了嗎?”
到目前為止,還是有很多女人相信隻有生孩子,才能實作女人的價值。從生物學的角度上講,結婚的本質,确實是為了生子。
然而,如今90後、00後的女性,卻并不這麼認為。因為比起生育,她們更在意的是自己的獨立與成長。
是以,她們便沒有了生育的熱情。
正如《女性主義有什麼用?》提到的那樣,“一個真正獨立的女性,不需要用母親或妻子來定義自己的身份,她通過自己的選擇來定義自己,既不借助孩子,也不借助男人,而是采取自我認同,自己選擇了自己。”
3. 個人空間的壓縮,
讓女性對婚姻望而卻步
心理學中有一個理論,叫作“刺猬效應”,強調的是人際交往中的“心理距離”。
“兩隻刺猬要相依取暖,一開始由于距離太近,各自的刺将對方刺得鮮血淋漓,後來它們調整了姿勢,互相之間拉開了适當的距離,不但互相之間能夠取暖,而且很好地保護了對方。”
經常聽說男女雙方因為家庭、孩子,壓縮了自己的個人空間後,完全失去了自我。
年輕時還未實作的夢想、事業上拼搏下來的果實、能讓自己産生幸福感的興趣。當這所有的一切,都因為家庭和孩子,而不得不放棄時,你又怎麼可能會幸福?一個不幸福、充滿怨念的母親,又怎麼可能教育出一個樂觀、健康的孩子?
聽過這樣一句話,覺得說得很對:“美好婚姻的本質不是愛情,而是共生關系。”
婚姻中所謂的“共生”,應該是互不打擾、彼此協助、合力共赢的關系。而不該是極力壓縮一個人的個人空間,去成全另一個人的自由。
還記得那位56歲離家出走,“自駕旅行”的阿姨蘇敏嗎?
幾十年來,蘇敏一直為丈夫活、為孩子活、為孫子活。既要外出工作,又要操持家務,還要忍受丈夫的臉色。長久以來,蘇敏活得并不開心,因為她根本就沒有自由。
小到飯菜的口味,大到生活開銷,蘇敏根本就沒有決定權。直到她駕車離開,去其它城市轉轉,蘇敏才重新品嘗了自由,也重新露出了笑容。
現實生活中,還有很多的“蘇敏”。90後、00後女性一邊鼓勵蘇敏阿姨,一邊告訴自己,警惕被婚姻壓縮掉了自由。但婚姻是兩個人的事,本着對伴侶的尊重,你根本沒辦法獨立決定自己的自由。
于是,慢慢地,在“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失望中,90後、00後女性,開始對婚姻、對生育望而卻步。
羅曼·羅蘭說:“生活中隻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那麼,認清了婚姻的本質後,又是否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婚姻中呢?這大概需要90後、00後女性拿出很大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