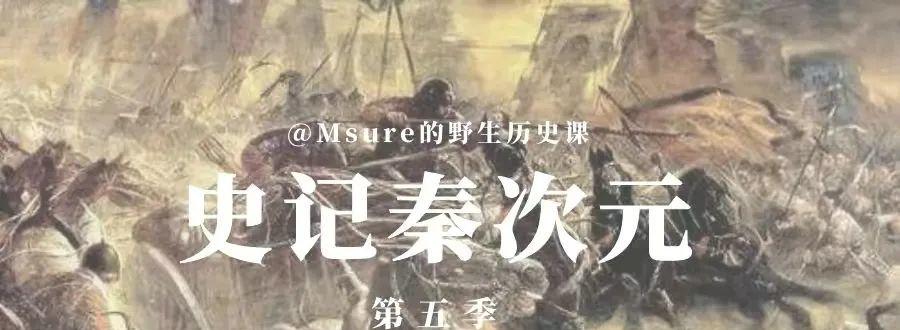
秦德公繼位的時候三十三歲,正值年富力強的時候。他的哥哥秦武公有個兒子叫白,沒能繼承他父親的位置,封到了平陽。《史記》中是這麼說的:
“(秦武公)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
從這個記錄看,讓弟弟德公繼位,像是秦武公的安排。秦武公死後,也葬在了平陽。他的兒子被封在平陽,也許僅僅是安排他為自己的父親守墳而已。還有一件事,秦武公死後,陪葬的人就有六十六人。這些應該都是秦武公的親信重臣。辦這事的人顯然是秦德公,就算是秦武公臨終這麼安排的,秦德公似乎在執行這件事上,一點都沒有手軟。
秦德公繼位那一年是公元前677年,也是這一年,在晉國,晉獻公繼位。
晉獻公雖說在後來兒子繼位的事情安排得有點荒唐,但是,并不妨礙他是春秋時期的一代雄主,也是他在位期間,讓晉國國力大增,成為一方大國。客觀上也許可以說,是他奠定了晉文公後來成為霸主的基礎實力。
新興起來的秦國對于晉國來說,應該還是一個不入眼的小國。不過,在這個時期,情況變得微妙起來。在這之前,秦國的發展似乎和東方各國沒有什麼直接的沖突,他們不過是在和西戎的各部族之間搶地盤。随着他們的實力不斷壯大,向東發展也就成了他們的國策。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蔔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
我們也許應該特别留意秦德公在雍城的這次祭祀。這是秦德公在位期間,最重要的一件事。秦人似乎需要的也就是這次祭祀時占蔔的結果:“後子孫飲馬于河。”
秦國的後代子孫将繼續向東擴張領土,到黃河飲馬。
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秦國和東方各國的沖突必然發生。首當其沖的就是晉國。
秦德公在位期間,和晉國之間好像還沒有發生什麼直接的利益沖突。畢竟,他在位時間太短了,盡管當年他隻有三十三歲,隻幹了兩年,就死了。是不是死于在他繼位第二年夏天的那場瘟疫,很難說。他的兒子秦宣公繼位。
從秦德公的年齡上推斷,秦宣公繼位時應該也很年輕。畢竟他爹死的時候,也隻有三十多歲。
此時距離周王朝建立已經過了三百多年,也就是說,像晉這樣的老牌諸侯國,也已經立國三百年了。随着周王室的衰弱,齊國和晉國坐大,成為兩個超級大國。
而此時的秦國,算是剛剛登上曆史舞台,在和西戎的不斷征戰中,逐漸穩定了自己的地盤,開始向東推進。此時應該沒有人把他們放在眼裡。
那幾年,幾個諸侯國幹什麼呢?
“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穨。三年,鄭伯、虢叔殺子穨而入惠王。”
也就是說,至少衛國、燕國、鄭國、虢國在那段時間,忙着介入周王室的奪位之争。說白了,就是在周王室建立自己的代言人。
秦國沒有參與。對于新興的秦國來說,他們應該明白,趟這趟渾水對他們未必有什麼實際利益。穩固自己的地盤,繼續兼并西戎各部族,對他們來得更實際。
晉獻公主導下的晉國也沒有參與。這可能是因為他在這段時間,一直忙着擺平晉國内部公族的威脅。此時他似乎也并不需要周王室來支援他。從後來我們可以看到,就在晉獻公在位的那些年,他讓晉國的版圖擴張了三倍。也就是說,晉獻公應該非常穩健地推進他的領土擴張計劃,這也是從蠶食晉周邊的小國和西戎各部族的地盤開始的。比如,在公元前672年(晉獻公五年),晉獻公就攻下骊戎,得到了骊姬和她妹妹。這也埋下了晉國後來的隐患。
好了,我們應該可以看到秦晉兩國沖突的所在了。新興的秦國在擴張地盤,老牌的大國也在擴大他的版圖。秦人向東推進的步伐終于和東方的大國有了直面接觸。這種接觸是從沖突開始的。于是,秦晉第一戰爆發了。
“(秦)與晉戰河陽,勝之。”
這一戰的直接導火索是什麼?《史記》中沒有說,誰先挑起的,也沒有說。從這句話的意思看,秦國作為一個新興的諸侯國,面對老牌的大國晉國,并沒有退縮。多年來,他們經過太多的戰争洗禮了,打仗他們不怕。結果,他們也真的打赢了。
這算一次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嗎?似乎也算不上。這一年也是公元前672年。面對西方的新興的秦國,晉國也許隻是把它當作一個西戎小國來看,也許敗于輕敵。但同時也意味着,在多年和西戎各部族的戰争中,秦國磨練出了真正的實力,讓他們有能力和東方各國也可以交一下手了。
河陽之戰,應該大大提振了秦國的士氣,同時,這個從西方一路穩步東進的年輕諸侯國應該也是以進入東方各國的視野。這也是秦國進入東方這個大戰場的開始。
從這一刻起,秦國和東方的沖突再也不可避免了。同時,打了勝仗的秦國應該也意識到,和晉國爆發這樣直面的沖突,還遠不是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