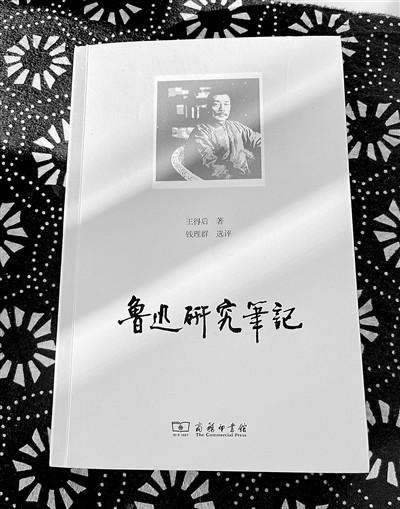
王得後1975年在天津
王得後(左)與錢理群在開封合影 趙園供圖 1933年1月出生的王得後先生,是享譽學界的魯迅研究專家。他的《〈兩地書〉研究》《魯迅與中國文化精神》《魯迅心解》《魯迅教我》與《魯迅與孔子》等書,在“新時期”以來的魯迅研究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王先生最為知名的貢獻,是在1981年魯迅誕生一百周年時提出并且系統論述了“立人”是魯迅思想的核心。用孫郁教授的話說,王先生的這一成就,“近四十年間,一直被學界引用”,“我們現代讨論魯迅思想的原色,都在引用他的看法”。而在同為魯迅研究專家的老友錢理群看來,王得後先生的業績還有《兩地書》研究、魯迅與孔子思想比較研究,以及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異同研究。所有這些,都是魯迅研究也是現代中國文學史與思想史上的“真問題”與“大問題”。
得後先生的探索,有些已經化作“常識”,成為了有關魯迅的“基本知識”;但也還有更多,因為深刻、獨異與不合時宜,其意義與價值尚有待充分認識。有鑒于此,在魯迅誕生140周年之際,錢理群先生為王先生編選了一部魯迅研究精選集——《魯迅研究筆記》(商務印書館,2021),是書收錄了得後先生從事魯迅研究近半個世紀的代表作。錢先生撰寫了兩萬餘言的長篇導讀,又在前言中叙及得後先生其人。王先生之著述與錢先生之評點可謂“相得益彰”。書中處處可見錢先生的“知人者言”,而王先生文字的思想力量也藉此更在在可觀。
我們特約鮑國華與王芳二位青年學者,寫下他們心目中的得後先生,既彰顯前輩為人為學的風采,也表達由衷的祝福。
——特約組稿李浴洋(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
——王得後先生《魯迅研究筆記》讀劄
“根柢在人”
◎鮑國華(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得後老師的着力之處則在“人”
在新年前夕,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錢理群老師選評的《魯迅研究筆記》,精選得後老師不同時期的魯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協理此事的李浴洋兄打來電話,約我為該書撰文,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心裡卻不免惴惴。這半是因為對得後老師的著作了解不深,缺少心得;半是因為多年前在後海邊,老師曾告誡我和同遊的兩位朋友,不要寫有關他的任何文章。幾天後收到電子書,拜讀一過,深感有撰文的必要。這不僅是為了20年來的師生情誼,更源于再一次被他的文字及其背後的人性光芒所打動。
《魯迅研究筆記》收錄了得後老師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魯迅的20篇論文和雜文,是他數十年來研究的精華。魯迅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重新起步,伴随甚至引領着時代思想的風華。以李何林、王瑤、唐弢等為代表的老一輩學人,以嚴家炎、樊駿、王信等為代表的“中生代”,和以王得後、錢理群、王富仁等為代表的“新生代”,幾代學人形成合力,共同締造了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輝煌時代。在20世紀80年代崛起的魯迅研究者中,得後老師顯得有些特殊:年齡和“中生代”接近,學術理念則與“新生代”類同。那一代或幾代學人對魯迅的研究,各有側重,或衡文,或論史,或說理,或述道,得後老師的着力之處則在“人”。“根柢在人”(魯迅《文化偏至論》)是他對魯迅的思想原點的發現,也成為他一系列研究的出發點。
在《〈魯迅教我〉題記》中,王得後老師從魯迅的全部著作與譯文中發現了他以“立人”為出發點和中心,據此提出20條互相關聯的論斷,堪稱一篇“魯迅人學思想論綱”。這一系列論斷,源于得後老師數十年來的閱讀與思考,也是對“魯迅是否有思想”這一诘問的有力回應。今天看來,以“人”為原點論述魯迅思想,似乎平淡無奇,不過是常識。例如在得後老師著作中最常引用的魯迅文字“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忽然想到》五至六)。然而,在無視甚至違反常識的年代,思考并總結常識,堅持對常識的言說,則需要非凡的智慧和勇氣。得後老師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魯迅研究著作是《〈兩地書〉研究》(1982年)。與當時備受關注的魯迅小說、散文詩和雜文相比,《兩地書》無疑更具私人性。該書從校勘魯迅許廣平原信和正式出版的《兩地書》入手,提出一系列重要問題,這固然源于他任職于北京魯迅博物館,有資料方面的便利,更在于對魯迅其人及其“立人”思想的長期關注,由此産生獨特的問題意識,努力在研究者關注較少的私人性文本中獲得新的發現。這樣看來,得後老師的魯迅研究不僅具有思想意義,也具有思想史的意義。
照亮同道和後輩的前行之路
研究者對一個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浸淫日久,往往就會不自覺地打上其烙印,不僅形成自家的知識結構,還可能塑造其人格。得後老師之于魯迅和魯迅研究,也是如此。他畢其一生研讀魯迅,對魯迅作品爛熟于心,幾乎在自家所有的著述中都要或多或少地引用魯迅的文字,這絕非刻意為之,而是一種信手拈來的自在從容。魯迅其人其文早已内化于得後老師的精神深處,但他又不是隐身于魯迅背後的學者,為魯迅的文字和人性光芒所掩蓋。
得後老師研究魯迅,從魯迅那裡獲得光,也用自家的生命之光照亮魯迅和魯迅研究的世界,照亮同道和後輩的前行之路。
他的學術著作如《魯迅新解》《魯迅教我》,包括剛剛出版的《魯迅研究筆記》,書名平實内斂,展現出學者的謙遜。倒是退休後出版的幾部雜文集的書名,如《垂死掙紮集》《我哪裡去了》《刀客有道》,更見鋒芒。得後老師之于魯迅,可謂得其文,亦得其人,前者形成他溫潤灑脫的性情,後者則鑄就其古直堅硬的風骨。“立人”是魯迅思想的出發點、歸宿和中心,也是得後老師思想的出發點、歸宿和中心。可以這樣講,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發現和闡釋,塑造了作為研究者的得後老師的人格;而對光明偉岸的人格境界的追求,又使他能夠獨具隻眼、别有慧心地發現和闡釋魯迅的“立人”思想。
“根柢在人”既是得後老師研究魯迅的原點,又是其畢生的精神追求。
從魯迅研究中獲得自我曆練和自我檢討
在迄今已逾百年的魯迅研究史上,一些研究者逐漸泯滅了自我,一些研究者則試圖泯滅魯迅。一部魯迅研究史由此成為現代中國思想與文化的變遷史,也成為形形色色知識分子或自我曆練、自我檢討,或自我表白、自我炫耀、自我膨脹的心靈史。這樣看來,将魯迅和魯迅研究視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面鏡子,也并不為過。顯然,得後老師是從魯迅研究中獲得自我曆練和自我檢討的人。他曾經這樣評價李何林先生:“何林師的魯迅研究是獨樹一幟的。魯迅,是他的研究對象,也是他的信仰。人文學科,在曆史轉型關頭,一個作家順應時代,基于人性與人道倡導新的價值取向,提出系列價值觀,對于他的研究僅僅限于知識層面,限于曆史性的資源,限于紙面的言說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把自己燒進去,從理想、理論到感情誠實地解讀,吸納新的價值觀和價值取向,才有益于人我,才是一種真實的研究。”(《李何林老師與魯迅》)研究者要“把自己燒進去”,這既是對李何林先生學術思想的概括,也是得後老師的夫子自道。
與得後老師相識20年了,每次登門求教,照例是一邊品蓋碗茶,一邊聽他講魯迅,講當年在青海公路學校任國文教師和在天津機修工廠熱處理工廠中的房間當勞工的經曆,在茶興與談興中,一下子拉進了彼此的距離。矜持如我,也能很快放松下來。之是以一直稱他得後老師,而不是王老師,半是因為我碩士和博士階段的導師都姓王,為差別計;半是因為這種無法用語言形容的親近感。
最近一次見面是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初夏。因為眼疾,他已看不清我的容貌,隻能憑借語音判斷來人。照例是蓋碗茶,午飯時還不忘給自己叫上一碗炸醬面。這年冬天他和趙園老師搬入泰康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疫情暴發以來,我難得進京,更難以進入泰康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和老師一别兩年,未能相聚。誠惶誠恐地寫下這篇不成樣子的小文章,期待能到北京為他慶生,還在一起品蓋碗茶,吃炸醬面,談魯迅。
從答辯會上的大學子說起
——得後先生印象
◎王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這本書把版本校對做得血肉鮮活
說實話,我親炙先生的機會不多,按說并沒有資格寫這樣的文章,之是以動筆,還是因為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是得後先生參加的最後一屆,給我的印象太深了,能讓大家看到這幾張珍貴有趣的照片,也算是這篇小文存在的意義了吧,還望先生不要怪罪。
從王瑤先生起,得後老師與北大幾代學人尤其是魯迅研究者有密切的交往,而他的著作也是一代代北大現代文學專業學子的愛讀書。記得最早在圖書館翻過得後先生的《研究》,當時覺得作者真是心思細膩,大段的改動姑且不論,尤能從一詞之改、一句之删中看出隐秘而重大的變化,比如許廣平信中的“秘密窩”被換成“尊府”,是藏起了“秘密的赤忱”等等,年輕時候總容易注意這些小事嘛,不過也順便記得了,這本書把版本校對做得血肉鮮活。
多年後,我去安貞裡接得後先生來北大參加木山英雄先生新書的研讨會,印象最深的還是一件小事。中午接到得後先生的資訊,問我吃午飯了沒,我說正在他們樓下的東方宮吃拉面,先生回說他和趙園老師經常在那兒吃,面特别好,早知道一起吃了啦,“老先生”這麼活潑不拘,我一下子就放下了緊張的心情。
這次為寫小文我又翻看了郵箱——我的記性簡直比老先生還差——原來當時得後先生用碩大的字和我“伊妹兒”(得後先生語)往來,研讨會後還發郵件詢問,我給木山英雄先生提的問題是什麼,他當時沒聽清楚,我如實發去,是關于木山先生“冤獄劇”說法的一點思考,沒想到得後先生來了一封長信和我讨論,可惜我的古詩詞水準有限,沒有很好地讨論起來,如今這因為慚愧而被塵封的記憶一角被突然掀開,實在讓我猝不及防。
成為一種批判和制衡的思想資源
越過這“斷檔”的記憶再次和得後先生見面,就是我答辯的那天了。得後先生不僅經常受陳平原老師之邀來北大做演講和對談,也是陳老師學生答辯會的“常客”,那天先生與錢理群、孫郁、陸建德、王中忱等幾位先生同來,一切如常,誰知卻做了出人意料的“聲明”。
記得是答辯還沒開始的時候,在一片雜亂聲中,得後先生像往常一樣帶着可愛的微笑坐定,不過從包裡掏出來的卻不是印有北大校徽藍色封面的論文,而是厚厚一沓列印紙,A3那麼大,整整齊齊用線裝訂着,得後先生推着眼鏡皺着眉頭,把這麼個大學子翻到中間,幾乎将鼻尖湊了上去,又看了好一會兒。
先生視力不好,陳老師已提前告知了,但現場看到自己的論文被制作得如此“宏偉”,我還是大吃了一驚,或許是聽到了大家的議論,先生放下本子解釋說,近來眼睛越來越不好了,讀論文隻能把字放大了,列印出來一個一個看,不過這樣實在太累,速度也太慢,雖然很努力地看,但到現在也沒全部看完,非常對不起,是以這大概是他參加的最後一次博士論文答辯了。那一刻我的情緒特别複雜,一來是感動,但更多的是過意不去,想不到得後老師竟然會因為看不完我的論文而宣布不再參加答辯(!),當時直覺要說沒關系,但還是忍住了,我明白,這和我的論文如何無關,是老師對自己的嚴格要求。
回想起來,那天就是帶着這樣複雜的心情開始答辯的吧。好在得後先生對我的題目還挺感興趣,和錢理群老師一樣,他始終關注魯迅研究的動向,關注年輕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更新。會上他提了幾個問題,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是關于魯迅對于進化論的态度,得後先生指出雖然魯迅的思想一直有變化,但始終沒有放棄進化論。對此我當然是認同的,不過那時我還沒有看過他的《魯迅與成仿吾們的分際》一文,不清楚先生關注進化論的思路是什麼,答辯後找來看,發覺得後先生是直面魯迅思想的核心:他從一般左翼思想中獨辟出“魯迅左翼思想”,強調魯迅的左翼思想是警惕“你死我活”的鬥争,反之主張“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而進化論是其特質和根柢之一,并由此拒絕對魯迅進行前期、後期的機械劃分,強調人性視角下魯迅思想的連貫性——在這個思路裡,進化論的意義在于從科學的角度确認了(作為“動物性”延續的)“人性”的存在,而“人性”則将“階級性”相對化,成為一種批判和制衡的思想資源。
表達了對當下魯迅研究的一個憂慮
和我以知識為出發點不同,得後先生的論述背後是基于人生經驗的根柢性思考。得後先生這一代學人多是人本主義者,人生經曆使他們對于激進的革命和落後的封建都足夠警惕,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很多關鍵問題都被内化為了他們自己的問題,是以他們不會滿足于探究一枝一節,硬是要突入到文化和現實的根子上去的。和好幾位研究魯迅的老先生一樣,得後先生也表達了對當下魯迅研究的一個憂慮,即過度将魯迅日常化,事實上,今天我們的确需要直面魯迅遺産的現實意義。
得後老師舉了一個例子,讓身為女性的我動容。“新文化興起今年足足一百年了,一百年來,穩固的全面的成就不過白話文。而新文化中的‘男女平等’,至今極不如人意。廣袤的農村不待言,即使北上廣深頭号大城市,女性的就業、薪酬、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地位,依舊低于男性。極端的社會不公,是母親受胎後,如果檢查出是女性,‘做掉’的現象并非個别。何況其他更加難以改革的方面。”(《關于“魯迅文化遺産……”》)看清現實,清點遺産,才能觸及魯迅的核心問題,而我這樣常從“鳥獸蟲魚”看魯迅的後生小子,正時時需要得後先生的良言,反躬自省,審視自己治學的方向和意義。
有人評價得後先生的魯迅研究方法是“以魯解魯”。我想,以得後先生對材料的熟悉和了解、使用之精到,這個評價是恰當的,而得後先生自己則點出了“方法”表象背後的深心:“竭澤而漁是防止自己因為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顧此失彼的疏漏,也是為了識破無意或有意斷章取義,隐瞞、歪曲魯迅,為一己私利欺騙大衆的行為。……通讀、多讀魯迅原著,竭澤而漁,隻要自己有顆誠實的心,就不會自欺欺人。”(《我們今天怎樣認識魯迅》)“竭澤而漁”地閱讀,目的是對人對己的誠實不欺,得後先生可謂得魯迅之真髓,對于我們年輕學人而言,這讀法不僅僅是治學金針,更是理論操練和信仰狂熱的解毒藥石。
至于得後先生自己,我是來了文學所之後才看了他的自述《我一生中的五個偶然》,這篇文章我在微信裡備注的是“最後一個偶然最動人”。這兩天為了寫這篇小文翻出來重看,依舊為此感動,“當我讀完李何林先生的《魯迅的生平及雜文》,我為他擔心了。一些‘批倒批臭’的觀點,他依然故我。他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忍心他重蹈覆轍,我給他寫了一封提出具體意見的長信。我的目的不在讨論問題,更沒有以此認識李先生的意思。我沒有寫出通信位址,不想李先生回信。” 李何林先生欣賞得後先生的善良和才華,不相信出身的限制,為得後先生的工作四處奔走,最後把他帶在身邊才解決。完全不認識的兩個人,因為魯迅結緣,彼此擔心和欣賞,哪一位都沒有任何私心雜念,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得後先生讓我感到親切——他是真的有着一顆赤子之心。
流水賬般的寫着寫着,我的記憶逐漸複蘇,一同清晰起來的,還有得後先生活潑潑的笑臉,真想趕緊找機會去拜訪他,和他聊聊魯迅,聽他說說自己。